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寧肯:一個現實題材的非現實可能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12月02日11:12 來源:北京晚報 孫小寧 寧肯 宮蘇藝攝
寧肯 宮蘇藝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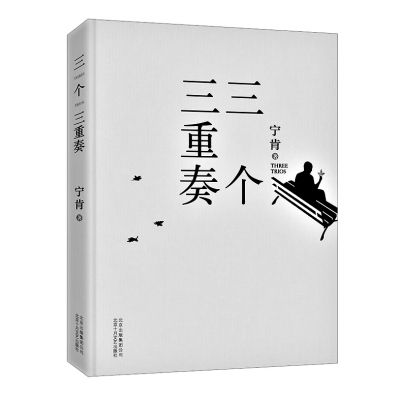
在完美的罪行中,
完美本身就是罪行,
如同在透明的惡中透明本身就是惡一樣。
不過,
完美總是得到懲罰:
對它的懲罰就是再現完美。
——鮑德里亞《完美的罪行》
當現實變得比小說更精彩,當它本身已成為最高的敘述者
“過去我們把權力當成一種他者來看待,是官場之事,和我們老百姓離得很遠,但今天,那些侵入市場的毒奶粉、三聚氰胺等,讓我們知道,這后面都有權錢交易,權力其實已侵入了我們的生活,和每個人都相關。”
孫:還記得我對你的《天·藏》所做的訪談嗎?結束時我說,這部作品太棒了,你恐怕不可能超越。現在看來是武斷了,你又拿出這么一部。一個精神氣質很高蹈的作家,怎么會想著寫權力、性、金錢?這可是另一類作家喜歡的呀。
寧肯(以下簡稱寧):還是跟《天·藏》有關。那部作品完成后,對我有一種壓迫,包括你剛才說的那些,后面隱含的其實是:你還能寫什么?后來我就覺得,應該走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天·藏》是形而上的代表,那么另一個方向是什么呢?肯定是大俗的東西。大雅必須大俗來破。就說到我在這期間的感受:現實生活中的權力與腐敗。這種東西,進入21世紀之后,經過互聯網的放大與直播,更加赤裸地展現在大家面前。而且都有戲劇性,以至于讓作為小說家的我們都感到無力。
過去老百姓看這些,說誰貪了幾十億,都當個笑話。也憤怒,但會覺得離自己遠。現在,新聞不時曝出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之類,你會認識到,這后面有權錢交易。權力腐敗已經很深地侵入了我們的生活。這時就要自問,作為一個當代書寫者,你有沒有能力面對這個東西。
孫:其實是問怎樣面對?
寧:對。不是說沒有小說家面對過,比如那些官場小說之類。也寫得很真實,但大家卻說它們不叫文學,我就在想,它們的問題出在哪兒?
孫:你的結論是?
寧:我認為既然是文學,還是要考慮文學的出發點是什么。文學的主體,你不能失掉。這里先不說這個主體是什么,回頭看那些官場小說。它們寫腐敗、揭黑,內幕也展現得驚心動魄。進一步的,也探討了原因。但這兩點即使寫得再深刻,也都不是文學上的深刻,而是社會學層面的深刻,新聞的深刻。而這些,非虛構作品完全可以替代。
而《美國往事》,黑社會題材,為什么卻震撼人心?不是它揭黑幕揭得深,原因探究得深刻,而是寫了成長、愛情、友誼、背叛、宿命,這些都是人性中的東西,和每個人都相通。所以你能看出,《美國往事》成為經典,不是黑社會寫得多么好,而是它用黑社會做了一道菜,做出來的是美國往事。而前面提到的那類小說,是用權力腐敗做菜,做出來的還是腐敗。
孫:一般認為內幕的東西寫作者躲不開。但你恰恰把權力里面的這些給抽離了。權力因此就像被罩了一件黑袍,很神秘。這讓我想到上月去浙江戴笠故居。那里陳列了很多照片,但都不如墻上的帽子、斗篷往一起一拼,更能凸顯戴笠作為特務頭子的氣質。
寧:你說得對。精氣神是最主要的。還不能正面寫官場,因為一旦是正面進入,就進入它的軌道。只能在它設定的制約下敘述、輾轉,也就被它牽著走了。
孫:而這其實是你最不熟悉的。
寧:是我的短板。我就是再做功課也熟悉不過別人。所以必須獨辟蹊徑。文學有時需要以實寫虛,有時需要以虛寫實。在這個題材上,我想以虛寫實。這樣我才敢觸碰這個題材。
只有住在小屋的窮人,才知道別墅的價值
“以前的題材就相當于我是在小屋寫作,也還挺自得的。現在寫權力,我等于來到一個豪華別墅,我發現它給我提供的人性的東西,實在是太豐富了,也太有挑戰性了。”
孫:三個三重奏,第一組出現的人物關系是杜遠方、李敏芬和黃子夫。杜遠方位高權重,黃子夫與他相比,就是個滑稽小丑。但他們同時存在于小學教師李敏芬的生活中,都想征服她。杜遠方以靜制動,而黃子夫是得機會就下手,卻屢屢不中。我每次看敏芬和黃子夫的戲,都在樂,覺得有喜感。因為敏芬不斷在心理上說服自己服從權力,但每到關鍵時刻,就沒法忍受黃子夫亮出的那口爛牙。
寧:這個細節我受的是德國小說《朗讀者》的啟發。書里的女主人公不識字,但為了掩蓋這一點,她寧愿承擔所有的罪。在外人看來,這是多么不值當的虛榮,但卻是她的自尊所在。小說家就是在這個微小的點上建構起一個人物。非常了不起。
小說中敏芬也是這樣。她在主要的部分已經接受了黃子夫的求愛,卻在外貌上排斥。而這次要的東西里面,有她做人的底線。
孫:因為通常意義上的主要、次要,是從社會、功利角度來講的,對敏芬這個個體來說,這個是她的主要。
寧:而在次要的地方守住自己,這個也只有在權力這個題材張力下才能凸顯出來。
孫:對。換一種題材,敏芬這就叫以貌取人了。而在這里,隱喻的是她對權力的反抗。
寧:這也是我碰觸這個題材不斷有的驚喜。以前我的小說都非常個人化:個人與歷史,個人與大自然。還沒把人投到官場,讓他們面對政治、權力這種復雜的東西。現在發現,這些在某種程度上更能折射出復雜而豐富的人性。也才能出現后面杜遠方、居延澤、李離這樣復雜的人物關系。
孫:這個是你的第二個三重奏。同樣是兩男一女,感覺他們三個人像在對弈,每個人都是以其中一個為棋子,下給第三方看。中間有進退,但每個人都有令人驚異的表現。
寧:這三人年齡結構很有意思:杜遠方比李離大15歲,李比居延澤大15歲。他們是上下級關系,同時又是情感糾結體。為什么愛而不能,又欲罷不能,這里面還是因為有權力攪和著。權力使人性、人際變得如此復雜詭譎。
權力,真是一個強悍的題材。
孫:當然強悍。以前讀《天·藏》,感覺你的語言是玻璃般的光澤,現在似乎都有了像杜遠方一樣的霸氣了。
寧:霸氣也是因為杜遠方、居延澤們是權力的代表。中國幾千年來就是一個官本位社會,權力掌控一切。無論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你想這樣一個系統打磨出來的精英,那個氣場得多大啊。這里面如果有腐敗有犯罪,那也是高智商犯罪。
孫:所以你在小說前面引用了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一段話:在完美的罪行中,完美本身就是罪行,如同在透明的惡中透明本身就是惡一樣……不過,完美總是得到懲罰:對它的懲罰就是再現完美。”這句話太神了,簡直就像是為你這部小說而存在。
寧:事實不是。鮑德里亞這里指的不是權力,而是虛擬世界。講虛擬世界怎樣改變人。我是在寫到第一部分之后看到這個。太喜歡了就放在書前。
孫:既然提到虛擬世界,我們就再談談你小說中的非現實的幻。微博上我們有過一次私信交流,我說的是:“你把現實處理得超現實,但又在精神層面上高度真切”。這當然指的是居延澤被審訊那部分。那個空間甚至讓人想到798,而且為了審訊,你還真設計了一個前衛藝術家進來。那部分太幻了,正是那句:“對它的懲罰就是再現完美……”
寧:審訊這東西太具象,你寫得越像,就把自己變成了那個東西。所以必須寫意。對它進行藝術化處理。學術上經常講所指和能指。能指在這個題材里可能是審訊啦、逃亡啦之類,但一定要知道,所指是權力。而所有的描述,應該是通過能指,將所指寫出來。
孫:也就是居延澤在審訊間沉默不說,他沉默的支撐是什么。這個通過閱讀,讀者最能心領神會。
寧:對。這里以虛寫實,也是和一般官場小說刻意區別開。面對這個題材,你只有把它的公共性給解構掉,本質才能裸露出來。否則,在這個題材上的文學性、藝術性,還有創造性,都解放不出來。
孫:是啊,你的創造性可真是給解放出來了。
寧: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一比,窮人是最懂富人的。從題材講,我以前是一個住在小屋里的人,當然也很自足,突然有天就來到一座大別墅,發現這里可供審美的東西太多了,而這是擁有它的人意識不到的。
孫:對,連那些寫官場小說的人大概也覺得,這東西就是這么一回事,已經不構成審美了。但你在這里,連罪行、連審訊、連男人對女人的征服,都寫得構成審美。
寧:讀官場小說,你其實很能想到潮水與礁石的關系。潮起潮落,本是最豐富的,但它們只保留了礁石,罪行倒是看得倍兒清楚,但水在哪兒呢?純文學就是把水寫出來。水是什么,水就是人性,是過程,也是審美。
孫:三個三重奏,第三組人物是楊修、“我”還有李南。在這部分你寫到了八十年代的北京,相信最能調動起你個人的生命體驗。有關紅塔禮堂的那部分,我還在自己版上刊出過,當時并不知,是為這部小說而寫。
寧:這部分最開始沒打算寫。是在寫完杜遠方、李敏芬、黃子夫之后意識到的——我需要為整個故事找個敘述人,否則故事和故事間連接不上。于是就有了坐在輪椅上的“我”這個敘述者。“我”飽讀詩書,經常做些知識分子形而上的思考。
孫:這個勁頭兒蠻像博爾赫斯。
寧:是借用了這老爺子身上的氣質,思考宇宙、思考時間,也自我反諷、自嘲,總之有那股知識分子的牛勁兒。但我想,不管你多么形而上,如果將你的輪椅推向死刑犯,推向社會,會怎樣?于是我就讓他身處另一個圖書館——監獄。這也是活生生的書啊,因為每個罪犯身上都有大量的社會信息。而他為什么去,又為什么能去,這里我就必須給出一個條件:他有一個強有力的朋友楊修。楊修和“我”曾是大學同學,現在手握權力。從權力者角度看,“我”整天讀書,既不知什么叫社會,也不知道真正的人生,有什么出息。于是就安排他去見死刑犯。一旦找出“我”和楊修的對應關系,我就覺得這個人物太有藝術張力了。必須將他擴寫。寫到他的過去。因為他之所以成為今天這樣,也是和歷史相關的。很多問題都可以往前追溯。
這個三重奏完全是當背景性的舞臺遠景在寫,但也暗含了我的思考。我們說八十年代是理想年代,是熱情的、啟蒙的,但實際上八十年代很多問題都懸而未決。比如權力如何制約。你看幾個人共同騎車去北戴河,路遇麻煩,最終問題得到解決,還是靠李南的特殊身份。
因為一直沒有解決好對權力的制約問題,所以九十年代后物質發達,權力就變得越加畸形。
作家和現實,不只是緊張關系
“作家和現實,不只是緊張關系,它同時還要有智性關系、審美關系,這樣讀者讀你的作品,才進得去,出得來。如果僅僅是一種緊張關系,那就很容易形成……對眼。”
孫:對于楊修,你有一句評價:歷史是什么,他就是什么。這句話該怎么理解?
寧:這是我對楊修這個人物的批判。八十年代,他是典型的理想青年;九十年代,他是經濟大潮的弄潮兒;再到后來,他又因為手中權力而犯罪。一個人看來具有每個時代的典型特征,但恰恰失去的是自我。而在他強大氣場對比下的“敘述者”我,盡管時時被他嘲笑、揶揄,但其實是有自我的,甚至,他的自我就是在這個輪椅上建立的。
孫:一個坐輪椅的讀書人。這個意象,決定了他是在用特定的視角在看待世間。看來有局限,但因此也顯得獨一無二。有的小說寫盡世間,情節波瀾壯闊,但就是無法被擊中,因為你始終找不到它的獨特性。
寧:是,它可能是歷史,是苦難,但它不是自我。一旦敘述者的“我”和這些重合,就顯不出文學的獨特性。因為敘述歷史、敘述苦難,其他文體也可以做。你做了不能說沒意義,但無非是給社會學做個印證。
孫:這個不是每一個寫小說的人都能意識到。或者是從他所表現的題材里面掙脫的。
寧:因為我們中國人的個人歷史意識一直很弱,或者換句話說,沿著個人歷史走的人特別不容易。所以自我非常容易被各種情勢淹沒或者變得模糊。更多的人是在趕時代的趟兒,都是楊修。而我,最大的優點是自我始終強烈。
孫:這部小說和你的《天·藏》一樣,是部自由的小說,有內部的秩序。也有自己的語言方式。我前面說你的語言很霸氣,但其實這里面有進有退,是矛盾的統一。
寧:語言反映的是一個人的思維方法。我們總是講點和點對應,但你有時不妨用面對著那個點。它一定會出你意想不到的東西。你欣賞這個東西,因為你喜歡禪,禪的思維里有這種跳。一跳,就有很多角出來。
我總覺得作為作家,思維與情感的原型不能太簡單。簡單到我只是要揭示要控訴。一定要對所揭示的東西有所觀照。缺少這個,不小心你也就成了它。
孫:但也有人會稱贊那種對于現實采取“我控訴”姿態的小說。因為有句話是說:作家和現實要一直保持緊張感。
寧:保持緊張感,當然是必要的,但作家和現實,不只是這一層關系,它同時還要有智性關系、審美關系,這樣讀者讀你的作品,才進得去,出得來。如果僅僅是一種緊張關系,那就很容易形成……對眼。
有時候你在作品中調侃自己,懷疑自己,一切呈現一種開放心態。這部小說中作為“敘述者”的“我”就是這樣,他也展現自己局限、可笑的一面,這也是我的自我表達。隨著閱讀和年齡的增長,人會知道,作為知識分子,你可以像上帝一樣思考,但也要知道自己并非無所不能。沒什么讓你美得不得了,也沒什么讓你痛苦得不得了……想明白這個,作品才會有多重的可能,也才能讓更多的人和你共鳴。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