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wǎng)>> 舞臺 >> 評論 >> 評論 >> 正文
鈴木忠志 戲劇面具下的哲學(xué)家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11月20日10:47 來源:人民日報 徐 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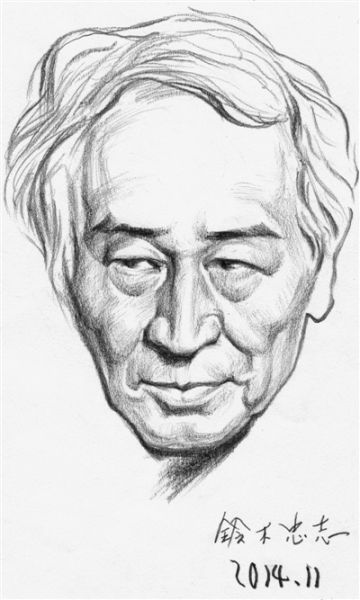 鈴木忠志(速寫) 羅雪村繪
鈴木忠志(速寫) 羅雪村繪人物簡介:
(1939年—),世界著名戲劇導(dǎo)演,擅長融合日本傳統(tǒng)表演藝術(shù)及其獨創(chuàng)的演員表演體系,將契訶夫、莎士比亞等經(jīng)典劇作改編為多語言的當(dāng)代舞臺作品。他同時是日本國際戲劇節(jié)(利賀戲劇節(jié))創(chuàng)始人、國際戲劇奧林匹克與中日韓戲劇節(jié)主要創(chuàng)辦人,多年來積極推動中日戲劇交流。
能夠排演一部完全由中國演員表演的戲劇,是他的心愿。
感謝第六屆戲劇奧林匹克移師中國,它把鈴木忠志帶到了我們的面前。
鈴木忠志,這一國際戲劇盛會發(fā)起者之一,百年來第一位在國際劇壇上與布萊希特、梅耶荷德、彼得·布魯克齊名的亞洲戲劇導(dǎo)演。
而當(dāng)我或坐在他的劇場觀劇,或伏案聽其在字里行間的娓娓道來,或坐在他的面前與其交談,強(qiáng)烈地感受到,戲劇于他,是精雕細(xì)琢的手工藝術(shù)品,是創(chuàng)作的全部——與此同時,戲劇于他,又“僅僅”是一個“介質(zhì)”。如何排戲、排什么樣的戲、在哪里排戲,每一個圍繞著戲劇展開的問號,都是可以牽引人們走向他思想深處的地圖:鈴木忠志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戲劇家,但首先是一位生活在當(dāng)代的哲學(xué)家。甚至可以說,后者是因,前者是果。
以戲劇
對抗“脫身體化”
以此次展演的《李爾王》來說,整臺戲就像一臺精密的由大小不一的齒輪緊密咬合而成的儀器,同時又是生命力蓬勃得幾乎要溢出舞臺的有機(jī)體;它泛著冰冷的金屬的光澤,卻又如此優(yōu)雅迷人,讓人牢牢地被“嵌”入其中。而最具鈴木風(fēng)格的,當(dāng)屬舞臺上演員對身體的使用,這身體包括聲音、包括肢體。
比如,在眾多人物中,除了護(hù)士這一角色有鞋穿,其他人或者赤足,或者腳穿日本傳統(tǒng)足袋——為何如此?“樹越長越高,但根也隨之在大地中越扎越深,向上與向下的力是平衡的。而人類隨著文明的發(fā)展,距離地面越來越遠(yuǎn),不要忘了,人類依賴大地:食物與能源來自土地,我們死后歸于塵土。”在自成體系并為世界眾多戲劇人借鑒的鈴木演員訓(xùn)練法中,腳與地面的關(guān)系最被他本人所強(qiáng)調(diào),“我在訓(xùn)練中反復(fù)告誡演員不要忘記自己和土地的關(guān)系。莫言的小說,在我看來,也是在提醒眾人這一點。”在他的舞臺上,演員赤足或穿著傳統(tǒng)的由植物纖維織成的柔軟足袋,不是如生活中僅僅“站”在地上,而是要通過訓(xùn)練,經(jīng)由腳與地面的接觸,讓身體從地面獲得力量。看鈴木忠志的作品,演員對腳、對全身的使用,借鑒了日本傳統(tǒng)能劇、歌舞伎的技巧,更延續(xù)了這樣一種農(nóng)業(yè)文明時期人與土地的精神關(guān)聯(lián)。
鈴木忠志對演員身體能量的調(diào)動,不止于此。《李爾王》的舞臺上有兩種美妙的線條。一種是靜態(tài)的,由光與影勾畫,被歐洲觀眾比作林布蘭登的油畫,被日本戲劇界視作另類;一種是動態(tài)的,由演員的身體及其動作繪制。李爾王的小女兒考迪莉婭與其他“大人物”的出將入相,如在冰面上以筆直身姿滑行的玩偶,身體始終保持著自己的高度。再看侍衛(wèi),雖快速屈膝往復(fù),但平穩(wěn),身體也始終在一個水平線上——“水平移動”,是鈴木舞臺風(fēng)格之一。與這“橫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垂直的“豎線”。舞臺上,演員即使在站姿與坐姿的轉(zhuǎn)換之間,也始終保持著上半身的筆直。
可以看出,締造鈴木忠志劇場風(fēng)格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演員的身體。這樣訓(xùn)練與要求演員,是追求精致的優(yōu)雅,也是為了讓演員集中使用自身的能量,同時為觀眾提供一種穩(wěn)定感。作為回報,他以無形的大手,將眾人的目光聚焦在演員的身上:看他的作品,就是在鑒賞演員、鑒賞演員對身體的使用。
那么,鈴木忠志為什么這樣關(guān)注身體?“現(xiàn)代人在不斷地‘脫身體化’。過去,人和人的溝通只能通過肢體語言或面對面的交談,隨后出現(xiàn)了麥克風(fēng)、電話,如今是電子郵件。你能想象夫妻兩人同桌用餐,丈夫敲短訊問妻子‘好吃嗎?’‘好吃’妻子也用短訊回復(fù)?這就是現(xiàn)代人的處境。高科技延展了人體的功能,作為生活工具,我不反對,但不能以此作為衡量文明程度的標(biāo)準(zhǔn)。”簡單來說,鈴木忠志是通過對演員身體使用的強(qiáng)調(diào),對抗“文明”對人身體的壓抑,對人動物性能量的削弱與剝奪。在他看來,“文化就是身體”——其獨樹一幟的表演體系與其舞臺美學(xué)風(fēng)格,只是這一思想的“副產(chǎn)品”。
以村莊
磨礪“初心生涯”
除了身體,談鈴木劇場藝術(shù)繞不開的是他和他的利賀村。回到《李爾王》的舞臺。表演區(qū)后方黑色的木制長廊與長廊上六扇黑色木制拉門,讓人有如走進(jìn)日本傳統(tǒng)家屋。這一設(shè)計讓導(dǎo)演對諸多人物的調(diào)度行云流水,也分割出了劇中的現(xiàn)實世界與想象的場景;木制拉門的開與合、光的起與落,以及光影交錯,更讓整部戲有如夢境。不過,這并非鈴木忠志如此設(shè)計的主要目的。
“我這樣做是為了把利賀村的舞臺‘搬’到北京。”是的,利賀村。這個被東京人視作“比莫斯科還要遠(yuǎn)”的深山中的村莊,貧窮且氣候多變,冬天積雪可達(dá)4米,卻是鈴木忠志人生戲劇最重要的布景、舞臺。35年前,40歲的他從東京咖啡館的二層遷至這里,將劇界與媒體的質(zhì)疑、擔(dān)憂斬斷在村莊之外。如今,村莊與鈴木忠志的戲劇王國早已融合在一起,成為各國戲劇愛好者的“朝圣地”,人們看到這里一年一度的國際戲劇節(jié),看到以傳統(tǒng)日本合掌屋改建而成的劇場,以及以利賀村的山與云、云與水為背景的露天表演——這就是鈴木忠志遷至此地的原因嗎?
這只是結(jié)果。其因還是在于他對生命、對世界的認(rèn)識。“人生不是精細(xì)計算與預(yù)設(shè)好的,而是要不斷面對各種偶然、不斷做出選擇。人們在面對偶然性時往往是抗拒的,加上很多時候偶然性又是負(fù)面的。對我來說,不是想盡辦法排除偶然性,而是去彈性地面對它——這就是生命力!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缺少這樣的生命力,因為他們生活在人工的盡可能避免偶然性的環(huán)境里。”
偶然性意味著變數(shù),意味著不可預(yù)期、不可控制。在生活中每一個瞬間、每一次偶然事件前,以開放、新鮮的心態(tài)面對,對鈴木忠志來說,正是生命的魅力與寶貴之處。他最喜歡的詞就是“初心生涯”。最能磨礪自己以初心面對生命的,莫過于充滿變數(shù)的大自然。利賀村因其地理特點,頗擅長表現(xiàn)大自然善變的這一特質(zhì)。遷至這里,鈴木忠志把自己和劇團(tuán)放置在最不可抗的大自然的偶然性中,推至極限,以此試探、打磨、激發(fā)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能量與應(yīng)對性。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他的劇團(tuán)里,每個人不僅是演員,還是炊事員、燈光師、搬運(yùn)工,為什么鈴木忠志也會下田割稻、上山采集草藥換取日常費(fèi)用……與其說大家選擇了遠(yuǎn)離都市潛心創(chuàng)作,不如說選擇了這樣的生活方式、這樣一種面對生命的態(tài)度。
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以戲劇家身份為世人所知的鈴木忠志,反而說自己并不是在做戲。是的,他傾其大半生,都是在以戲劇為媒介,向世人傳達(dá)他對生命的認(rèn)知,對生活的認(rèn)知。從這一角度來說,鈴木忠志對于人們的意義,不僅僅是劇場。
網(wǎng)友評論
專 題




網(wǎng)上期刊社


博 客


網(wǎng)絡(luò)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