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wǎng)>>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格非 創(chuàng)造一個故事里的世界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10月11日10:05 來源:天津日報隱匿在喧囂時代背后的作家

9月23日晚,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在京頒獎。格非、徐則臣、黃傳會、大解、劉亮程、孟繁華、趙振江代表獲獎作家發(fā)表獲獎感言。格非的獲獎感言,將曹雪芹和魯迅分別稱作中國古代文學和近現(xiàn)代文學的制高點,他說:“仰望這兩個高度,寫作者還需努力。”
格非的獲獎作品是中篇小說《隱身衣》,之前,這篇小說還獲得了2014年老舍文學獎。
《隱身衣》以格非的朋友老余為原型創(chuàng)作。老余是膽機(電子管發(fā)燒音響器材)愛好者,沒受過什么正規(guī)教育,按他并不因境遇窘困而改變獨特的人生信念,最終成了北京城聞名遐邇的“膽機之王”。
在這個時代,一個寫作者又何嘗不需要如此的堅持?格非不是流行作家,他的作品和他本人與時代的趣味有著鮮明的對立,他的寫作一直保持著特殊的文學氣息。
格非早期以先鋒小說知名,他與余華、蘇童、北村等一起,有意避開紛繁復雜的現(xiàn)實生活,而進入對文本的探索。他擅長在小說中制造謎題,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青春時代的懷舊情愫構成了他主要的抒情要素,而在《隱身衣》中,這種懷舊情愫變成更為宏大的感情。
曾兩次采訪格非,第一次是在銀川的全國書市,第二次是今年的上海書展。兩次采訪時隔兩年,格非的白發(fā)似乎又多了一些。今年他整整50歲,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終還是那個上世紀80年代文學潮流中走在最前面的先鋒。他說話的語速很快,邏輯縝密,出口成章,但從他的言談中很難捕捉到和俗世有關的只言片語。他以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與日常瑣事保持了應有距離。其實,這恰恰是一個作家應該具有的對生活的“警惕”。
格非說自己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人,確實不喜與人交往,能有個安靜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但他也有自己喜歡的生活。他在大學里做了二十年的教書匠,他喜歡音樂,家中有一整面墻的唱片,在《隱身衣》中他把自己對音樂、對音樂器材的獨特知識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他喜歡電影,欣賞費穆的《小城之春》和崔嵬的《小兵張嘎》;他喜歡圍棋,一心盼著自己喜愛的馬曉春九段能經(jīng)常贏棋。
除了這一切,格非最喜歡的還是思考。他認為,從根本上說,文學家和哲學家一樣,因為他們一定會發(fā)表對世界的洞見,發(fā)表他們的看法。只不過哲學家使用的是邏輯性的、陳述性的方法;文學家是通過打比方、講故事,通過陳述具體的形象來展現(xiàn)這種意味。“如果你更善于形象思維,你可能會成為一個文學家;你喜歡思辨,你可能會像尼采那樣通過思辨來思考問題。”格非選擇了文學,他認為好的文學一定有陌生化的效果,“如果文學不能超出我們的預想、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完全一致,那就完全不需要文學了。”所以,讀他的小說你會發(fā)現(xiàn),你會隨著閱讀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謎一般的空間,在這喧囂的時代,他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故事里的世界。
格非口述
80年代的作家有一種共同體般的親密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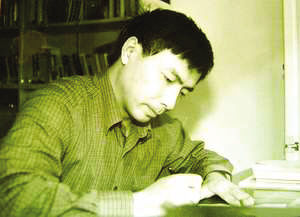
1986年,中國作協(xié)邀請我去青島參加一個筆會。在筆會上我遇到了多多、北島等大師級的詩人、作家。我跟他們的友誼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我見到了我的一個好朋友北村,我們那時候還很年輕,北村比我還小一歲。年紀大的作家們都在一起開會,不帶我們玩兒,我們很孤獨。跟我們一樣大的還有遲子建,但她好像也不太愿意跟我們玩兒。所以我記得有好幾天,我和北村都在討論殘雪的小說,她的作品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我對上世紀80年代還有一個重要感受,就是作家彼此聯(lián)絡很多,誰有了好書趕緊向朋友推薦,如果一個人買到一本很難買到的書,這本書就會以郵寄的方式在作家之間流傳。我記得當時在上海碰到過一件事情,有人帶來一本安德烈·紀德臺灣版的散文集,這本書很珍貴,但第二天那個人要回沈陽,六七個人都想看這本書,所以分給每個人看書的時間只有兩三個小時,必須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把書看完。那個時代就是這么一種氛圍,有一種共同體的親密感。這是我們今天應該反省的地方。
上世紀80年代,各種新思潮風起云涌,拿國內文壇來說,每隔一兩個月的時間,就會發(fā)生“重大事件”。所以你去看80年代的文學編年,你會發(fā)現(xiàn),那是一個非常活躍的時期。我自己有幸經(jīng)歷了那個時期,今天想起來,覺得非常充實。現(xiàn)在我每次和余華、馬原他們見面,一起聊天的時候就會聊到那個時候。所以80年代在某種意義上是很值得懷念的。
那時候我在華東師大,很多年輕的作家朋友在我們學校定期聚會,討論文學,討論各自的作品。除了文學氛圍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是,那個時代評論家跟作家之間形成了很好的互動,一個作品剛剛發(fā)表,就會有很多評論家去解讀、批評。評論家、讀者在批評作家的時候不留情面,作家同行之間批評作品也不留情面,大家用不著顧忌說好話。
大家知道,今天這個風氣已經(jīng)變得很讓人難受了。今天在正式的場合朋友之間不能說壞話,因為可能對別人的市場有影響,作家之間都諱莫如深,都比較謹慎。甚至作家私下見面,有的時候也不太敢交流對作品的意見。如果要我來回答今天文學的氛圍和80年代有什么不同,我覺得我們今天受商業(yè)化的控制越來越強。所以我希望能夠有更好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有更好的年輕作家能夠出現(xiàn),形成非常好的、良性的互動。
名人訪談
格非 創(chuàng)造一個故事里的世界

本報記者 何玉新
格非,原名劉勇,1964年8月生,江蘇丹徒人。1981年入讀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現(xiàn)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講寫作、小說敘事學、伯格曼與歐洲電影等課程。代表作《迷舟》《褐色鳥群》《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隱身衣》等。
回歸古典,仍是先鋒
記者:在上世紀80年代您是中國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到后來有人說先鋒文學的時代已經(jīng)結束了,最近這兩年因為馬原復出,又有人說先鋒文學復活了,這種變化是否會影響到您?
格非:馬原也好,余華也好,我也好,我們都是曾經(jīng)的先鋒派。但是我在我的小說集《隱身衣》的序言中講,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比較不幸,因為中國發(fā)生巨大的變革,在這樣的社會里,一個作家不變化是不可能的。文學需要不斷變化,那么這個變化是不是先鋒派所能概括的,我表示懷疑。有人說先鋒派已經(jīng)死掉了,我覺得這個說法也挺好,不死掉怎么會有新的先鋒出現(xiàn)呢?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過分強調先鋒派的復活。
記者:您過去的小說,比如《褐色鳥群》和《迷舟》,有很多實驗性的東西,后來的作品像“江南三部曲”相對來講接近于古典主義,請您談談這種轉變。
格非:我覺得一個作家應該多一些筆墨,一個作家只有一套文字是不對的,需要多準備幾套,到了一定階段以后,這幾個方面可以互相補充。一個作家的文字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鍛煉,我的基本看法是,真正有自己語言特色的作家其實很少,我這話說得很苛刻。但你放眼去看,真正有自己語言特色的作家,沒幾個。這是一個作家畢生的追求,文字要把非常準確的意蘊、那種微妙的東西傳達出來,這是文學最重要的功夫。有些作家大的東西能傳達,小的東西傳達不了。我也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在語言上有所變化。我的方法比較保守,我覺得變化不要太大,不要徹底把自己推翻,重新來一種語言。我不會這么做。每一部小說都有一些變化,集小的變化成大的變化,若干年以后你可能發(fā)現(xiàn),你的文字已經(jīng)變了。
我跟學生說,語言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學生回答,準確。我又問他們,語言的最高要求是什么,學生說不知道,我告訴他們,還是準確。這兩個“準確”可能不一樣,最低要求的“準確”可能是把一個事件交代完整,人物各安其分;最高境界的“準確”,那種細微之處,微妙的地方可能是毫厘之間的東西,稍微過頭一點兒,那個文字就不能看了。特別考驗你的文字功力。
記者:您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譯到國外,但您的小說語言可以說是唯美的、古典的,這種中國式的語言,在翻譯上會不會有很大的障礙?
格非:我經(jīng)常舉的一個例子,“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中國人讀非常有味道,英文怎么翻?完全沒辦法。這是文學里非常大的遺憾。國際上有一種說法,昆德拉式的寫作,他要表達的意思非常清晰,句子也比較明白,比較短,翻譯的時候比較好辦。最難翻的可能是張愛玲的作品,她的作品好的地方在于味道,味道一旦失去,翻成英文可能一塌糊涂。所以我們對于自己的作品翻譯成外國文字,或者我們閱讀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時,都會有一些寬容。我在讀外國作品之前,我可能會想這是哪個國家作家的作品,是誰翻譯的,我對他們信不信任,作家都有這個習慣,首先會問這個翻譯家靠不靠得住,如果靠不住,就不讀了。
作家要適應市場,也要有所反思
記者:現(xiàn)在這個時代越來越市場化,做什么事情都在考慮受眾,在寫作時您會考慮到讀者閱讀的感受嗎?
格非:對我來講,真正的讀者我可能認識的很少。讀者在哪兒?我是為虛幻的讀者寫作。比如說,我的書在一千年、兩千年以后還有讀者的話,這些讀者我不認識,但是我還是會為他們寫作。我寫作的時候可能會想到跟兩百年以后的讀者較量,我會思考,兩百年以后的人讀我的書的時候會不會明白我的書?
我的讀者有兩種,一種讀者對我語言上的變化可能不太高興;也有讀者認為我在80年代的作品不能看,現(xiàn)在的作品更好。我覺得讀者在解讀方面有各自的自由。不管怎么樣,我的看法是這樣,一個人在35歲以后會發(fā)生重大變化。就是說,我原來不太喜歡的東西,突然喜歡了。我35歲以后對詩意、浪漫有一點排斥。不是完全排斥,而是我已經(jīng)接受不了那種不著邊際的浪漫了。那么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也許有一個原因,80年代我讀現(xiàn)代主義作品比較多,30歲以后開始重新讀經(jīng)典,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福樓拜這些作家的作品,我相信這種閱讀對我會有所影響。作家不能裝,假如說我已經(jīng)出現(xiàn)變化了,我就不能堅持認為我以前的想法是對的,我在創(chuàng)作起來也只能適應這個變化。
記者:您會重讀自己的作品嗎?
格非:對于讀者來說,讀一本書,都希望把這個書記住,尤其是好書;可是對作家來講,寫完之后最大的愿望是把這個書忘掉。因為如果不忘掉的話,就沒辦法展開新的工作。所以多年來我也形成了一個習慣,就是我很少重讀自己的作品。把一個作品寫完,就好像把一個負擔卸掉,這個時候你就覺得天空突然變得很清新,所有的工作都很新鮮,我就開始積累這種新鮮感,當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會突然出現(xiàn)想寫小說的愿望。
記者:您的小說里有沒有自己生活的呈現(xiàn)?
格非:有,但我要告訴你的是,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最痛苦的就是既要把自己的痕跡放進去,同時也要抹掉,讓它變成另外的東西,這是創(chuàng)作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你如果在我的小說里發(fā)現(xiàn)哪些東西是我個人的經(jīng)驗,那我覺得你就是很了不起的讀者,因為這種發(fā)現(xiàn)需要很多層次的轉換。
一個記者描述一個東西,記錄下來就行了;但作家不是,作家是看在眼里,暫時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他會把這個經(jīng)驗積累在大腦里,到寫作的時候要反芻——就像牛吃草一樣,牛吃了之后吐出來的不是草——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反芻,反芻以后才能形成別的東西,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常識。所以我覺得毫無疑問,我的小說寫的都是我自己的經(jīng)驗,沒有我體會之外的東西。但這個經(jīng)驗也不全是我自己經(jīng)歷的,也包括很多這個世界其他的信息,這個過程比較復雜。比如我讀過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列夫·托爾斯泰,我也需要和這些人對話。比方說,我看到他們表達孤獨的主題,假如換成我,我要怎么表達?他們表達過荒謬性的主題,換成我,我怎么表達?這就是對話關系,可以運用到寫作中。
對年輕作家要寬容和鼓勵
記者:現(xiàn)在大家都在玩朋友圈,您對文學的圈子怎么看?您這一代作家會和“80后”“90后”作家交往嗎?
格非:在小說界,尤其是最近這30年以來,大家的代際劃分還是比較嚴格的。“80后”“90后”的作家我也認識,其中有一些是我的朋友,但很少來往,大家很少在一起談事。我也不知道小說界這種“規(guī)矩”是怎么形成的,我們的上一代——馬原、韓少功、莫言、史鐵生,我們大家能夠坦誠相見,他們也很樂意提攜我們,很少有前輩作家說年輕人寫得不行。包括王蒙,他對很多年輕人不遺余力地贊揚。等我們“60后”這代人變成白發(fā)蒼蒼像我這樣,我們可能也從前輩的做法里吸取到一定的東西,所以我們對年輕作家雖然有的時候也不是很滿意,也會有些意見,但總覺得人家剛剛開始寫作,對他們應該寬容。我們跟“80后”“90后”作家彼此之間相敬如賓,都尊重對方的創(chuàng)作,大家也去彼此了解,但是很少對同行的作品進行指責,所以大家相處還算是比較愉快。其實一個時代不可能只出一兩個好作家,往往是會出一大堆作家,你看拉丁美洲、歐洲的例子都是這樣。我很希望我年輕的同行能寫出非常好的作品,這樣整個中國的文化水平才能提高。
記者: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包括有些“90后”網(wǎng)絡作家,寫作時喜歡用一些網(wǎng)絡語言,您怎么看網(wǎng)絡語言?
格非:文學語言有時會被大眾語言借用,尤其是現(xiàn)在這樣一個傳媒發(fā)達的時代,文學語言跟大眾語言之間的交互作用越來越明顯。一個作家很難不受大眾語言影響,但是我平時上課也會提醒學生要注重表達的效果,要明白自己想表達的東西是什么,這時候你使用什么樣的語言方式我覺得非常關鍵。一個作家在語言上要保持足夠的警惕,要知道哪些語言被污染了,哪些語言不能充分表達作者的意圖。對一個作家來講,對語言的考慮永遠是要擺在第一位的。我以前的寫作老師,華東師大的葉百豐老師有句名言:“作為文學系的教學老師,對年輕人一定要寬容,一定要鼓勵他們。”這也是我做老師多年的習慣,我從來不在課堂上批評任何一個學生的作文寫得不好,如果你在課堂上批評一個學生的作文,這個學生一輩子都會受到打擊,會永遠忘不掉。你怎么知道人家若干年以后不會成熟?
記者:您一直在大學教書,很多人都會對一位著名作家的課程產(chǎn)生興趣,能不能談談您講課的風格?
格非:我上課從來不點名。有的人從很遠的地方到北京游學。有一個學生在我的班上聽課,突然問了一個問題,我說你是哪兒的?他說是渤海大學的,我說你怎么跑到這來了?他說他已經(jīng)聽了很久了。社會上有很多人到學校來聽我講課,教務處希望他們登記,我不知道為什么要登記。相對來說我的課比較放松。學生可以隨時打斷我的話,跟我討論。不過現(xiàn)在學生膽子還是很小的。我也不重視考試,一篇文章也好,寫兩個題目也好,怎么能考出一個人的水平?很難。我基本的方法就是讓學生交論文,可以花時間準備,大家都一樣公平。你花的時間多,你的積累好,知識全面,我給的分數(shù)就高。
網(wǎng)友評論
專 題




網(wǎng)上期刊社


博 客


網(wǎng)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