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關于《日頭》和“農民三部曲”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9月15日09:00 來源:河北日報 張繼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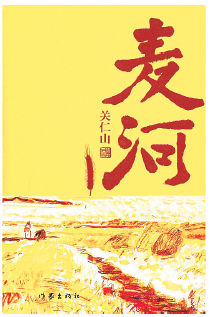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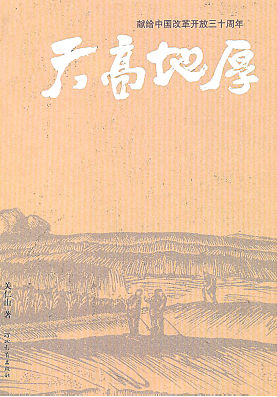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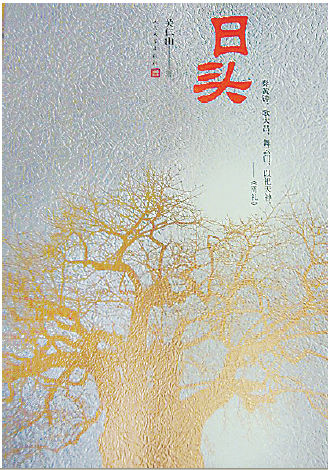
近日,省作協主席、著名作家關仁山的長篇小說《日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并于8月27日在第21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舉行新書首發式。作為關仁山“農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該書以現代中國北方農村為背景,對當下中國農民的出路、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和精神困境進行了深度探尋和思考。有學者認為,該書是一部深刻反映農村變革的長篇力作,它將傳統寫實與鄉村魔幻巧妙融合,書寫了傳統農耕文明逐漸瓦解的過程和新文明建構的艱難,關注和書寫了改革開放中的鄉土中國,富有歷史感和思想的深刻性。日前,本報記者在京與關仁山就《日頭》及其“農民三部曲”展開了一場對話。
《麥河》落選茅盾文學獎
記者:2011年夏,《麥河》曾經參與當年的茅盾文學獎評選,雖然順利入圍前十名,但最終還是以微弱劣勢與茅獎失之交臂。請問,這種評選結果,是否打擾了您的寫作心態與創作方向?此后,您如何安排自身的文學創作呢?
關仁山:這是一個敏感話題,還應該坦誠面對。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作品獲大獎,但是,評獎就像體育比賽,注定有人得冠軍,有人被淘汰,而且原因很復雜,作家不能為了獎而創作,這涉及寫作“為了誰”的問題。我就想,永生永世為那些土地上勞動的農民寫作,盡管他們不買我的書。可是,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聯播《天高地厚》時,收到貴州農民從田間地頭寄來的鼓勵信,這種獎賞更令人欣慰。那年《麥河》落選,我覺得,還是作品寫得不夠好。我馬上調整好心態,繼續寫《日頭》的創作大綱,絲毫沒有影響我的情緒,我以旺盛的精力,創作完成了“農民三部曲”的第三部《日頭》。
記者:作為“農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日頭》這部小說對《麥河》有怎樣的參照和突破?在讀者閱讀方面抱有哪些期待?同時,您又遇到了哪些美中不足的細節呢?
關仁山:說到《麥河》,它真是這部《日頭》的參照。一個作家的創作,無論是廣度和深度上,還是藝術創新上,都必須對上一部作品有所突破,否則就沒有寫作的意義。《麥河》是以一個唱“樂亭大鼓”的盲人視角寫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重點寫了今天的土地流轉。土地是小說的靈魂。《日頭》選擇了兩個人交叉敘述,小說中有兩個“我”,即兩個敘述人,一個是敲鐘人老軫頭,一個是天上的毛嘎子。兩種語氣敘述,前者在地上客觀參與,一個在天空抒情議論,這肯定是一個挑戰。其難度是實和虛的處理,弄不好會讓讀者以為是兩部小說,產生割裂感,無法有機地成為一體,成為故弄玄虛的敗筆。毛嘎子被賦予了一個特殊能力,他飛回村里,只能落在樹林里的一棵菩提樹上,老軫頭與毛嘎子之間能夠對話,智者的對話,眾人聽不見,這讓小說產生了有趣的形式感,也讓哲理思考自然呈現。
因為老軫頭是一個老農民的敘述,必然口語化,本土化,他親歷日頭村的變遷,一方面是權桑麻的親家,一方面又與金沐灶有著特殊關系,可以說是“準岳父”。他是敲鐘人,身份決定了故事的傳奇性和野逸風格。毛嘎子的語調優美抒情,長長的句式,讓其富有哲思和美感。因為我們通常把精神和心靈的愉悅稱為美感。有了這樣的審美目標,這個天上的敘述只能是精神或靈魂敘述了。即便是曇花一現的幻影,也要出現生命美感體驗,那是憂患之美,純潔和高尚之美。描述的故事不再是目的,他只是借助對故鄉的懷念和質疑,對人類的生存發問,是想讓作品來抒發人類的共同理想和心聲,蘊含其中的古怪的激情和精神疑難,讓讀者體悟鮮活澎湃的生命感。毛嘎子還有一些特異功能,他有在天上的云頂,根據星宿的閃光給人解夢的功能。實際上給予了他全知全能的視角,對老軫頭講述故事的局限做了補充。
當然,這部作品也難免美中不足,就是想象力沒有盡情發揮,毛嘎子應該思考人類的命運。
記者:您的“農民三部曲”,依次包括《天高地厚》《麥河》《日頭》。請問這三部長篇小說在藝術題材和小說創作上,具備哪些異同之處?在具體的創作當中,您碰到了哪些較難解決的問題,又是如何解決的?
關仁山:我創作《九月還鄉》《大雪無鄉》等作品時,對農村安撫靈魂的道路描述是單向的,在《天高地厚》這部小說中,開始追問農民的出路在哪里?但不能全景,難以壯闊,叫人不滿足。后來,我把敘事放在盡量宏大的背景上,開始了多向度的寫作,開始更為復雜、更為深入、更為超拔地講述冀東平原的動人故事。“農民三部曲”中,每一部都有改變。《天高地厚》生活氣息濃厚,寫得比較瓷實,缺少一些飛翔的東西;《麥河》就注意到了這些問題,有了一些變化,以一只鷹的兩次蛻變為隱喻,形而上的思考多了一些;《日頭》更注重虛實結合,魔幻的東西更多,虛幻的東西和哲理意味更足一些。
《日頭》是一座“分水嶺”
記者:我個人認為,《日頭》是您小說創作的“分水嶺”。所謂“分水嶺”,就是在《天高地厚》和《麥河》之間發生了重大變化。
關仁山:《日頭》是我小說創作的“分水嶺”,這個提法很新鮮。我想,如果說《日頭》是我的重要作品更為恰當吧。
有一次,我瀏覽河北作家網,一位朋友給我留言:你的創作不錯了,但還有遺憾,不能總按領導的意思寫,要寫真正的好作品。這個留言給我觸動很深。過去歌頌土地多了一些,這一篇再也不能與農民的苦難擦肩而過了,要加強批判色彩。換句話說,就是讓自己這部作品能夠遵從內心,遵從藝術,勇于探險。寫農民的書,怎樣才能做得好?有人說,農村小說只有寫得不像農村小說了才有可能出現好小說。《日頭》跳出了農民種地打糧的傳統模式,拋棄了原來用過的精神資源,帶著憂患意識去寫一種新的形態。農民的生活伴隨著苦難和眼淚,小說必然是沉重的。這類小說必須面對沉重的問題和嚴峻現實,所以說,作家必須是勇敢的。對于作家來說,存在的勇氣就是寫作的勇氣,而寫作的勇氣來自內心的強大。這對我是個嚴峻的考驗。我在寫提綱階段,不斷對自己說:這是“農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書,要面對良心說真話,以良心的名義。所以,在風格上就尖銳一些,大膽地探索一些問題,寫出時代的漩渦,寫出新農民的精神裂變。其實,小說解決不了所有的精神問題,但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態,代表時代的良心。我想以此引起社會的注意,如果真正為中國農民著想,就應該認真地去考慮解決這些問題。即使一時還不能做到位,也要將此作為長遠目標來努力。以此看來,說《日頭》是我小說創作“分水嶺”也有道理。我以后的創作,可能會在精神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遠一些。
記者:創作《日頭》這部小說前后耗費了您多長的時間?其間寫作狀態如何?在藝術上的探索表現在什么地方?
關仁山:這部小說從搜集素材開始,到構思,到寫作初稿,三遍大改,共用了四年多的時間。寫作過程很痛苦,其間,確實出現過比較理想的寫作狀態。比如,故事的傳奇性,人攪著事,事推著人,農民在生活中探索性地往前走,這本身是故事,作品有了逼真的寫實,這是不夠的,作家要超越現實。顯然,這需要作家的想象力,將現實打碎再加以重塑。我想應該在隱喻和象征中建構傳奇。我想在故事和人物身上抹上一層傳奇色彩,讓他們部分地異于常人,異于常理。然后又在玄幻、詭秘和神奇中回歸常人,回歸常理。靠什么?魔幻是我所偏愛的手段之一。一提到魔幻,我們往往就想到西方的魔幻現實主義,特別是想到《百年孤獨》,但是,我所要做的是讓中國式的魔幻自然地走進作品。從《天高地厚》的蝙蝠開始,到《麥河》中的盲人與鬼魂對話,再到《日頭》里神話傳說中的紅嘴烏鴉和古槐流血,這些都是冀東平原的民間傳說。特別是紅嘴烏鴉,我在遷西的景忠山上親眼見到過。
好的小說家除寫作技巧之外,還要學很多東西,比如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民謠和民俗等,這對豐富小說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很重要。僅有傳說還不夠,一部厚重的作品必須要有文化的提升。小說的文化氣息,需要“國學”根底作支撐,我去北大聽過國學老師講課,還學習過基督教的知識。當然,文學作品表現的文化不能單一,應讓鄉村政治文化、倫理文化、自然文化、神秘文化等交織在一起。
記者:這個話題讓我想到文學的多面性和豐富性。與國外的作家作品相比,中國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存在一些明顯的“短板”,比如您剛才提到的文化意識缺乏的問題。那么,對于中國的當代作家來說,究竟應該怎樣彌補文史缺憾,如何發揮傳統文化的優勢投入到創作之中呢?
關仁山:好小說應該是寫文化。說到文化,我自然先想到燕趙文化,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一脈。
對于文化,樂觀與悲觀,都不是簡單的判斷。面對鄉村文化的崩潰,金沐灶從藥王廟的道士杜伯儒那里接受了道家文化,但是,刻骨銘心刻在他心底的還是佛教文化。他母親信奉佛教,他的父親和爺爺,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者,但是他父親卻死在天啟大鐘前,他隨身帶著沾著他父親血液的拓片《金剛經》。佛家講“因果”,金沐灶身上的寬容、大愛得益于佛教更多一些,但是,道家、佛家和儒家以及后來槐兒帶來的《圣經》,幾乎在他身上都有所體現。其實,宗教在入口處雖然是有沖突的,但最后都歸結于善和愛。你感覺金沐灶完美了一些,因為他寄托了我的理想。但是,從故事中還是能看到我對他的不滿,對他還是有批判的。比如,他整合宗教的荒唐,他的某些偏激,他的魯莽,他的絕望。他把軫木撅折一半扔向天空,一半扔到河里,最終悲壯地消失,這些細節說明他絕望中有希望,希望中有向往。他注定是這樣的命運,他的來與他的去,建立在模糊渾濁上,是一種自然生長……
“農民三部曲”與現實主義創作
記者:您的長篇小說以反映中國農村的現實生活為主,身為作家,您為什么像農民種糧一樣,堅守農村題材的寫作?
關仁山:我對中國農村的社會現實有濃厚的興趣。農村題材的經典著作太多了,如《山鄉巨變》《創業史》等,人們很難逾越。不過,如今農村題材小說,明顯衰弱了,就像一穗“老玉米”,很難啃出新意來。我感覺,在這篇變遷的土地上,創作還能夠沖破舊有模式,依靠新鮮的生活,書寫農民的命運史和精神史。對于現實主義,有人強調它的批判功能,批判功能的確很重要,但是批判功能不能簡化生活的復雜性。我們呼喚一種開放式的現實主義,不僅生活氣息濃郁,而且還有概括功能、典型人物塑造、敘事的綜合能力等等。
我在《天高地厚》的后記中說過:農民可以不關心文學,文學萬萬不能不關注農民生存。我寫農民的小說出版后,贏得了一些贊譽,也聽到一些批評。把我劃進寫現實題材的作家,特別是寫當代農民的作家行列,我感覺沒什么不好。
記者:面對現實鄉村,作家很痛苦,原因是找不到新的精神資源,找不到與今天大眾的精神連接點。請問,舊有的傳統經驗還可不可以用?小情感、小圈子是不是可靠?是否會遮蔽更廣闊、更鮮活的世界?
關仁山:文學本身是一種困難的事業。一切都在克服困難、突破自我、突破前人中行進。每個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隨著社會的發展,作家感受生活的方式也會改變。要想全景深入地反映當代生活,蹲在一個地方不可能達到目的,就必須縱橫交織地全面體驗生活。
《日頭》區別于上兩部作品的最重要內容,是兩個人物形象的確立。權桑麻這一形象的意義就在于,他是中國農村基層的真實寫照,這個人物形象本身就涵蓋了中國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史。權桑麻建立的農民帝國,集專制、嚴密、混亂、愚昧、迷信、短視、功利、破壞于一體,他所構建的資本、權力、“土豪”三位一體的利益格局,成為中國社會利益鏈條的象征。權桑麻死了,但他的陰魂不散,他的脊骨保留在兒子權國金身上,也象征著權桑麻專制體制的實質性延續,改革的路任重道遠,中國的現代化既是制度的、也是人的和文化的。農民問題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的。
記者:在農村題材這個范疇,國內作家的整體狀況如何?您如何適應這種“各領風騷”的創作環境?此外,河北作家存在哪些普遍性的不足?
關仁山:農村題材小說劃分已經不科學了,有人說,把農村小說寫成不像農村小說了,那小說就成功了。辯證地看,也有一定道理,現代農業發展目標是減少農民,少數現代農民留在土地搞現代農業。在城鎮化潮流中,大量農民進城,農村小說與城市小說也悄悄融合。中國有寫農村題材小說的重鎮如陜西、山西和山東等,東北的農村題材電視劇深受老百姓喜愛。河北作家寫農村題材的小說,是有現實主義傳統的,我們的作家有生活根基,有些青年作家,已經培育起了藝術創新的自覺,比如,繼“三駕馬車”之后,文壇又涌現出“河北四俠”。
我也有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有時,我懷疑自己寫長篇的能力,這個能力指的是綜合素質,尤其是思想的力量。既然是小說,是寫愛恨情仇的,其情感深度代表作品深度,作品深度靠思想力量。好小說最缺的不是故事,是哲學,是思想,所以必須埋下問題,浮起追問。金沐灶是個民間思想者,借助他對這些問題進行追問,這樣方能帶領讀者去思考。沒有思想的手術刀,哪能剖析農民貧困的根源呢?
記者:如今,您的“農民三部曲”已經出齊,將來您還會繼續關注農民的命運嗎?商品社會對閱讀也有沖擊,農村題材受到青年讀者冷落,此后,您如何規劃安排自身的文學創作呢?作為省作協主席,您認為河北整體的文學創作在全國處于怎樣的地位,目前呈現出哪些特點呢?
關仁山:在剛剛結束的第六屆全國“魯迅文學獎”的評獎中,河北的作家胡學文、張楚和大解獲獎。從這個情況看,河北的創作在全國不弱。但是,我們也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大作力作還不多。河北作協很重視青年作家培養,近幾年每年都舉辦青年作家培訓班,今年還要召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表彰成績突出的十佳青年作家。為青年作家出版叢書,研討他們的新作,河北文學院“合同制作家”向青年作家傾斜。一句話,我們要為青年作家服務,為他們的好作品問世提供脫穎而出的平臺。
多年來,幾代青年讀者一直都非常喜歡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如果我們寫出好作品,青年讀者也會喜歡的。如今,“農民三部曲”已經全部出版了,此后的寫作卻不能停止。我對自己的創作沒有長遠規劃,適合什么就寫什么。是生活感動了我,我才有激情寫作。《日頭》寫完后,農民和土地我還會繼續關注的,還要嘗試寫一些城市生活的小說。
《日頭》節選
關仁山 著
 關仁山
關仁山 仰了臉兒瞅,雪紛紛揚揚。
雪花將古鐘糊住了。古鐘掛在狀元槐,槐枝嘎地響了一聲,不知是鐘太沉,還是雪太厚。老槐樹枯著,竟然沒折,家雀呼啦啦飛了。灰巴巴的槐樹枝,一律快活地動著,彈出雪粉。槐樹下的麥秸垛也氣吹似的脹起來,隱隱有些抖動。
常日溜達的老人和孩子,一個也不見。
雪越下越瘋了,看樣子一時半會兒歇不住。雪和泥攪成一團,踩在腳下,揉搓出干燥的摩擦聲,哧啦哧啦的。路很滑,我走得不緊不慢,卻跌跌撞撞的,只一個孤獨的影了。
我就是會講故事的敲鐘人老軫頭。
我踏雪敲鐘來了。我在槐樹下站了好久,雪粉從枝杈上掉下來,奇怪的是這雪粉竟像烙鐵一樣燙人。
我開始用軫木敲鐘了。
咣!咣!鐘聲跳著,滾著,響遠了。
我叫汪長軫,是一個八十八歲的老人。我須發花白,臉上的褶子很深,牙掉得沒剩幾顆。我穿戴邋遢,卻滿面紅光。到了這把歲數,難免有些怪異,神神道道。我種過莊稼,守過大車店,當過飼養員,殺過豬,宰過羊,賣過雞蛋,還是村里最后一個敲鐘人。在村人的印象里,我老軫頭是和古鐘、槐樹、紅嘴烏鴉、血燕連在一塊兒的。盡管耳朵被鐘聲震木了,我還是樂意敲鐘。鐘聲就是村里的日子。每逢節日,我就敲鐘,要是趕上日月同輝的日子,村里就會出現異象,還得敲鐘警示村人。眼下人人都焦慮,想錢想瘋了,日子難免過得雞飛狗跳。鐘聲能給人警醒,給人安詳。我推著慈悲木開始敲鐘,雙手觸摸慈悲木的一瞬間,手竟有些抖。悠揚的鐘聲在大雪天里響起,順著老街蕩出去,滾過大平原,爬上披霞山,滿世界都是天堂的聲音了。鐘聲的余音,野外都能聽到。隆隆的聲音猶如遙遠的雷鳴,給小村平添了一股浩蕩之氣。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