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劉斯奮:本土化創作也要有不守一隅的文化視野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8月11日10:15 來源:羊城晚報 吳小攀 張甜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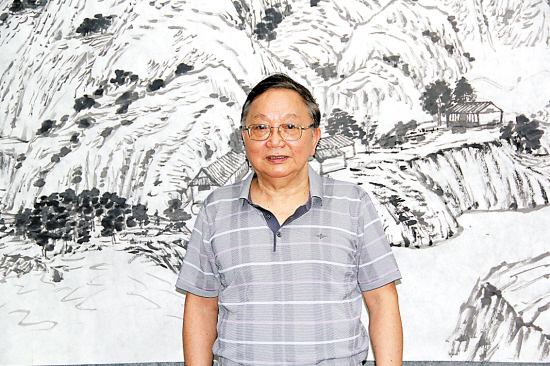 |
| 劉斯奮近照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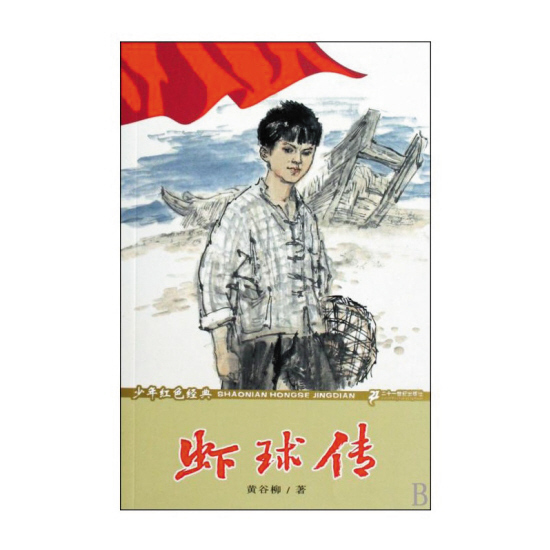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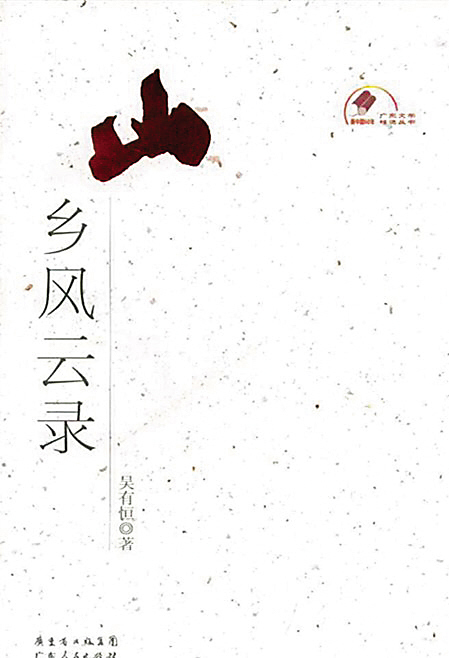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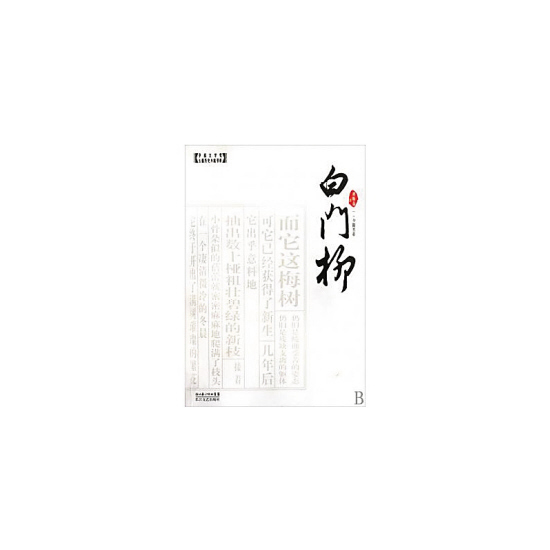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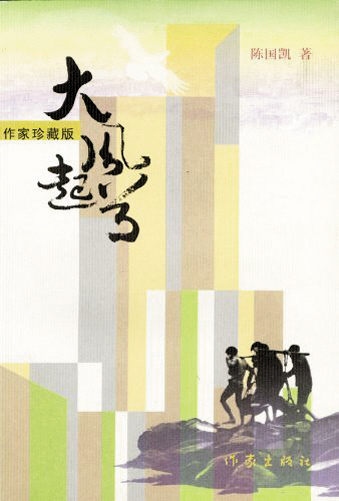 |
□圖/文 羊城晚報記者 吳小攀 實習生 張甜甜
1《白門柳》:
用嶺南精神創作出的江南小說
羊城晚報:您文藝生涯的奠基之作是長篇小說《白門柳》,當時為什么會選擇這么一個非本土的題材來創作?不擔心這樣一個非本土的題材不好把握?
劉斯奮:作為一個廣東人,我對廣東、廣州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我的文化視野從來都沒有局限于廣東,我一向是從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來觀察和思考問題 的。既然我想從自身的修養、積累出發去寫中國的文化,就不能拘泥于廣東;而明清之際的江南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并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要揭示 中國文化在某個歷史發展階段的最新動向,明末清初的江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另外,歷史小說和現實小說不一樣。歷史是已經過去的歲月,時 至今日,可以說江山依舊,但人事早已全非,地形地貌固然需要考察,但當年的人和事則只能憑借歷史資料去想象揣摩,就這一點而言,不論是江南作家還是嶺南作 家其實都是一樣的。當地作家會有地利與人和的優勢,但外地作家卻是旁觀者清,受成見成說影響更少些,創作起來更加自主。
羊城晚報:但畢竟您是廣東人,長期受到嶺南文化的浸染,這對創作這部小說有什么影響?
劉斯奮:嶺南文化的特質據我的總結就是: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因此,我在創作中所恪守的,一是要敢于有所突破。古代的精英知識分子階層,古代 的大思想家,以這些人物作小說的主角,前人似乎未有范本,應該說是一個有相當難度的新嘗試。二是以平視的角度對待這些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把他們作為一個 有血有肉的平常人來探究、來描寫。之所以能夠這樣做,也許都是源于嶺南文化的創新傳統和平等精神。
羊城晚報:《白門柳》寫的是江南題材,有很濃的江南味道,而您是廣東的作家……您認為這部小說是屬于嶺南文學還是江南文學?
劉斯奮:我覺得它屬于中國文學,這是由我的文化視野決定的;或者說,它是用嶺南文化的精神去寫出的一部關于江南的歷史題材的小說。這本身也已經跨越了地域。
2美術創作:
突破嶺南一隅走向全國
羊城晚報:您在美術創作審美上有沒有自己的追求目標?
劉斯奮:這和文學創作類似,還是我對嶺南文化的那三點歸納。我沒有明確的師承,但人人又都是我的老師,也許就是所謂博采眾長,然后自成面目吧!我很強調 走自己的路子。因為在藝術創作中,共性是沒有多少價值的,只有獨一無二的個性才是有價值的。所以我根本不想歸入哪一派,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藝術感覺,努力 把畫畫好,才是最重要的。寫完小說,不想干了,就畫畫,先是畫古代人物,再畫現代人物,現在又畫山水……當然,每樣都有一定的目標和追求。
羊城晚報:加上詩詞、書法創作及文化理論的提出,這種跨界確實可以看成是嶺南文化精神一種影響。
劉斯奮:工業文明之后,從家庭小作坊生產到大工業的流水線生產,這在物質生產上極大滿足了社會對消費的需求,是人類社會一次大飛躍,功不可沒。但嚴格的 專業分工,也對人的精神創造產生負面影響,嚴格的專業分工,壓抑了人的多種潛能的發揮,標準化的大批量生產,則扼殺了精神創造的個性。嶺南文化精神也許有 助于突破這種后現代困境。
羊城晚報:雖然您強調了不守一隅的精神,但在您的這些畫作中還是隱約可以看到嶺南的影子,比如畫中的山水總是溫潤的。
劉斯奮:這只是表象,造成這種面貌也許是我更崇尚中國傳統的審美理想,即含蓄、圓融、內斂。而且,中國傳統的繪畫也傾向于表現人生美好的一面,不像以原 罪、救贖為核心的西方文化那樣直接表現死亡、血腥、戰亂。至于整體畫風,我則是繼承了中國文人畫的寫意傳統,這次到北京中國美術館搞展覽,就有評論家認為 我是最大限度地去西方化,并糾正了嶺南畫風中某些功利和媚俗的偏頗。當然,由于我生長于嶺南,平時所見都是青山綠水,這自然會強有力地影響著我的心境和創 作。不過重要的是同樣是青山綠水,如何畫出自身的個性和特點,畫出自身的文化情懷,而不是盲目的模仿和跟風,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這樣,廣東繪畫才會突破 嶺南一隅的局限,真正走向全國。
3本土性:
廣東文化就是雜交文化
羊城晚報:您怎么看文藝創作過程中對于本土性的強調?
劉斯奮:如果本土性是指題材,特別是現實題材,自然無可厚非。因為一個藝術家,對于生于斯、長于斯這片土地,無疑有著先天的生活優勢,表現起來會更加得 心應手。比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廣東涌現出一批直接反映改革開放的電影、電視劇,像《雅瑪哈魚檔》、《公關小姐》、《外來妹》、《情滿珠江》、《英雄無 悔》、《和平年代》,等等,都曾經引起全國轟動。而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長期生活在廣東,是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不過后來,這種廣 受關注的效應失去了勢頭,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并非不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本土作者的創作觀念未能跟上時代的發展。
事實上,隨著時間 的推移,觀眾和讀者的品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已經不再滿足于對生活作原生態的再現,而是要求從題材、觀念到表現形式都有更大的開拓,更高的提升。而 我們的作者,卻仍舊只滿足于原來的一套,變得止步不前,最終失去觀眾和讀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實上,即使是現在,廣東有很多生活形態、思想觀念,都仍 然是走在全國前列的。問題是我們的文藝家如何使自己對這種現實生活的認識和表現,從原生態的層面上,提升到一種新的審美高度和思想高度,從而給觀眾和讀者 以更深刻的啟迪和更高層次的審美愉悅?而這,實在是當前本土性創作所共同面臨的一大課題。
羊城晚報:您如何看待近些年來廣東所謂新移民作家的現象?
劉斯奮:我從來都不狹隘地強調本土性,廣東文化的本土性從來就不是封閉自守。廣東是歷代移民大量地、不斷地遷入的地區,不同地域的文化在這里“雜交”, 其強大活力也恰恰體現在這里。也許可以說,廣東文化的本土性就是雜交性,也是這個社會開放包容的原因。我注意到一個現象,對嶺南文化感興趣而且去研究的, 大多是來自外省的新移民。作家也是一樣,他們來到廣東,發現這里和家鄉不一樣,馬上引起研究和創作的興趣。有時候本土人習以為常,見慣不怪的生活形態,他 們反而能發現其中的不尋常。這也有點像我寫江南風物時的情況。當然,也不能滿足于浮光掠影,需要真正沉下來,慢慢地去深入琢磨體會,包括廣東的現狀和歷 史。如果說,我作為廣東作家,尚且能寫出《白門柳》,那么對于新移民作家,就沒有理由懷疑他(她)能寫出一部更加出色的關于廣東的作品來。
羊城晚報:如何看待有些評論家呼吁廣州文藝創作要對諸如西關風情的再現?
劉斯奮:廣州西關是一個廣府地區習俗比較集中的地區,加以關注和表現當然有必要。但西關風情涵蓋不了整個嶺南的文化,如果只強調這一點,倒把本土性理解得狹窄了。
本版于7月27日、8月3日相繼推出《廣東女作家為什么那么紅?》、《女作家為廣東文學“熱帶雨林”增添斑斕色彩》策劃專版,引起讀者關注,關于廣東文藝本土創作的討論進一步深入。廣東本土的文藝創作存在什么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為什么一談本土創作就有點尷尬?
除了“時代背景”還要重視地域性
曾大興(廣州大學文學地理學研究中心主任):從小學到大學,老師跟我們講文學作品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在黑板上寫“時代背景”這幾個字,告訴我們這個作 品產生的時代背景,這個作家產生的時代背景。這個確實很重要,但是僅僅這樣還不夠,為什么?因為任何事物都是在時間和空間中形成和發展的,時間和空間是事 物運動的兩種基本形式。而我們過去講文學基本上只有時間這個概念,只講文學的時代性,只講作家、作品的時代背景,這就有很大的片面性。為了還原文學的真 相,我們還應該有空間這個概念,還應該講講作家、作品產生的地理環境。
中國的文學從《詩經》開始就有地域性,尤其是到了當代,文學的地 域色彩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鮮明。我們現在熟悉的當代著名作家莫言,他的創作就以山東高密東北鄉作為根據地。陜西有三個代表性作家,賈平凹、陳忠實、路 遙,這三個人剛好出生在陜西的南部、中部、北部。賈平凹的作品是陜南風格,陳忠實的是關中風格,路遙的是陜北風格。
再往南邊數過來,幾乎每個省都是這樣,往南到廣東,古代作家就不用說了,現代作家有創作了《蝦球轉》的黃谷柳,創作了以廣州西關為背景的《三家巷》的歐陽山,再就是陳殘云,他寫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生活就是以廣州白云區一帶為背景。在年輕的作家當中,梁鳳蓮是一個代表。
陳實(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還有,陳國凱寫特區,呂雷寫新時期的西江流域,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打工文學”,包括鄭小瓊、王十月、謝湘南,等等,這些作家的作品里基本上寫的都是廣東改革開放的生活。
本土文學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
梁鳳蓮(廣州市社科院嶺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在為什么在廣東和廣州一談本土創作、本土特色,好像就有一點尷尬,我們要面對地域特色日漸模糊和融合的 現狀。因為廣州已經成為一個移民城市,匯集在這里的人都帶來了各自的母體文化,各種文化在這里碰撞。真正可以作為創作的旗幟來張揚的地域文化,還需要好好 地去匡正、認定、澄清。就是真正以地域特色作為標識,正視在各種文化匯集、碰撞和變異中,怎么樣繼續保留古老的地方特色魅力?
曾大興: 我認為本土文學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本土文學的題材是本土的,但是它所包含的意義應該是全人類的,也就是說應該具有普遍意義。像莫言他寫的是山東高密東 北鄉的故事,但是他所體現的是整個中國農民半個世紀以來的生活與心路歷程,這就具有普遍意義。沈從文寫湘西,體現的是對單純、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具有普遍 意義;魯迅寫紹興農村,所揭示的是舊中國農村的破敗景象與農民的悲慘命運,也具有普遍意義。題材是局部的、本土的,意義是廣泛的、普遍的,這才是我們所說 的本土文學。如果題材是本土的,意義也是本土的,那就有局限性。
本土文學不僅僅是本土作家創作的,外地作家也參與了本土文學的創作。我 們以中國文學史為例:像蘇軾被貶到惠州來的時候,就寫了許多以嶺南本土為題材的作品。比如《荔枝嘆》:“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 顆,不辭長做嶺南人。”像這樣的作品,你是把它劃到嶺南文學?還是劃到巴蜀文學?韓愈也是這樣,他先被貶到陽山,后來又被貶到潮州,他在這兩個地方都留下 了很多作品,例如他的《山石》,就很有可能寫在陽山這一帶,這就屬于嶺南文學。
本土文學的作者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本地作家,也就是土 生土長的作家,一個是生活在本地的外地作家,像古代有的是被貶謫在這里,有的是被流放在這里;1949年以后,有的是作為干部調配到這里,有的是因為其他 原因短期居住在這里。從外地到嶺南,他是一個客居者,但是他寫的是嶺南題材,那么他的這一部分作品就屬于嶺南文學,也就是本土文學。本土文學不僅僅是本土 作家創作的文學,任何人,只要你熟悉這個地方的生活,你就可以從事本土文學的創作。這樣來看,廣東的作家究竟有多少?我想一定是很可觀的。
一個作家,如果對本土文學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如果他的作品沒有一個地域標記的話,他是很難被人們記住的。自從有諾貝爾文學獎以來,幾乎每一個獲獎者的 頒獎詞,都會強調他卓越地描寫了本民族、本地區、本國人民的生活,也就是說,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當然,在中國,在廣東,也有少數作家不是這樣,寫 了很多,但是沒有任何地域特色。按照地域性文學史的編寫原則,這樣的人是進不了廣東文學史的。
為什么很多廣東作家浮在表面?
梁鳳蓮:為什么很多廣東作家浮在表面,沒有潛進去?目前的一個誤區是,把文化當成一種裝飾、一個單純的背景,或者一個附庸的東西,而不真正去追究為什么 它會對人產生這樣的影響。很多東西在廣東文學創作里還是空缺,這個空缺還導致文學機構長期形成一個模式,就是雇傭軍的模式、空降兵的模式。像亞運會都是請 外援,包括很多粵劇,最搞笑的是也請外地文研所,然后讓我們的粵劇編輯把它補上廣東話,全部置換了,貌合神離,而且根本找不到它的精髓。
對本土文化只有了解才有認識,只有認識才有認同,只有認同才有熱愛,只有熱愛才會共同地建設它、完善它。假如這個鏈條一斷裂的話,很多誤解的東西就會產 生,因為這已經是一個移民世界,每個人帶著不同的文化烙印來這里,你沒有文化認同的話,就必然有道聽途說、忽略放棄,形成種種誤讀,導致現在的困境。
文化認同之外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文化融合,誰融合誰就有話語權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經常用北方的標準,或者用一種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標準來衡量我們,這是歷 史造成的。如果你再用中原唯一尺度的話,我們肯定被邊緣化了。要認識它、了解它、熱愛它,然后要建立自己的評判標準,擁有自己的話語權。
地方文化成熟的標志,唯一的標志就是文化產品的輸出,你真正能通過文化產品輸出去改變別人的價值觀,這才是文化成熟的完全意義。假如政府的倡導,從業者 的覺悟,對文化的熱愛,這三者不能結合的話,我們能出什么?我們就只能出“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不是不好,但是隨著文化的縱深發展,社會往前推 進,這種自愛自戀、風花雪月的東西就很難有什么社會正能量。假如你的書寫只是對你個人的宣泄,你可以在日記上鋪天蓋地,假如作為文學藝術作品發表出來,你 不可避免就要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
本版版圖/東方IC
吳小攀、張甜甜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