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觸摸當下鄉村的“真實體溫”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7月15日09:52 來源:深圳商報 陳亦然作家楊獻平新作《生死故鄉》直面“潰敗的鄉村”
觸摸當下鄉村的“真實體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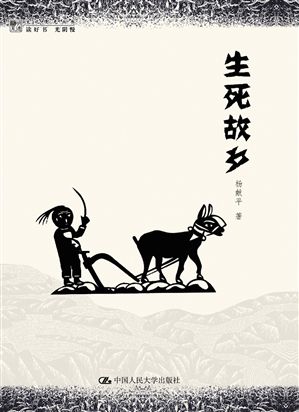 ▲《生死故鄉》楊獻平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5月定價:35.00元
▲《生死故鄉》楊獻平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5月定價:35.00元 ◀生于河北、客居成都的楊獻平,以“不是虛構、也不是紀實”的方式,直面自己曾經生長的土地:南太行山區鄉村。新作《生死故鄉》讓我們得以目擊和見證他新鮮的散文精神與寫作態度。 (受訪者供圖)
◀生于河北、客居成都的楊獻平,以“不是虛構、也不是紀實”的方式,直面自己曾經生長的土地:南太行山區鄉村。新作《生死故鄉》讓我們得以目擊和見證他新鮮的散文精神與寫作態度。 (受訪者供圖)在人到中年的時候,作家楊獻平選擇了與故鄉“握手言和”。
此時,故鄉已是“潰敗的鄉村”,而他卻成為一位“寬容的游子”。生于河北、如今客居成都的楊獻平,以“不是虛構、也不是紀實”的方式,直面自己曾經生長的土地:南太行山區鄉村。放下對故土的偏見,沒有藏掖,沒有偽飾,讓我們得以目擊和見證他新鮮的散文精神與寫作態度。
鄉村人群一方面自然消亡,一方面以各種方式加入到城鎮當中,這種劇變酷烈而深刻,前所未有。作為民族文明和風習的主要沿襲地與文化場域,傳統鄉村正在面臨形式和精神上的雙重崩潰。如何審視當下鄉村現狀及其文學表現,是一個頗具意義的文學和社會的“焦點”。
在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新書《生死故鄉》中,楊獻平以南太行山區鄉村及其人群為主要考察對象,真實而藝術地呈現了十多位具體農民截然不同的奇詭命運和人生遭際。近日,筆者就本書內容、鄉村現狀及當下散文寫作等方面,對楊獻平進行了獨家專訪。
我們時代的“鄉土之根”
《文化廣場》:創作《生死故鄉》的緣起是什么?您在《生死故鄉》的楔子中說,一個南太行,可以輻射到整個中國北方鄉野,您是否期待關照更多?“故鄉”前面加了“生死”二字,有了沉重的意味。
楊獻平:一個人其實關照不了更多,尤其是平民。處在一隅,能夠看到的世界只是它確切的某一處;身在人群,與大地眾生齊平,凌空俯瞰絕對是一種虛假姿態,也不可能真切、全面地觸及。多年前,對地域及其人群的書寫,我也有狹隘、卑小、不值得關切和書寫等疑慮,為此也很苦惱。但慢慢地我發現,大地上的人只是所處方位和環境不同,其命運、生存境遇與精神訴求幾無二致。
隨著老人們的逐漸“與世長辭”,年輕人紛紛進城謀生,鄉村自然淪為“正在消失的人類聚居地”,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及其攜帶的文明不僅在外部逐漸向“廢墟”和“遺跡”行進,接續鄉村文明和傳統的人也幾乎不復存在。目前來看,鄉村的死亡不可避免,傳統鄉野文化和文明的斷裂與再造、新生已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鄉村的“生與死”對于這時代有著“鄉土之根”的這一部分來說,有著文化和精神上的重要影響和意義。
《文化廣場》:《生死故鄉》里,堅韌的生命,卑微的生存,頗具戲劇性。我以為,這里應該是沒有“虛構”的,不知對否?人類自身的幽深、復雜、離奇,是不是比小說更豐富?
楊獻平:任何的想象力都必然以現實存在為依托。《生死故鄉》當中的人及他們的故事、命運,有相當一部分是確有其事,只是在書寫當中,適當加強了矛盾沖突,使其更具有感染力。再者,無論哪種文學體裁,讓人有興致讀下去才是首要的問題。
有批評家說現實生活和匪夷所思的新聞永遠都無法取代文學,這沒錯。但在這個有意思的年代,作家的想象力和講故事能力顯然弱于這個時代的現實。將來則未必。過于強調文學的藝術性或現實生活的力量,都是偏頗的。好的文學,當是從塵埃里來,到云霄上去;從人群中生發,在精神和靈魂生根。時間、自然乃至人類,其存在、變遷本身就是一部奇詭之書。這世上每個具體人的命運,也都是與之相對應和協調的。
現實只會比文字更生猛
《文化廣場》:您的《生死故鄉》,有一種野蠻生長的“原生態”。這種“原生態”的殘酷,破壞了我們想象中的“田園式幻想”,請問這是當下鄉村的“普遍真實”嗎?我們是不是常常錯估當下鄉村的溫度?
楊獻平:田園牧歌式的鄉村書寫流行甚至被捧了很多年,其主要迎合的是城市知識分子及其精神烏托邦。從文學角度說,這沒錯。作家建立的是自己的文學高地。但對于鄉村和農民是不公平的。
不能說所有的中國鄉村都如《生死故鄉》,但至少北方大部分地區如此,甚至比之更“生猛”。《生死故鄉》中的鄉村絕對“普遍真實”,還有比之更慘烈的,我想在下本書中寫出來。以文學的方式還原當下真實的鄉村現狀,讓更多人觸摸當下鄉村的確切“體溫”,雖然與當下時代文化特征相悖,但很有價值。有人參與“合唱”,也要允許有人“跑調”。
《文化廣場》:《生死故鄉》中有大量的筆墨,涉及到“鄉村里的性”,讓人有一種出乎意料的“隨意”。鄉村人對性的態度,折射出了什么?
楊獻平:性是生命源動力。鄉村人直接,崇尚暴力;文化信仰混亂,再加上生存環境及生活質量的普遍低劣,在絕望與痛苦之中,唯一可以讓他們暫時“幸福”的一個是掙到錢,一個就是性。這兩種東西,不僅在城市如是,在鄉村亦然。可以說,性是鄉村人群借以自我安慰,消解苦痛的最有效的生理和精神活動。
我本質上是一個農民
《文化廣場》:您個人的經歷很是傳奇,農民、打工者、軍人、作家,這些轉換中的身份,之于今天的楊獻平,都有什么意義?
楊獻平:農民是根,聯結大地與最低層人群,當然還有鄉村文明及其文化傳統;打工時間很短暫,學過幾個月木匠而已;可忽略不提。軍人血中有鐵,有夢想,是諸多職業中最有使命感與夢想之音的。樸素是生命本身,夢想當中不僅包含個人心性,還有家國情懷。居一隅而望四野,雖一人卻念眾生。這該是一個比較高的境界。
《文化廣場》:20年前,您就曾經用文學的方式,一次次對故鄉南太行及其人群進行書寫。但后來,您表示了不滿意,去除了偏見,從而有了這次全新的書寫。這樣的過程,是不是也伴隨著一位作家的蛻變?
楊獻平:這該是一個促狹到開闊,仇恨到寬容的過程。20年前我以為惡人惡事只有南太行鄉村才有,后來才知道遍及全人類。鄉村生存資源本來匱乏,有些利益沖突也正常。都是為了生存,只要不傷及性命和尊嚴,沒有什么不可以寬容的。這種心態的不斷蛻變,也和年齡與看世界的方式不斷自我矯正有關。
《文化廣場》:寫作者對待故鄉常常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詩意和美化,一種是諱莫如深。而在《生死故鄉》中,卻感覺你與故鄉“握手言和”,直面自己,直面鄉土,沒有藏掖,也沒有偽飾。與故鄉“握手言和”之后,您最大的變化是什么?還會有“變形怪物”之感嗎?
楊獻平:鄉村人爭斗,代價慘重,傷人也傷己。他們也很可憐。理解便會同情,無奈也是悲憫。真實呈現他們的種種行狀,尤其是苦難遭際,有告誡的意思在內,更多的是期望。這也是一種和解方式。對故鄉,我還是愛的。我本質上還是一個農民,雖在外省城市,但心還在鄉野。我想這是我和故鄉最好的一種“關系”和“狀態”。
空谷是最好的去處
《文化廣場》:楊顯惠老師說,讀完《生死故鄉》后,腦海里出現的就是蕭紅的《生死場》、《呼蘭河傳》,稱您這部書寫出了這30年的農村史。您是否無意中,承接了某種文脈?如何看待楊顯惠老師的評價?
楊獻平:苦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生人的一種集體“未完成生命體驗”。《生死故鄉》初稿完成,我發給楊顯惠先生,并替他擬好了一段話。楊老師說他要親自看。兩個月后,他發來一段他自己的話。他這樣評價,我沒想到。欣喜也很忐忑。我的《生死故鄉》確實寫了近30年來的鄉村人群命運變遷。但距離楊顯惠老師的評價,還是有距離的。他無意中給我鼓勵,也給了我今后的動力。
《文化廣場》:您在序的最后,對自己的文字是否被人接受,似乎有一些疑慮,但也灑脫。您說:“不管這些文字是不是有著與其他文字不同的面目和內質,也不管這些文字會不會得到更多的同感和好評,寫和還能寫下去,對我來說,就是勝利。”為何會有這樣的疑慮,這樣的灑脫?
楊獻平:我們這個時代的多數人需要的是“物質上的成功”、“迷惘、苦累中的自我娛樂和情感寄寓”。鄉村書寫基本上淡出文學主流。像《生死故鄉》這樣一部底層苦難書、鄉村人物傳,受關注的可能性不大。沒人愿意再在紙上獲取更為沉重的“他者”經驗。另外,不以寫作為生,就不必顧慮太多。當一個人不需要喝彩的時候,空谷是最好的去處。
《文化廣場》:當下的散文寫作,呈現著一種什么樣的生態,是否也存在一些流弊?您認為文學最打動人心的應該是什么?
楊獻平:當下的散文狀態可能是30年來最好的。流弊一是歷史題材寫作沒有生命溫度,缺乏精神諧振;二是城市題材強調個人精神和思想異化、生活的新鮮感與個人現實主義;三是鄉村題材寫作過分詩意、美化懷舊色彩偏重;四是坊間影碟解讀及讀書隨筆缺乏人間煙火氣息,偏執偏頗。五是散文批評跟風習氣濃郁,缺乏全面精準的論說與發現。文學最打動人心的,是讓人從中看到自己的“內心結構”、“情感紋理”和“精神質地”。 (深圳商報特約撰稿 陳亦然)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