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海飛:誤打誤撞進入文學圈的異類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6月26日09:47 來源:中華讀書報 舒晉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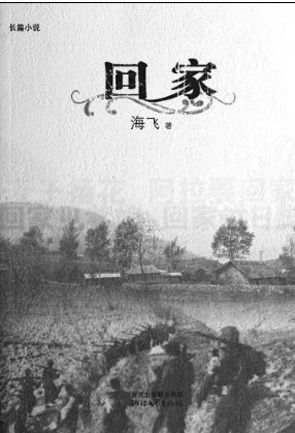 《回家》,海飛著,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32.00元
《回家》,海飛著,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32.00元我對我私下里猜度的,我所幻想的人生充滿憧憬,并且樂此不疲地生活在這種虛構的場景里。我一直以為《向延安》寫的是蒼涼上海的一場老夢,而《回家》寫的是一場江南的令人憂傷的黑白默片。
他曾經是諸暨化肥廠造氣車間一名晃來蕩去的工人。下班之后看錄像、打牌、談戀愛以及無所事事地發呆。
他的職業是拉煤渣的工人,此前還當過臨時工,擺過小攤,當過文書和記者……除了寫作以外,他的職業五花八門。但是這些并不妨礙他寫作。他買來了方格稿子,抄寫自以為是小說的文字,然后虔誠地投給雜志社。也許他僅僅是想讓工友們知道:我不僅拉煤力氣很大 ,寫文章也是可以的,應該屬于是文武雙全型人才。他覺得自己懵里懵懂成為寫作中的一員,就像是誤長在草地上的一株紫云英。
終于有一天,《旗袍》火了,大家才開始注意到,寫下這部作品的年輕人,他的名字叫海飛。當他的身上云集關注的目光時,他卻說,他只是選擇了一條小路。當別人向往飛翔時,他在這小路上慢慢走,一直到日落西山。這是多么從容而美好的事情!
近日,海飛又一部作品《回家》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他沒寫戰爭英雄,而是聚焦了傷兵和逃兵的故事。無論是傷兵還是逃兵,他們都想回家。可是在那個年代里,他們一直都不能回家。最后他們再次成為真正的戰士,成為這個國家泥土的一部分,芬芳的一部分,野草的一部分。
讀書報:《回家》讀完,感覺很抒情、很溫情。沒有描寫主戰場的戰爭,而是巧妙地以“回家”為主線,反思戰爭,反觀人性的善與惡。這是作品的獨特,也是一種“討巧”。這么構思,是最初就確定的嗎?是否也是揚長避短?
海飛:我一直以為,高大全的形象我們已經在文藝作品中見得太多了,但是我們卻很少見到活生生的“人”。在開始構思《回家》的時候,我查閱了好多抗戰資料,知道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戰爭年代的故事。所以我愿意我小說的主人公是鐵匠、裁縫、船夫、菜農……這些人都可以在我生活過的村莊丹桂房見到。你有一個親人在當兵,在抗戰前線,我覺得他最大的可能是士兵,或者是排長,而不太會是將軍。所以我要寫的是士兵,他們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親人,他們一直想要回家。我覺得這已經不是一種“討巧”,其實這是一種陳舊。在反映二戰的一些經典文藝作品中,經常會出現“回家”這一主題。
讀書報:在70后作家群體中,戰爭題材(估且暫這么定位)一直是個短板。但是你的很多作品,是一個有力的補充。在駕馭這樣的題材時,你覺得哪些方面對自己是較大的挑戰?如何克服?從《旗袍》到《回家》,你為什么會對這類題材感興趣?
海飛:《旗袍》是電視劇,而《向延安》才是一個原創的長篇小說。我對那個時期十分感興趣,我覺得那是一個產生故事的年代,山水清明,地氣升騰,民國年間的人們行進在那時候的街道和阡陌。那時候盛產戰爭、紛亂、顛沛流離,也生長著稻米、愛情、歌舞升平和恩怨情仇。其實在小說創作中,我一直時刻提醒自己,我寫的是人,不是戰爭,不是諜戰。既然是寫人,那么就需要真實地讓人活在文字中,所有的背景,道具,包括我寫到的戰爭,只不過是“人”活起來所需要的舞臺,或者說水、空氣和養份。我對我私下里猜度的,我所幻想的人生充滿憧憬,并且樂此不疲地生活在這種虛構的場景里。我一直以為《向延安》寫的是蒼涼上海的一場老夢,而《回家》寫的是一場江南的令人憂傷的黑白默片。我想我會繼續致力于這樣的寫作,致力于向讀者提供這樣的文本,致力于讓那個年代的人事,以新鮮荔枝一樣的形式,充滿植物氣息地呈現在讀者目光所及的枝頭。
讀書報:不論是國民黨、新四軍還是日本戰俘,無論他們的政治立場或對戰爭的態度怎樣不同,他們都期待著“回家”。這些人物,有多少是有原型的?是怎樣的契機觸發你寫這樣一部作品?
海飛:要說具體的原型,應該是有一些的。但是并不能完全這樣說,比如說張團長,其實他是那時候國軍抗日將領的一個縮影,一個綜合體。比如說國共兩軍的傷兵,就是那個年代士兵們的真實寫照。他們有些是壯丁,如小號兵蟈蟈;有些是逃犯,如國軍連長黃燦燦;有些是陰差陽錯地參了軍的,如新四軍隊長陳嶺北。20年前,我曾經是一名軍人,聽到軍號和口令聲,總會令我熱血沸騰。也因為這,我一直想要寫一場南方的戰爭,是因為現在可見的戰爭小說中,很少有寫到江南戰事的。曾經我想寫過四行倉庫保衛戰,但是后來被我否了,因為四行倉庫在上海。而我想讓這個小說有大地、山川、河流,松動的泥土以及蒲公英,甚至新鮮的牛糞。《回家》在《向延安》完成后我就開始籌劃,陳嶺北和黃燦燦、柳春芽等人,在我的一次次幻想中,栩栩如生地走到我的面前。嶺北是我諸暨老家的一個鄉鎮的名字,施啟東、李歪脖、章大民都是我的朋友的名字。他們都是我的親人。
讀書報:在寫出很多有影響的電視劇之后,在小說創作上依然能夠保持“純文學”的水準和語言的純凈與詩意,是令很多讀者意外的。你在創作是否刻意保持小說創作的特點?
海飛:我的創作像一只開關一樣,一會兒開到電視劇本,一會兒開到小說中。我沒有覺得這是一種好的狀態,但是我的創作已經讓我慢慢養成了這樣的生活。當初我為什么要寫小說,特別真實地說,我想通過小說改變命運,因為我不想一直呆在化肥廠里。我為什么還在堅持寫小說,坦白地說,我愛上了小說。這有點兒類似于先結婚后戀愛。在劇本和小說兩種文體的轉化過程中,首先要做的是讓自己安靜下來。我覺得小說的文字氛圍,需要用安靜的狀態來支撐。如果有一天我發現我自己的語言狀態已經不是令我滿意的狀態時,我只會有兩個選擇,一是回到語言的本身,一是不再提筆寫小說。只有兩個極端,愛,或者不愛。有很多小說家離開小說后沒有再回來,不是回不來,是他們不想回來了。他們回來的路徑只有一條,相對的安靜。
讀書報:你如何評價70后作家?今年有很多的同時代作家,推出了他們自己的力作,但是有一些嘗試是失敗的。你如何看待這個群體,這個群體創作存在哪些問題?
海飛:70后作家中,有好多優秀的小說家,我對他們十分的敬慕。這不是客套,我對他們的敬意來自于他們的執著與熱愛。對文學。我很難判別我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確。我總是覺得一部分的70后小說家,沉湎在自己的想象王國里,題材,手法都相當單一,還在不知疲倦地復制從前的一個作品。小說家更重要的是放下架子,小說家和其他手藝人沒有兩樣,造紙高手、著名漆匠、優秀的木工等等。所以小說家最不應該的是高看自己,應放低自己的身段。
一個有生命力的小說來自于想象力,以及對生活或者生命的超強洞察、成熟的小說寫作功力等等。我們在復制生活和復制小說的同時,輕視、怠慢了讀者,這是70后作家應該引起警惕的。當然,現在的70后作家,顯然已經成為文壇的生力軍。而我所知道的一些出道極早的小說家,卻因為種種原因遠離了文壇,從事著其他的職業。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