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蔣一談:河流的聲音是文學的聲音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6月06日13:48 來源:中國作家網 行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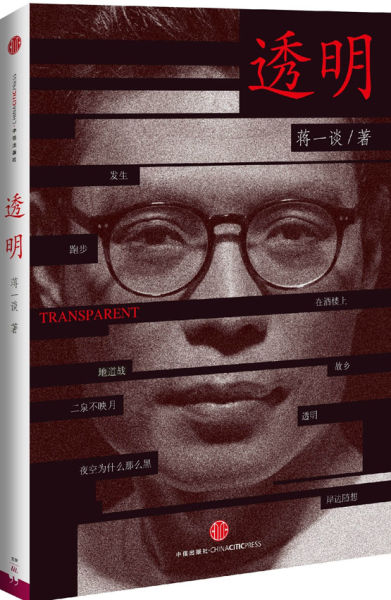
隨時開啟的“雷達”
記者:您曾在1994年出版過3部長篇小說《北京情人》《女人俱樂部》和《方壺》,當時的口碑、銷量都不錯,但那之后您卻放下寫作,專注于出版行業。15年之后,2009年年初,您開始寫作短篇小說,能否談一下轉變的原因?
蔣一談:2007、2008年的時候,我的個人生活遇到了一個難題,我沒有辦法解決,也沒有膽量擊碎這個難題。2009年1月25日,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一個人開著車在北京的環路上游蕩,路上幾乎沒有人。我回到家,看了一會兒電視,然后給朋友們發祝福短信,后來走進書房翻看之前的詩歌和讀書筆記,一直看到午夜之后,情緒非常低落,但我不太習慣找人傾訴。不知道為什么,那個時候忽然很想寫點什么。我完成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公羊》,一個生活在城市里的男人和一頭公羊的故事。寫了幾篇之后,得到朋友們的鼓勵,于是接著寫了下去。
記者:從2009年到現在,這5年您一直專心創作短篇小說,現在的心態產生了什么變化?
蔣一談:19歲的時候,我差不多確立了未來理想,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出版家。我沒想到自己會在40歲的時候還能拿起筆寫作,真沒有想到。2009年夏天,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出版后,我把它放進書柜最里面,好久不敢拿出來翻看,即使到了現在,我也習慣把新出版的小說集放在書柜里,有虛幻的、不真實的感覺。
寫了5年,覺得現在的自己更能體諒他人,不再像過去那么自我了,也更加相信生活和生命的無常,以及承受和理解的意義。文學傳統在選擇淘汰作家,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晚一點被時間淘汰,我想很多作家也是這么想的。
我最初的寫作是為了自己,那支筆的確像一個發泄出口,但在得到朋友和讀者的鼓勵后,心里有了信心和動力,反而想為他們好好寫作。我多年從事出版工作,深知讀者是游離的人群,他們可以鼓勵你,為你鼓掌喝彩,也能隨時嘲笑你,甚至遺忘你,所以寫作者不能也不要完全相信讀者的忠誠度,隨性和自由的選擇是人的本性。
讀者不是作家的朋友,而是作家的敵人,作家須努力用文字打動這個陌生的敵人,讓他在那一段時間里忘了自己,找到自己,找到同病相憐的人。
記者:09年之后您先后出版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魯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棲》《中國故事》《透明》六部短篇小說集,這些作品中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有哪些?
蔣一談:仔細回想,現在覺得《公羊》《ChinaStory》《魯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中國鯉》《刀宴》《溫暖的南極》《馬克呂布或吳冠中先生》《夏天》《夏末秋初》《芭比娃娃》《林蔭大道》《發生》《跑步》《故鄉》《在酒樓上》《透明》這些篇作品是我目前記憶最深的。我喜歡關注家庭故事和家庭里的人物情感,以及現代城市人生活與精神之間的錯位,這些常帶給我觸動。
記者:短篇小說是一個很難把握的文體,我聽過不少寫作者討論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到底那個更難寫的話題,您覺得呢?
蔣一談:比較一篇短篇小說和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難易度會比較簡單,這就好比兩個人比賽跑步,一個跑一百米一個跑馬拉松,完成馬拉松的選手的確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體力,所以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難度顯然大于一篇短篇小說的寫作難度。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可能會有另一個答案:如果一個作家準備用5年的時間寫一部長篇小說,另一個作家準備在5年的時間內寫很多篇短篇小說,那么寫作短篇小說會更加辛苦。作家捕捉社會信息、生活信息的時候需要運用自己的“雷達”,寫作長篇小說,“雷達”可以隨時關掉,可以中途休息一個月甚至幾個月然后再接著寫。寫短篇小說不行,持續寫短篇小說需要持續的文學狀態,“雷達”幾乎隨時都要處于開啟狀態,這會耗費很多時間和心力。對寫作者而言,寫作的難度都必須由一個人來扛。
短篇小說好比一個穿很少衣服的人,身材和皮膚的優缺點就在那兒,很難隱藏;而且短篇小說寫作者,特別忌諱故事構想和故事風格的重復,所以每一篇作品從構思到完成,都需要仔細對待。
記者:就寫作技巧本身而言,您認為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蔣一談: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試著回答。我覺得,就故事構想而言,現代短篇小說更側重故事構想而非故事本身,這個故事構想處于這樣一個交匯點:從生活出發后即刻返回的那個臨界點,即出發即返回的交錯點;或者說,短篇小說需要捕捉那一個將要(可能)發生還沒有發生的故事狀態。長篇小說更加依賴故事的延展性和人物生活的世俗性。長篇小說是世俗生活的畫卷,文學的真意都在世俗里。我喜歡具有河流氣息的文學作品。河流的源頭是小溪小河,是緩緩的涓涓細流,越往下流淌,河面會越流越寬,越有深意,這是文學的靜水深流。
記者:您有寫作長篇小說的想法嗎?
蔣一談:寫完《棲》之后,我有了寫一部長篇小說的沖動,故事和人物會時不時冒出來。后來覺得,現在這幾年,專注于寫作短篇小說是最最重要的,心要沉下來。長篇小說的故事素材和背景材料在慢慢積累中。
大自然里沒有直線
記者:我記得您曾說過:“對現代短篇小說寫作而言,故事創意的力量優于故事敘事本身,它是寫作者的文學DNA”。這是不是說,相比作品形式,您對故事構想更感興趣?
蔣一談:先有桌子,還是先有桌子的理念,這是柏拉圖時代的哲學話題,延續到現在依然很有意義。人類首先要有登上月亮的理念,才會去制造攀升的工具。無是冥冥之中的東西,無生有,想象力是決定力。文學故事的最初構想常常來自虛空,所以在某個時間段,寫作者需要無所事事的無聊生活狀態。
全世界的寫作者數不勝數,沒有獨特的故事構想和敘事方法,很難成為獨特的寫作者。我覺得,按篇幅來講,兩三千字之內的超短篇小說和字數在一萬五千字至兩萬字左右的短篇小說最難寫。超短篇的寫作更接近于禪機。現代短篇小說追求故事構想和細節呈現,不在意故事情節,所以一萬五千字至兩萬字左右的短篇小說,考驗著寫作者的綜合能力。
看似無事狀態下的人和事可能隱藏著獨特的故事。我喜歡思考,那些大家習以為常的故事和人物,能否用另外的方法、另外的角度重新呈現?或許可以試一試。生活的常態是無事,是單調和乏味,是重復昨日,一天挨著一天,跟著時間的腳步。在常態之下,生活的暗流在流淌,人物內心的暗流在起伏。小時候讀孔子的話:“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是很懂。后來慢慢長大,經歷了生活,才懂了些。河流不是時間,不是生活,不是文學,可是當古人把時間比喻為河流的時候,河流的身體發生了變化,河流變成了我們的時間,開始蘊含我們的文學和生活,變成某種思考方式。逝者如斯夫,這是時間和生命的流逝,更是河流本身的流逝,帶著回憶的流逝,物我相合的流逝。有些寫作者喜歡山,喜歡用山巒的方式思考人生,而我更喜歡水,因為水下還有高山,我喜歡用河流的方式思考人生。
記者:與一些追求先鋒性的作家相比,我認為您的敘述方式還是傾向于傳統的,您更注重尋找人們內心最脆弱的那個部分,以一種中性、溫和、婉轉的敘事方式擊中讀者,可以談談您的寫作風格嗎?
蔣一談:文學和藝術永遠需要先鋒精神,需要具有顛覆和散發新鮮活力的力量。西班牙建筑藝術家高迪說過:“藝術來自大自然,而在大自然里沒有直線。”而先鋒性就是要在自然里創造出直線,創造出這種不可能。傳統和先鋒,是文學鏡子的兩面,看鏡子這一面的時候,還要想到另一面,只有這樣才可能寫出短篇小說里樸實的“自然”和創造出來的那條“直線”,創造出獨特的文學真實。2012年春天,城市女性短篇小說集《棲》出版后,有讀者以為我是女作家,也有讀者以為我是同性戀者。兩者都不是。在讀書活動現場,我對讀者朋友們說,作家要努力成為雌雄同體的人。我喜歡腳踏實地的作品,也在努力學習并追求故事構想的獨特性和語言敘事的簡潔和準確。我也希望自己能在現實主義大風格的前提下,探尋故事構想和敘事的多種可能性。
記者:現實主義是一個很含混的概念。有些作家的作品看似寫的是現實生活,甚至是新聞事件,但表達卻是表層的、隔靴瘙癢的,不能真正深入現實的核心;而有的作品雖然是魔幻的、荒誕的,但它關注的卻是人類共通的問題,是放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成立的,所以讀者會覺得它無比真實。您如何看待文學故事和現實生活、新聞事件的關系?
蔣一談:非虛構寫作在歐美發展了很多年,作品的分類(傳記、回憶錄、紀實文學、事件調查、游記、類型文學等)寫作和傳播已經很成熟。取自新聞和真實事件的寫作常常意味著非虛構寫作,而非虛構寫作的要義是基于真實,擁抱虛構。而在擁抱虛構的過程中,作家的寫作能力起著關鍵作用。所以,遇到一個事件,一個大的歷史故事,故事結構和敘事方式,顯得越來越重要。這幾年,《人民文學》雜志社的非虛構欄目和寫作申請計劃,大大拉近了非虛構作品與讀者的距離;同時,這幾年出版的文化人物的個人和歷史回憶錄,一直受到讀者的喜愛。我覺得,中國需要更多、更好的非虛構文學。
無論是虛構作家,還是非虛構作家,你的問題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家最重要的寫作目標是什么?是描寫現實主義,還是描寫現實生活里的那些人?換句話說,作家是以筆下的人物為道具襯托出了他眼里的現實主義,還有以現實為背景托出了他心里想寫的那些人?
這幾年,我嘗試寫了幾篇故事構想與新聞事件有關聯的作品。2010寫的《中國鯉》,故事構想來自一部紀錄片:《中國鯉魚入侵美國》。2011年寫的《馬克呂布或吳冠中先生》,故事構想來自馬克呂布先生在北京的影像展和吳冠中先生的自傳《我負丹青》。2013年寫的《故鄉》,故事靈感來自一篇新聞報道:一個西班牙男人深陷“911”災難,他選擇右邊的樓梯井逃生后,內心一直恐慌,后來每次遇見路口,他都會下意識地選擇往右邊行走。這個西班牙男人刻印在了我的腦海里。
我個人覺得,現實世界發生的新聞和真實事件應該最大限度地歸屬于電視和網絡傳播,觀眾由此獲得信息已經足夠,而寫作者(其實也是觀眾)不能有和電視網絡搶占新聞信息的心理,更不能沉浸其中。文學性真正決定作品的品質,無論你寫的是非虛構作品還是虛構作品。
記者:您的小說集題詞和作品文字里時常出現詩歌,都說詩歌是語言的極致表達,您怎么看待詩歌的閱讀、創作對您小說創作的影響?
蔣一談:我覺得,詩歌是距離禪宗最近的文體。我喜歡詩歌,一直在讀詩寫詩,這些年寫了兩三百首詩歌。我更喜歡口語詩歌,尤其是那些簡潔的平民口語詩歌。我希望通過詩歌的閱讀和寫作,用另一種敘述方式存儲自己的情感,同時也想通過詩歌寫作保持語言的溫度和濕度。詩歌和小說,是一對特殊的情侶。
知識分子和老男人:孤獨的現代人
記者:您的作品里有很多上年紀的“老男人”,比如《魯迅的胡子》《China Story》《故鄉》《發生》《故鄉》等等。這些人物處境不一,內心都很孤獨,這一類人物形象在您的作品中非常突出。為什么著意描寫這個特殊的群體?
蔣一談:讀完厄普代克的《父親的眼淚》,他筆下的那些老男人打動了我,我也開始儲備這方面的寫作素材。之前的筆記本里,有十幾位這樣的人物,年齡從五十七八歲到六七十歲。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現代人的壽命雖然比過去長,但古人的傳統理念還在留存。一個人過了70歲,會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離死亡更近了。我父親今年75歲,他時常一個人坐在那兒,靜靜地注視外面的世界,能坐很久。這一幕帶給我更多的是無力感。前一段時間,電視臺做了一個“誰是家里的頂梁柱”的生活調查,男人差不多都是家里的頂梁柱,可是時間和歲月對男人的折磨是很殘酷的。女人害怕五官的衰老,男人害怕內心的衰老。
記者:您之前出版過以城市女性為描寫對象的短篇小說集《棲》,主人公的年齡在20多歲到40歲左右,未來會寫六七十歲的老女人嗎?
蔣一談:不會多寫。我覺得,男人一旦衰老,比女人更能體味到脆弱和無力。男人要承受由強大(哪怕是虛飾的強大)到虛弱這一無可奈何的轉變。在我看來,年邁的中國女人比年邁的中國男人,內心更顯堅韌和堅強。我更喜歡探尋虛弱的人物。
記者:除了“老男人”,知識分子形象在您的作品里也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魯迅的胡子》《林蔭大道》《在酒樓上》《溫暖的南極》《跑步》《故鄉》等作品,都是以知識分子為主人公的。您的小說常常刻畫他們失意的、掙扎和努力承受的現實和精神現狀,為什么對這個群體格外關注?
蔣一談:寫完《魯迅的胡子》之后,我開始儲備與知識分子有關聯的故事構想。我想在合適的時間出版一本當代知識分子主題的短篇小說集,但我知道,這本小說集里的作品不能著急寫,需要一篇一篇積累。城市女人和知識分子是我長期關注的人物群落。世界由知識碰撞推動前進,相比過去,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數量比以往多很多。但是,何謂知識分子?何謂合格的知識分子?這個話題非常大卻又非常模糊。我無意于探尋當代知識分子的模糊和尷尬身份,因為有比身份確認更重要的事情。
我是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里,我有失敗感,有自己的精神疑難。我認識的一些“50后”、“60后”、“70后”、“80后”知識分子,也有這樣那樣的無力感和失敗感。相比過去,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內心更為糾結的一群人。知識是他們尋找世界、和世界對話的方式和工具,可是太多的知識和信息也會變成心里的牢籠和業障。我目前的作品與我的實際經歷沒有關聯,可是在寫作知識分子的時候,我覺得好像在寫另一個自我,這種感受會讓人心生沮喪。
記者:《跑步》里的主人公就是這樣一位內心掙扎的知識分子,他在跑步機上奮力奔跑的場面很真實。一個生活中處處不如意的中年男人,似乎只能用最原始的奔跑與他人競爭,以此證明自己的存在和虛妄勝利。
蔣一談:我在跑步機上鍛煉身體,之前沒有想過寫這樣一個故事。去年在新加坡的時候,我路過一間健身房,透過玻璃窗看見兩個男人正在跑步機上跑步,寫作靈感是在那一刻來的。我想探討一個40歲左右的知識分子,一個文弱的男人,面對現實的原始暴力,需要在現實面前扮演強大的父親角色。
父親養育孩子,這是無法回避的血液里的責任,可是父親這個角色,這個由更多的知識支撐起來的父親角色,在突如其來的暴力面前,會怎么樣呢?他的經歷和思維模式,讓他遺忘了暴力和力量,他被自己的生活異化了、弱化了,但后來他知道自己迫切需要男人的那種原始的暴力和力量,哪怕是跑步機上暫時的扮演,他也想以此努力喚醒自己、證明自己,同時安慰自己。社會現實越實際、越具有破壞力,知識分子就越需要扮演。
記者:您的作品經常涉及到家庭的疏離、傷痛和彌合,您剛才也提到,喜歡關注家庭故事和家庭里的人物情感,可以談談其中的原因嗎?
蔣一談: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也是家庭中人。人生是機緣碎片的組合,國家是家庭碎片的組合,家庭碎片漂浮在國家時空里,尋找著各自的位置。和過往相比,這個時代,國家和家國的概念,生存和存在的概念,都在發生著變化,而變化間的人和事,蘊含著文學生機。
可能是因為性格和閱讀偏好,我喜歡關注人物的情感世界,即使人和人之間產生的那種情感是瞬間的;因為瞬間,我喜歡“一機一會”這個詞語,這是站在懸崖邊的狀態,而短篇小說的構想初始是這個狀態。一個故事構想,要么感應到抓住了,要么就會掉下懸崖。所以,短篇小說的構思之端非常陡峭,但在寫作的時候,陡峭感又不能顯現出來。
選擇了什么樣的生活,或許決定了寫作者的故事選材偏好。我喜歡家庭故事,也很愿意成為一名“中國家庭作家。”
記者:您的短篇小說,絕大多數是在描寫城市男女的故事。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比較晚,相應的城市文學出現得也比較晚,發展不夠成熟。我個人認為,真正的城市文學關注的應該是生活在城市,吃穿不愁、物質層面沒什么困難,而在精神層面出現問題的人。但是,目前國內很多作家還是將目光放在城市中的底層,他們所描寫的生存問題基本上還是跟生計有關的。您的作品在這方面卻有特別的表現,比如這本小說集里的《發生》《跑步》《夜空為什么那么黑》《透明》等,都在關注城市人的精神困境。您心目中好的城市文學應該是什么樣的?
蔣一談:這個問題也很難回答。每一個作家都是有局限的,可是局限本身又給我們留下兩個思考話題:作家如何在自己的局限里創造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故事和人物,如何在持續的寫作中突破自己的想象和敘事局限。
關于底層故事,我寫過《芭比娃娃》。就像你說的,底層人物的生計問題常常排在精神疑難前面,或者說那個故事本身就是生計問題。后來,我又嘗試寫了幾個底層故事,但中途都放棄了。這里面有一個個人寫作心理的問題。我不太喜歡“底層”或者“小人物”這樣的文學表述概念,我更愿意接受“普通人物”和“平民化”這樣的表述。如果非要用“底層”人物概念,這樣的人物似乎應該由兩種人物構成:經濟上的底層人物和精神上的底層人物;而精神上的卑微人物即是精神上的底層人物。在現實生活面前,在內心深處,那些社會地位高、收入高,且文化層面高的人物,內心里那種精神上的卑微感是真實存在的,或者說在某一個時空,會時不時閃現一下的。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更能體會到精神上的卑微感,體會到精神上的瞬間崩塌。
中國現在有4.3億個家庭,其中城市家庭的比例今年為52%左右,城市家庭數量一直在持續增加。我曾在網上讀過一個著名作家的訪談,他說他喜歡寫過去的故事而不喜歡寫當代現實生活,他認為當代生活很容易寫,所以不寫。我倒覺得當代現實生活是非常難寫的,因為我們的讀者是當代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時間維度里,讀者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生活感受,而作家的職責就是要讓讀者相信文字的虛構。這是一種角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認為會有越來越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尤其是那些有一定知識背景的城里人,會離開城市來到城市的最邊緣或者鄉村里,他們可能是在逃避,也可能想重新發現未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有人物的地方才有故事,而未來的中國鄉土文學,抑或村落文學,從題材到思想,將會發生新的變化。
最開始寫作城市文學的時候,我給自己定了“三不”原則。一,不寫城市的外化符號,虛化背景;二,不寫人物的五官特征;三,不獵奇。我想讓自己不去注意或者遺忘眼睛所見的東西。
漢語寫作與中國故事
記者:很多作家說過,童年經歷影響著一個作家的寫作,您是這樣認為的嗎?
蔣一談:童年時代是以記憶為時間起始的。有些人,兩三歲的時候有了記憶;有些人,四、五歲的時候才有了比較清晰的記憶。我對四、五歲之前的事情沒有太多印記,可是我對那一段失憶的往事很有興趣。我問過父母親,可是他們的回答不能滿足我。我父母是中學老師,我們家在校園里面,下午放學后,校園里很安靜,我喜歡一個人在教室里轉來轉去,走遍了校園里的角角落落。讀中學期間,我有口吃的毛病,害怕上語文和英語課,害怕和陌生人說話,內心有自卑感。我時常一個玩,一個人待著,或許那時候正在經歷孤獨,但我還不知道孤獨的含義。我喜歡夏天,因為夏天多雨,我喜歡待在家里,坐在小板凳上,隔著竹簾縫隙,聽看外面的雨。我相信童年的經歷影響了我的性格,我喜歡獨處,至今不習慣人多的地方。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始終對那段我沒有記憶的往事充滿好奇,那是一個空白地帶、模糊地帶,而我喜歡想象那個模糊地帶,反而忽視了童年時代真正發生的那些故事。對我而言,寫作或許就是對失憶時空的想象和探尋吧。
記者:在您最新的小說集《透明》中,《故鄉》和《在酒樓上》都會讓讀者聯想到魯迅先生的作品,您是否在有意寫作這樣的同題短篇小說?還有后續的寫作計劃嗎?
蔣一談:寫完《魯迅的胡子》之后,我有了這個想法,但一直不敢動筆。我想尋找和魯迅先生作品的敘事差異,也想探尋過去年代的知識分子和當代知識分子的心理異同。魯迅先生的《故鄉》,敘事從外至里,整體調性是悵然的,我想選擇從里至外的視角,把人物性格放置在糾結和模棱兩可的世界情緒里去。魯迅筆下的故鄉發生了變化,但故鄉依然存在,可是在當代中國,故鄉很有可能已經無處可尋,主人公身在異國他鄉,只有通過網絡科技,才能近距離地和虛擬的故鄉實現心理上的觸碰。在魯迅先生的《在酒樓上》中,兩個知識分子對飲傷懷,事實上是一個人在傾訴和哀嘆,那個酒樓只是對話的襯托場所,空間意義是單向度的。時至今日,對中國人而言,酒樓已是最普通的現實空間,但這個空間里面除了娛樂和歡鬧氛圍,還會有精神上的壓抑和壓迫感。我想寫這樣一個發生在酒樓里的故事,可是故事發生之后,酒樓空間或者說酒樓的命運會怎么樣呢?“酒樓”這個物理空間,是否可以具有文學“人物”般的命運啟發和延展性呢?我想嘗試一下。我也想通過“80后”的知識分子和酒樓空間,與讀者探討一個隨時有可能擺在眼前的現實生活難題。對當代漢語寫作者而言,魯迅先生以及他的作品都是一個巨大的存在,無人可比。我目前正在構思《藥》《傷逝》《祝福》等其他作品,這是一個很困難、很磨人的寫作過程,需要兩年多的時間才能完成。
記者:除了魯迅之外,還有哪些作家對您產生過重要影響?
蔣一談:在我的心底,除了魯迅,契訶夫、菲茲杰拉爾德和納博科夫最早影響了我的寫作。當代在世的世界作家中,我喜歡門羅和裘帕拉西莉的短篇小說,喜歡石黑一雄和奧茲的長篇小說,喜歡他們平緩、細微、深沉的敘事。20世紀的文學現代化和21世紀的網絡文化,遮蔽了19世紀世界文學的光芒和魅力。我特別感謝大學時代的老師,那個時候提醒我們要仔細閱讀契訶夫的作品,要把基礎打牢。現在遇到一些更年輕的作家,我也會把老師的話轉述給他們,別遺忘了契訶夫,別太迷信現代主義文學。對短篇小說寫作者而言,契訶夫是一位源頭性的文學巨匠,寫作短篇小說要從認真閱讀契訶夫開始,然后再在寫作實踐中尋找自己的寫作風格。
記者:具體而言,這些作家對您的寫作產生了什么影響?
蔣一談:閱讀愛好常常決定寫作文風。我喜歡平實的文字,慢慢浸透人物氣息的文字,所以那些狂放的文字、靈秀瀟灑的文字、戲謔調侃的文字,不在我的書櫥里面。閱讀喜歡的作家讓我明白,寫作者要對文學抱有虔誠的態度和赤子之心,應當與現實世界保持適當的距離,要和現實生活保持一定的疏離或者緊張度,這是避免作品淪為生活模擬化寫作的重要一環;同時,也讓我漸漸明白,一個寫作者不能只想著描述人與現實的關系,要努力寫出現實生活里的那個人,那個獨特的故事和人物。寫作者筆下的現實只是一個背景,是為了襯托獨特的故事和人物而存在的。
文學來自現實,寫作者要對現實生活有種獨特的感受力和抓取能力;文學高于現實,作家的作品要能讓讀者既感受到陌生又感受到新鮮和熟悉。這是“來自”和“高于”文學理論的現代文學對應關系。離現實太近,文學會被現實吞沒,離得太遠,文學又會顯得凌空虛蹈,故事和人物就會減弱或者失去現實的附著力和影響力。
記者:您出生于1969年,批評界按照慣例會把你歸為“60后”作家,可是您的作品在故事構想和精神氣質上卻與余華、蘇童、格非、畢飛宇、李洱等著名的“60后”作家有很大不同,您怎么看待這其中的差異?您在40歲的時候才開始寫短篇小說,心里有壓力嗎?
蔣一談:我相信一點,人活在自己的時間里,需要傾聽時間的暗示。這些作家成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們在寫作的時候,我也在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我們雖然出生于同一個年代,但在文學寫作的時間上,他們是先行者。我尊重時間,所以我的心里沒有壓力。我很慶幸自己出生在1969年,這是時間和經歷的秘密,沒有在1969年出生,我會錯過很多很多故事和感受,寫作心態也會發生變化。事實上,有不少朋友和讀者問過我類似的問題,我這樣表述過:“我在2009年開始正式寫作,剛剛起步。我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作家。”
面對先行者的作品,我首先要學習,然后尋找繞開的路徑,這是文學上的尊重,也是寫作路途上的自我尋找。我在寫當代城市生活,在寫此時此刻,沒有寫個人的生活經驗,我在努力虛化故事背景,潛意識里沒有和歷史纏繞,這或許是我的寫作與他們的差異之處吧。
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覺得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缺少一個比較文學的環節(或許有,但還不是十分明顯)。比方說,從2000年開始至2010年,或者說,從2010年至2020年,世界上的優秀作家們都在寫什么,寫了什么?中國的作家們在寫什么,寫了什么?或許這樣的每隔五年或者十年的橫向比較文學研究,能幫助我們的漢語寫作跳出語言的邊界,尋找到另外一種寫作思維的可能性,尋找到這個世界共通的情緒和情感。
我是中國作家,用漢語寫作是一輩子的事情,既然漢語是我永遠的唯一的寫作標簽,那我能否在自己的漢語作品里淡化“中國故事”的外在符號?能否用世界思維去寫中國故事?極端地說,如果把作品里的中國人物的名字換成外國人的名字,把中國城市和街景的名稱換成國外的地名,中國故事的邏輯和人物情感傳遞是否依然存在并有效?這樣的中國故事是否會更有人類的情感通融性?我在思考這個問題,也在嘗試寫作這樣的作品。這兩三年,也和國外的朋友交流,他們告訴我,《中國鯉》、《ChinaStory》、《夏末秋初》、《夏天》、《溫暖的南極》、《發生》、《故鄉》、《透明》、《在酒樓上》這樣的作品,他們讀完后能夠感同身受,能夠理解并接受人物的內心情感。接下來的幾年,我想進一步寫作這樣的中國故事,雖然寫起來很辛苦,但覺得應該去嘗試探尋。
記者:您的下一本短篇小說集會寫什么?
蔣一談:會是一本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主題的短篇小說集。目前已經積累了六七篇作品,希望今年內能把其余的幾篇作品修改完成。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