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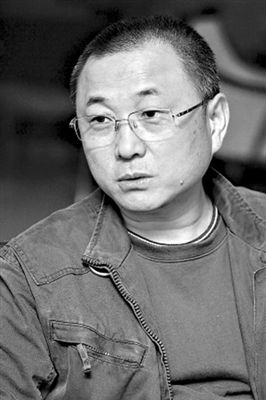
少年時的劉醒龍,在湖北黃州的山村里,用腳一寸一寸地丈量著家鄉的河流。和許多山里少年一樣,他攀上山頂仰望無際的天空,想起夜晚爺爺給他講的各式古代俠義故事,也想著山巒的盡頭,是世界的何處。多年后,他回憶起曾經被啟蒙的一個瞬間:“我少年的時候,就喜歡一個人躺在山坡上看天空。記得有一次一架飛機從天上飛過,我突然產生了一種恐懼感,一種對生命的無奈,想著世界上還有那么多的東西都還沒有嘗試過,也不知道這輩子能不能接觸到,就很絕望。”一種小路有盡頭,大路可朝天的期待逐漸打破了單純的“天籟狀態”。隨著父親的工作調動,他也離開家鄉,隨著挑夫起伏的背影,“一步一步地走進大別山腹地”。
在后來的成長歲月里,對于家鄉的印象越來越遙遠,逐漸內化成記憶中的一個焦點。他常用“漂泊無定”這樣蒼老的詞匯來形容少年時光,“很多時候,連我都覺得自己的身份十分可疑,而更相信自己漂泊無定,沒有真正意義的故鄉、故土和老家,無法像大多數人那樣,有一座老屋可以寄放,有一棵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樹木作為標志,再加上無論走得多遠都能讓內心踏實可感的一塊土地”。當他開始寫作,并期望手中的筆寫下家鄉時,發覺家園雖惘然,根脈卻抽出新枝,“人一旦離鄉村遠了,其心靈離鄉土就會更近”。因為少,也便更珍惜筆觸,他把家鄉當作濃郁的精神意象,沉浸在小說中,發掘深埋的心靈,就如獲2011年茅盾文學獎的《天行者》,主角鄉村民辦教師,被他視為“哺育二十世紀后半葉鄉村心靈的英雄”。
少小離家老大回。成年后的劉醒龍,很少回家鄉,他對記者說:“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在家鄉待過一整天。”而每一次短暫停留,在他記憶中都是忘不掉的大事。第一次回老家,還是30歲那年,父親帶著他,“為了替垂危的爺爺選一塊墓地”。那時他悟出了答案:“除了將心靈作為老家,我實在別無選擇。”他再次踏上這條鄉間小路時,手中多了父親。也就是這一次,他決定第一次以形而下非虛構的方式,寫下家鄉,寫下父親。
他在2012年末寫下的這篇散文,名為《抱著父親回故鄉》,而后發在2013年初的《北京文學》上,熟悉他的朋友看到這篇散文后,為其中隱忍的平和和流淌的回響所震動。他對記者說,這一次“一切都不再是抒情,而是一點都不含糊的真真切切的存在”。是第一次“父親與故鄉合為一體了”,也是他作為兒子,“第一次”且最后一次抱著父親。相隔一年,這篇散文獲2013年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也為這“第一次”平添了一層紀念意義。被潮濕小徑、寂靜小垸所喚醒的家鄉也在劉醒龍的答案中露出了原初模樣。
記者:《抱著父親回故鄉》 刊發后,許多人感受是溫情背后藏著深厚積蓄,延展出無限的家園感,是篇與眾不同的紀念親人文章。您寫完后是種什么樣的感覺?
劉醒龍:這些文字是為父親守靈時寫下的。當時覺得斷斷續續,寫到最后才發現,幾乎不需要再增刪什么,依著原始的樣子就行。主要的感覺是遺憾,是文學在表現情感時,無力達到真實狀態的那種遺憾。對家鄉的習俗我并不是太陌生,即便如此,當父親被掩埋在土地里,我還是強烈震撼了。熱心幫忙的鄉親們,將預先埋下的鋤柄從堆土中拔起,留下一個通向墓室的小洞。作為長子的我,幾乎是趴著將幾樣家鄉食物放進小洞中,讓深埋在土地里的父親吃上人世間最后一頓午餐,再用雙手捧起黃土堵上這洞口。這種震撼再過幾輩子我也許會寫出來,但在這篇文字里,我的文字是蒼白的。
記者:這篇散文里,您是重新踏上了一條回歸家園的真切小路,記憶都被喚醒了,魚丸、炊煙、包面,散發出慢慢“尋到根”的感覺,語言也是克制的,并不張揚。這讓我感覺,抱著父親葉落歸根,是情感上的儀式,尋回了許多往事。
劉醒龍:還有心痛。我這輩子沒有見過奶奶和外公,外婆也只出現在我一歲時那早已找不到蹤影的記憶中。爺爺和父親都是88歲時離開我們的。爺爺走時,我正鬧失眠癥,守了兩天兩夜之后,我從下午兩點一口氣睡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失眠癥就此痊愈。爺爺走時當事的是父親,所以,父親是我當事送別的第一個親人。那種心痛,包含著對諸多無法彌補的往事的追悔。
記者:您說:“此時此刻,我才發現大路朝天也好,小路總有盡頭也罷,都在自己的真情實感范圍之外。”當自己切身感受到那種生命內在聯系的復雜時,是否就不敢相信了?
劉醒龍:“根:是一種撫摸骨頭的感覺,一個人尋找到自己的根并不是一件令自己特別快樂的事情。它會讓人懷疑,從這根上生發出來的事物,真的與這根有著生生不息的關系嗎?
記者:這篇散文雖不長,但感覺隱藏了不少故事,比如父親只身在洪水來時抵抗決堤口,只希望全村人不用再出去乞討。您想過將來會通過散文形式更多地呈現嗎?
劉醒龍:散文是一種必須時刻保持警覺的文體,寫作者稍有不慎就會被自我異化。這也是我很少寫散文的緣故之一。除非我的情緒百分之百飽滿,除非我的心態百分之分正常。當然,真正的百分之百也是不可能的,起碼要達到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看上去散文是一種廣受歡迎的文體,實際上散文又是與讀者最不相干的一種文體,其非虛構性決定了它必須是寫作者的一種心靈狀態。在散文中的任何虛構,所殺傷的不是散文,而是寫作者自身。
記者:您曾提到30歲那年和父親回家鄉為爺爺選地時,因為當年棲身之所已成了別人的菜地,“關于故鄉的夢突然裂成碎片”,以及以前也提到自己童年是“流離失所”狀態,對家鄉的記憶是零散的,但您的小說并不缺豐富的家園意象。
劉醒龍:每每見到一些作品將大量鄉情恣意汪洋地堆砌其中,我就感到難受,是妒忌,也是遺憾。相比他們對家鄉的日常起居有太多了解,因為我所曉得的量少,就會更加珍惜。家園意象可以是一百件事,也可能是一件事。重要的是它們在每個人心中的分量。
記者:身居武漢多年,您曾說時時刻刻想著如何改變這座城市讓它更美好。城市也是許多人的“家鄉”,包括您的兒女,對于城市生活,您希望它的情感秩序是什么樣的?
劉醒龍:城市里的人反感拆遷,也是因為城市也是有故鄉的。這種情懷現在有了根本的改變,只要有足夠的拆遷補償,就算一年拆一次,一年搬一次家,也難得有人反對了。隨著城市建設的大功告成,生活相對穩定下來,人與人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情感秩序,也會慢慢回到城市。
記者:您主編《芳草》多年,觀察到的鄉土敘事寫作,對于“在場”和在城市書寫,這兩者之間如今呈現出哪些不同的特質?近兩年非虛構方式書寫鄉村的作品熱議頗多,也像是在對以往小說大量煽情的一種理性反撥。
劉醒龍:合格的寫作,優秀的作品,其狀態都應當是“在場”的。當代文學,包括小說、詩歌和散文,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正是其狀態沒有“在場”。既不在文學現場,也不在人生現場,甚至連生活現場都不在。在這一點上,詩歌反而是做得最好的。這些年,我所閱讀到的能撼動心魄的細節,既不是小說提供的,也不是散文提供的,而是由詩歌提供的。在這方面,小說做得最差。對細節的敘述原本是小說最核心的機密。這些年詩歌的活躍,在于詩歌發現并撿到被小說丟棄在田野上的麥穗。調查兇殺案的警察要弄清楚死亡原因,處理車禍的警察要弄清楚現場痕跡,文學若找不到文學的第一現場,就算每天上一次“排行榜”也不行。還是要聽信那句話:再偉大的男人,回到家鄉也是孫子。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