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葉兆言:我只是把經歷的一段歷史寫出來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4月11日10:18 來源:中華讀書報 舒晉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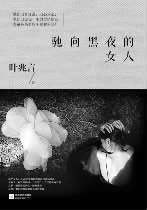 《馳向黑夜的女人》,葉兆言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38.00元
《馳向黑夜的女人》,葉兆言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38.00元28年前,參加廈門的長篇小說組稿會期間,留著長胡子、不修邊幅的葉兆言見到了被傳得神乎其神的“黃半仙”。據說他算命很準,很多作家都請他計算未來。
他看了看葉兆言的手心,又摸了摸他的鎖骨,誠懇地說:“你不能寫小說,你應該寫詩,你應該成為一個詩人。”葉兆言感到很沮喪,他知道自己熱愛詩歌,但是缺乏詩才,根本就不可能成為一名出色的詩人。可是,他是一個不肯向命運低頭的人。盡管有種種暗示,也有種種退稿或創作的挫折,葉兆言還是賭氣式地寫下去了。
時至今日,寫還是不寫根本不是一個問題,葉兆言早已深陷在寫作的泥淖之中,生命不息戰斗不止。他的心里永遠藏著“很久以前”,他終于沒能成為詩人,而成為一個講故事的人。
今年初,《收獲》刊出葉兆言長篇小說《很久以來》,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時,改為《馳向黑夜的女人》。這一取自多多詩歌意象的書名,不僅隱含著故事的走向,更隱秘地體現了葉兆言文學上創作的來處。那個沒能成為詩人的作家,青春年少時期其實更多地受到三午、多多等一批詩人的影響。
舒晉瑜:新作在《收獲》發表時題為《很久以來》,由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時將改名為《馳向黑夜的女人》。中間經歷了什么?
葉兆言:有很多話題可以說。一開始我并不愿意改名。編輯和我商量改名自有他們的道理,出版社要把我的書推出去,也有自己的策略和營銷手段,他們希望我能相信他們一次。編輯認真地和我在談改名字的事,有過很多討論。曾經有一度想叫《烈日的詛咒》、《笑吧,哀愁》。我個人比較喜歡多多的詩,在我還是個中學生的時候,特別迷戀多多。我和編輯說,只要能從他的詩中找到我喜歡的句子,就可以做書名。“馳向黑夜的女人”是一個很好的意象,它源于多多1979年的一首詩。寫這首詩的年代,正好是我的文學青春期,現在用它做書名同,也許就是天命。它適合小說的節奏、畫面感和故事走向。改名字當然要慎重,這一點毫無疑問,至于是否成功,還要經歷時間的考驗。
舒晉瑜:《一號命令》的內容和題目似乎有很大的反差。其實《一號命令》討論的是為什么會有“文革”,是在追溯“文革”的源頭;在《馳向黑夜的女人》中,寫到了“文革”之后。雖然故事之間沒有聯系,但是從時間上看,探討的是一條時間與歷史的河流。能否將這兩部作品看成是姊妹篇?
葉兆言:既可以,也不可以。說可以,是一個作家的作品,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姐妹篇,都有互文關系。這兩部小說其實有很大差異,首先是篇幅,一個是中篇,一個是長篇。內容也不一樣,它們的差別就像男人和女人的差別。當然,男人女人都是人,都是人的故事,都和文革有關,都和文革有關的東西有關。
舒晉瑜:很多時候您是一個特別愿意探詢可讀性的作家。這樣的努力是否相對來說,對讀者比較有信心?
葉兆言:我對讀者向來沒有什么信心,寫作就是一個你非常想寫的一個行為,你如鯁在喉,希望一吐為快。可讀性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東西,張三說可讀,李四會說不可讀,因此我并不考慮可讀性,不考慮,不是因為清高,是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叫可讀。大家都說金庸的小說可讀,可是我遇到有些女孩子,她們一點也不喜歡,她們并沒覺得金庸小說可讀性強。過去很多女孩子喜歡看《紅樓夢》,都覺得可讀,我可以肯定,很多男孩子未必受得了里面的哥哥妹妹。
如果可以做廣告,我會說一句,這個小說很可讀,很好看。然而這只是標準的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沒理由說自己的瓜不甜。當然究竟甜不甜,總不能我說了算。
舒晉瑜:《一號命令》和《馳向黑夜的女人》都用到了閃回的敘述方式,這樣的敘述,很有畫面感。是有意這么做嗎?
葉兆言:當然不是。它們其實是兩個不一樣的敘述,究竟如何不一樣,讀者只要看了就會明白。恐怕所有的小說都應該有些畫面感,文學要運用形象思維。總得有一些畫面來說事兒,這是虛構文學作品的基本要求。這倒不是說有了影視以后,畫面感才變得重要。好的唐詩宋詞也有畫面感。
舒晉瑜:畫面感可以給讀者提供很多想象空間,比如還有景物描寫帶來的畫面感。
葉兆言:景物描寫在當代作品中相對減少,跟敘述方式和閱讀方式的改變也有關系。在過去的時代,閱讀小說是最重要的消遣方式,人很空閑,好像有著大把的時間,那個時候的閱讀沒有替代品;現在替代品很多,人們用在閱讀上的時間已經很少,如果作品再有大量的景物描寫或巴爾扎克式的全景描寫,肯定也有問題。
舒晉瑜:這么做在某種程度上是否消減了作品的文學性?
葉兆言:也可以反過來說,是增加了作品的文學性。藝術創作的重要原則,是你要希望自己能比前輩作家描寫得更好,否則也沒有太大必要每一段都有景物描寫,畫虎不成反類犬。
舒晉瑜:如果這么說,小說家存在的理由,也必須是比前人寫得好或者有不可替代性?
葉兆言:要說比前輩寫得好不太可能;寫得“不一樣”是應該的,也因此證明了寫作的難度,這也是作家必須思考的,前人的成功有可能是你的陷阱。
舒晉瑜:自《沒有玻璃的花房》起,文革是您的主要關注點之一。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嗎?
葉兆言:過去沒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俗套太多,那樣的書寫可以在網絡上搜到很多,有的接近所謂的報告文學,游走在所謂的真實和非真實之間,放在中國傳統小說里看,會覺得這些描述非常接近黑幕小說,接近暴力和色情的邊緣。它在描寫中增加了慘重的、血淋淋和夸張的元素,有著太多不文學部分,更像法制低俗小說,反正是有一種我不愿意去做的東西存在。我一直覺得,如果我寫,一定會從另外的角度去談,不會有過多的獵奇。
舒晉瑜:為什么說今天可以寫?有什么具體原因么?
葉兆言:對于文革的敘述和討論已到了離譜的時候。無論正方反方都很怪,大家談論的文革都不太像文革,他們說的文革和真正的文革常常沒有關系。現在,真實的文革已不是流行話題,這時候,真要談這個話題反而簡單正常。今天的文革描述已經完全變味,有人認為文革是反腐敗的,沒有貧富差異;還有一種認為文革就是打砸搶,就是造反派的天下,就是大街上隨便拉一個人到體育館就可以批斗或者宣判槍斃。這和我熟悉的文革完全不一樣。
現在可以寫,是我發現文革正變得越來越簡單化,越來越概念化、符號化,變得非黑即白。我自己很清楚地知道,文革是活生生的一段河流,彎彎曲曲,很復雜。
舒晉瑜:您是否在寫作的過程中,考慮過把握故事節奏,讓它情節性更強一些?因為故事技巧對您來說早已不成問題,或者是否正因為過于嫻熟,才忽略了這一點?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一方面覺得您始終把敘述方式擺在重要的位置,而且一直嘗試敘述角度的試驗。可是作品帶給我的閱讀體驗卻不是這樣。
葉兆言:我的寫作從來不考慮可讀性。不是我清高,而是無法操控。如果說我寫了讀者就讀,那只是想當然。我們看福樓拜、福克納的小說,看經典作家的小說———海明威除了《永別的武器》也不那么可讀,《百年孤獨》這樣的小說很多人可能也只是知道它的名氣,未必能夠真正讀完。一個有堅定信心的作家,真實的想法就是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就是隨心所欲,就是盡力而為。
舒晉瑜:欣慰和春蘭的故事,折射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她們傳奇的一生在時代大變革的背景下顯得那么微不足道,盡管出身不俗,卻依然歸于平淡,甚至死如草芥。看完之后不由得為她們深深地惋惜。尤其是欣慰的死,令人感覺到時代的荒謬。您想要表達什么?
葉兆言:作家對很多問題的思考,和常人不太一樣。作家更在乎的,不是自己想表達什么,而是讀者能看到什么。你喊不醒一個裝睡覺的人,我不介意寫悲劇或喜劇,只希望寫一部接近原生態的東西。我覺得評價不重要,文革對或錯不重要,反思也不重要,這些都讓哲學家、思想家去判斷吧。一個作家不應該是思想家或哲學家,作家用不著啟蒙,因為他并不是在對傻子說話。
我始終覺得,一個作家不應該靠寫什么成名,怎么寫才決定他是否是一個好作家。寫什么和怎么寫像鳥的兩個翅膀,解決好這兩個問題,才能拍打翅膀飛起來。所以對于我來說,為什么寫這個故事,要達到什么目的,我不太多想。過去我們喜歡一個句式,通過這個我們認識到什么……對于作家來說,把“通過”的這個東西寫出來就行了。有人說我在控訴文革———我只是把經歷的一段歷史寫出來。我不覺得是在控訴,該控訴的東西太多了,文學也不應該僅僅是控訴。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