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東紫:寫作,祛除生命恐慌的藥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3月18日15:29 來源:山東商報東紫的本職是藥劑師,她在﹃極端化﹄與﹃理想化﹄之間的精神飛翔中描摹著那些﹃小切口、大傷痛﹄。她坦言,﹃文學是最公正的,只要我們真誠地去對待它,它就會真誠地回報我們。﹄本版撰稿記者張曉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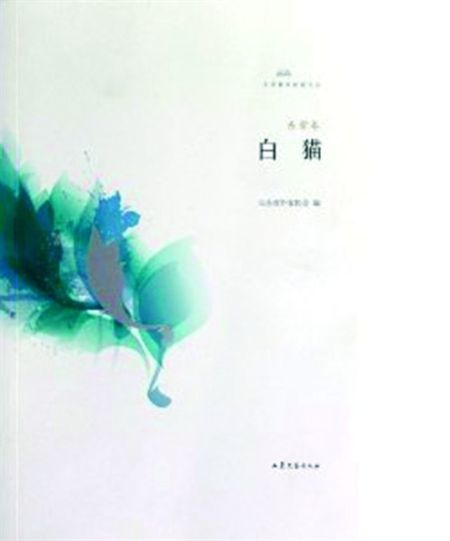
簡介
本名戚慧貞,創作長篇《好日子就要來了》及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若干。出版中篇小說集《天涯近》、《被復習的愛情》、《白貓》。曾榮獲人民文學獎、中國作家獎、泰山文藝獎、《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獎等獎項。
通過小切口尋找大疼痛
盡管在寫作方面成就斐然,但東紫坦言,并不認為自己已經成名——對她來說沒有這個概念。她表示,只是有那么幾個作品處理得好一些,得到了一些老師的肯定和讀者的喜歡而已。在她眼中,所謂的成就、獲獎等,其實跟作品本身、作者創作沒有直接關系,那是作品完成后在流傳的過程中產生的。“即使這一部作品反響再好、獲獎再大,也依然抵消不了創作下一部作品時,孤軍奮戰的艱辛、孤獨甚或恐慌。當然,獲獎等在一定程度上——特別對我這種正在努力成長的寫作者而言,還是有很大益處的——會增加寫作的信心,會感受到被別人關注的溫暖,這些對堅持文學創作都是有幫助的。”
山東商報:您將自己的文學道路分為愛好和執著兩個部分?
東紫: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讀初中,那是個詩社在祖國大地上處處盛開的年代,我的語文老師王世聯是農民詩社《山地》的主編,社長張榮山去聽他講課時和我“同桌”,作為主編的得意弟子和“社長的同桌”,我榮幸地成為他們詩社的幫工——幫著刻板、油印、裝訂,目睹了詩歌帶給他們的快樂、分享、友誼、愛情……那一切,對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既新奇又魔力無窮。我刻著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聞著文字散發出的神秘氣息,就這樣愛上了文學。偶爾,也學著老師的樣子寫點什么。偶爾寫點什么,是我2000年之前的“愛好”狀態;之后,當我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中只有寫作是相對優質的一部分,意識到不認真地對待文學就等于不認真地對待生命時,才開始“執著”的階段。
山東商報:女作家的身份,對創作方面有何影響?
東紫:作為女作家,我深刻地認識到——每一位女作家都特別不容易,我們為堅持文學創作往往比男性作家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堅守。所以,我在看女作家的作品或看她本人時,常常是心里充滿了疼惜。不說別的方面,就家庭中的角色來說,我們都知道一個母親的付出和擔當是可歌可泣的,何況我們還要擠出精力和心血來兼顧作家的角色。就我個人來說,雖說2000年后進入“執著”階段,其實也只是在理念上覺得這輩子要和文學糾纏到底,但在實際行動上是拿不出足夠多的精力來對待。我在山東中醫藥大學二附院工作,周一到周五要上班,周六要帶孩子,只有清凈的周日——孩子沒有感冒發燒、家中沒有急需打理的家務時,才屬于我的文學創作。這也是我作品少的一個原因,一個自我寬解自我原諒的借口。
山東商報:三十而立時有過恐慌,現在呢?
東紫:說實在的,恐慌感一直都存在著,只是某個階段強烈些某個階段相對弱一些罷了。接近三十歲的時候,是特別恐慌了一陣,甚至到了輕微抑郁癥的地步——那時,面對三十而立的古訓,檢看自己的生命,發現自己一事無成,一無是處——曾經還算光鮮的容顏開始衰老,曾經繽紛的夢想都僅僅是個夢,世俗的壓力逼迫你不得不說服自己去平凡,平常,平庸,去走母親走過的路——結婚生子操持家務——這時卻發現自己在婚戀的市場上并不受歡迎……那真叫一個郁悶恐慌。因為文學,熬過了那個階段。當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恐慌感淡了下去——寫作成了安慰生命恐慌的理由——我不是一事無成,我在堅持寫作呢。現在,恐慌感又強烈很多,因為意識到人到中年依然沒有把自己熱愛的寫作做好,意識到再不努力就會因為衰老、病痛等原因影響寫作。
談及成為山東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后的感受,東紫坦言,覺得寫作不再絕對是個人孤獨的事情了。“有一個組織,有一幫人,在關注你,關懷你,在盼望你寫得好,活得好。這種感覺很溫暖人。
山東商報:去年8月底的圖博會中國作家館“山東主賓省”活動中,您曾代表山東作家發言,當時談到“文學是最公正的,只要我們真誠地去對待它,它就會真誠的回報我們。”
東紫:這種回報,不僅僅是作品得到了發表、贊揚,它最大的回報是成為我們生命的支撐——因為它,我們生命中所遭遇所承受的一切不公、不幸、屈辱、挫折等等,都能成為可利用的材料,成為寫作時深入描寫人物生命體驗的直接經驗。由此,寫作成為我們日常的保健理療師,把那些容易導致人氣滯血瘀的東西,進行了排解轉化。
山東商報:您藥師的工作身份,對于寫作來說提供了靈感還是束縛了寫作的自由和時間?
東紫:在醫院工作,雖然很忙碌,但它畢竟是一個救治生命的場所,把身心健康和不健康的人集合到同一個空間里,使得我有了更豐富的觀察和體驗。這也是我的作品能夠有“小切口,大疼痛”(李掖平老師評語)的一個重要原因吧。其實,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用來深入耕種的自留地,醫院就是我的那塊自留地。在這里,我也想借此機會向那些多年來理解我支持我的醫院領導和同事們表示感謝,每每有作家朋友談到在單位里不敢讓人知道自己寫作——怕領導對其有看法時,我就覺得自己很幸福。
山東商報:聽說您剛寫完中篇《母雞小史》,寫作的動因是什么?
東紫:聽到了一個孤寡老太養雞,雞屢遭偷竊的事,這讓我意識到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存在著很多的問題,這個老太太的形象也讓我很心疼,就決定創作一個小說,希望通過這個小說讓讀到它的人有所感觸有所感動有所思考甚至有所行動吧。
山東商報:下一步的創作計劃是什么?
東紫:要看自己的時間,如果能有比較整的時間,我希望能寫那個早已做好了功課的長篇,就因為時間短缺才遲遲不敢動筆。
“評”說
胡平(原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東紫的小說筆力銳利,常刺入人性中薄弱的間隙,但筆調又是間離和幽默的,不斷以喜劇的色澤沖淡悲劇的壓抑,從中獲得一種奇特的修辭效果。東紫對人性的觀察是全面的、健康的,而不是褊狹和極端的,這種觀察也造成了她的創作的敦厚氣質。
李掖平(山東省作協副主席):東紫的小說擅長在人性的善惡復雜糾結下,在生活的尷尬無奈中,在感情的微妙邊緣處,描寫個體生命悲歡離合的遭遇,拿捏其靈魂深處的傷痛,文字時而犀利冷峭時而纏綿悱惻,搖曳出一種迷人的風情。
張麗軍(山東師范大學教授):東紫作品中對人性的復雜性的展現,我覺得在當代作家中是非常獨特的。作品語言描寫細致入微,體驗非常獨到。這種對語言的能力和這種思想的深刻程度,使東紫在70后作家中能夠脫穎而出。
馬兵(山東大學副教授):東紫的所有小說都可以用她的一個小說的名字《顯微鏡》來命名。所謂“顯微鏡”就是把人放在一個極端的情境中,把人性無限地放大,借此來考察人性的多元和復雜。
房偉(山東師范大學副教授):東紫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女作家。她前期有一些非常先鋒化的作品,之后在創作中可能有一個自我調整,使日常化、女性體驗和她的這種哲學深度相結合,創造了一種非常獨特的人文體驗。從某種角度來說是一種“刀鋒上的舞蹈”。
趙月斌(省作協一級作家):東紫的小說有一種強烈的偵探意味,很吊人胃口,又很好玩,能讓你津津有味地讀下去。東紫把這種偵探模式引入所謂嚴肅文學,可以說是她的高明之處,她懂得把小說寫得迷局重重,扣人心弦。
她寫
白貓一動不動。我突然想起五年前母親臨終的時刻。那也是個深夜,我孤獨地守在她的病床前,眼睜睜地看著她一點一點地衰亡。遠離。我被無能為力的悲哀控制了,看著自己的雙手痛哭不已。年富力強的它們竟然成為了一種擺設,絲毫沒有用處。幼年的時候,弱小的它們都能牢牢地拽住媽媽的衣角呀。我撫摸著白貓,生怕在抬手的霎那間丟失了它的呼吸。這一刻,我重新記起了守在親人病床前的強烈感覺——渴望著那呼吸是有形的,是能夠用手牽拽住的。渴望人和死神之間是有繩索的,是能夠由親人組成隊伍力拔的。但是,生命在危機的時刻總是孤獨的。孤獨地抗爭。——《白貓》
她看著那個無法伸展成葉片的芽苞,那樹林一樣擁擠著拼命消散自身的顏色博取別人一聲喝彩的短暫,想到那其實就是一個個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臺上沒有兩只水袖的女人。或許水袖是有兩只的,但舞動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須是緊握著的,是永遠不能順應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拋撒舞動的。——《春茶》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