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葉廣芩人生的三個W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3月18日10:09 來源:北京日報 周曉華讀她的文字,無論幽默還是調侃,底色總感蒼涼。只是近些年,通會之際,人文俱老,連蒼涼也化在水三點火兩重的一個“淡”字中了。
葉廣芩人生的三個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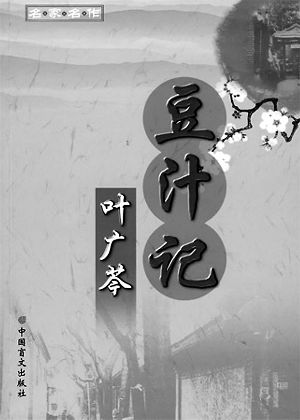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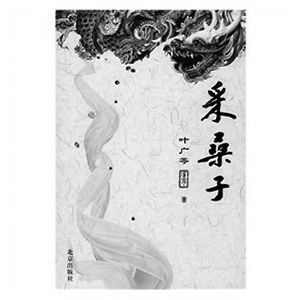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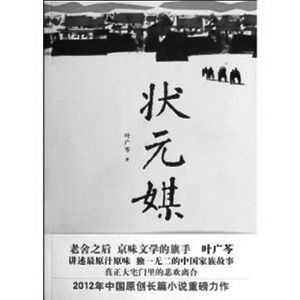
 葉廣芩 孟迷 攝
葉廣芩 孟迷 攝2014年初,根據葉廣芩的長篇小說《青木川》改編的開年大戲《一代梟雄》在多家衛視臺熱播。很多人不解,以文雅沉靜文風見長的女作家何以能與匪氣縱橫、霸氣十足的匪戲掛鉤,但是這個鉤還就掛上了,很是奇妙。
去拜訪她,按照她的指引,我地鐵轉地鐵轉地鐵再倒公交來到她住的樓門口。
她下樓來接我,穿得很普通,藍牛仔褲,紅棉襖,大風里,兩手裹著衣襟。
微卷的齊耳短發服帖地攏在腦后,從前面看覺得她是盤的長發,兩個獨特的大耳釘像兩朵明麗的花開在耳朵上,就是這一點用心,她整個人有了別樣的韻味。
熟悉她的讀者都知道她濃厚的北京情結,一個北京的女兒,“文革”到了陜西,一走40年,退休才終于回來。
“看君已作無家客,猶是逢人說故鄉”。《鳳還巢》只是她寫的小說,可小說里的那份情感卻實實在在是她自己的。聽她用地道的北京話慢條斯理地說著她心心念念的故鄉,她離家、回家的經歷,總覺得心里硌得慌。
進屋,屋里陳設簡單,對門條案上有溥儒的書法《蝶戀花》,窗明幾凈,被北京冬陽亮亮滿滿地抱著,舒適又安靜。
她泡了茶,若有若無的茉莉茶香里浮浮沉沉她的記憶。
1.
時間: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地點:北平
人物:丫丫
解放前,父親在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書,那是今日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我的三大爺也在這所學校工作……老哥兒倆不惟畫畫得好,而且戲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飯后,老哥兒倆常坐在金魚缸前、海棠樹下,拉琴自娛。那琴聲脆亮悠揚,美妙動聽,達到一種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幾位兄長亦各充角色,生旦凈末丑霎時湊全,笙笛鑼镲也是現成的,嗚哩哇啦一臺戲就此開場。首場便是《打漁殺家》,《打漁殺家》完了就演《空城計》,然后,《甘露寺》接著《盜御馬》,《吊金龜》接著《望江亭》,戲一折連著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母親說:狐仙都出來了,散了吧。聽母親說狐仙出來了,大家這才收家伙,各回各的屋。——《頤和園的寂寞》
海棠樹下,琴聲悠揚,戲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文中這個大家庭如此熱鬧的時候,她還沒有出生。可是對于她,那一段時光她并未缺席,那些家族的往事通過父親母親老哥老姐親戚朋友的講述絲絲縷縷融進她的骨血中。
她也許一直未曾意識到它們的潛伏,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她從心底從筆端牽出記憶的長線,將那個時代拉進自己生命,又呈現在讀者眼前。因此有了《本是同根生》《祖墳》,再有了后來的《采桑子》《狀元媒》等系列小說。
小說里,丫丫是金家14個孩子中的老小,老宅三進的四合院中,14個兄弟姐妹出進盤桓、哭笑玩鬧、爭吵打斗,演繹的故事無數,亦生出情感無數。丫丫見證了一個八旗世家的興衰,也身在其中體味著、反思著。
幾十年如滾針氈針針見血的人生經歷,讓小說的文字中無處不見她真切的感受,所以走進她文字再走出時,主角“丫丫”的經歷便和現實中的她高度重合起來。
然而小說畢竟是小說,故事里的事,說不是也是,是也不是。讀者將那小說里的“我”當成她本人,按圖索驥地去對照她的家事時,總讓她覺得尷尬,因為那里多是好奇和牽強附會的猜測。
2.
時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地點:陜西
人物:工人護士記者葉廣芩
一九六八年的一個早晨,我要離家了。
黎明的光淡淡地籠罩著城東這座古老的院落……老榆樹在院中是一動不動的靜,它是我兒時的伙伴,我在它的身上蕩過秋千,捋過榆錢兒,那粗壯的枝干里收藏了我數不清的童趣和這個家族太多的故事。這棵樹,這個家,這座城市已不屬于我……戶口是前天注銷的,派出所的民警將注銷的藍印平靜而冷漠朝我的名字蓋下去的時候,意味著懷揣著這張巴掌大的戶口卡片我要離開生活了十幾年的故鄉,只身奔向大西北,奔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扎根。這是命運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別無選擇。——《離家的時候》
說到去陜西,她用的是 “甩出去”。
離家,對她是一種撕裂,與故土與親人與熟悉生活的撕裂。到現在,她不喜歡坐火車,也不喜歡在火車站的感覺。1968年,離開北京那個早晨,妹妹舉著一個燒餅,追著火車哭喊的景象,是她心里永遠的痛。
到了陜西,她先在黃河灘上養豬和務農,后來被調進工廠。1983年,她被調到報社由護士變為記者編輯。
簡歷中短短幾句話,她用了幾十年去經歷去體味,體味人生的坎坷,命運的蹂躪。
叢維熙說過:“生活和命運把誰蹂躪了一番之后,才會把文學給你。”
“你不能跟命運較勁,不能跟周圍的人較勁,你最好的辦法就是跟自己較勁。韓非子說,‘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32歲,當護士的她用值夜班時間寫出的第一篇小說發表。
“我第一篇小說的編輯是路遙,那時他是《延河》編輯部小說組組長。他給我很鄭重地寫了封信,稱贊了這篇小說。還在信里問我是個怎么樣的人。后來,沒見過面的路遙推薦我加入了省作協的讀書班,脫產三個月,集中學習,專門研究文學創作。細想我能走上文學道路,從一個普通的護士到一個專業作家,跟路遙大有關聯,他是我進入文學之門的領路人……”
也許是因為太關注文學創作,在廠里看起來不務正業的她被推薦到報社,成了一名記者,“我在報社工作跑的是林業口,跑遍了秦嶺的犄角旮旯,到處去基層了解,我結交了很多基層朋友,深山老林里總有清新和真實的東西傳遞來。”
也是這樣一段到處跑的歷練,讓她真正了解陜西,讓她明白,寶貝并非像盜墓電影上演的那樣光芒四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往往并不引人注目,甚至可能是黯淡無光的,就像最初她看見的西安。
“在陜西,你走在路上,看見路邊有一些傾斜的石碑,后邊是荒冢。你走過去一看,碑額是大唐國長公主墓。長公主,唐玄宗的姐妹呀。碑額是唐玄宗寫的,唐隸;碑文是駙馬寫的,寫到武則天時代的一次宮廷宴會,武則天令子弟們演節目,李隆基男扮女裝,吹奏一段樂曲,他當時7歲。公主的墓碑,寫的多是生活細節。它傾斜在麥田里,如果你不停下來,不去品味,你體會不到。在那里,很多時候,你不經意就走進了歷史的皺褶里。”
陜西的生活給了她一種胸懷。
3.
時間: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地點:日本
人物:主婦 學生 葉廣芩
一到日本,我的身份便變成了“家族滯在”,“家族滯在”是個日本詞兒,中國沒這一說法,聽著別扭。說白了,意思就是“沒有工作的家屬”,在日本隨著掙錢者居住,是個“附帶品”。作為“附帶”,我每年得在日本居住幾個月,承擔一下“主婦”的責任。——《主婦雜記》
上世紀90年代初,丈夫作為交流學者到日本,在日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她隨丈夫一起去了日本。
忽然由一名滿世界跑的記者變成一個“家族滯在”,對她,實在是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她不能想象自己天天的生活就是干家務,就是怎么用微波爐轉雞,怎么跟爬上陽臺的藤蔓作戰,怎么騎著車去商店尋找中國的松花蛋……
她不能讓這些變成生活的全部。靠自己的努力,她進入了日本千葉大學法經學部學習。當然,能夠順利地進入大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她的日語基礎好,而這個日語基礎卻是她在陜西獨自放豬的收獲。當年她坐在黃河灘上背日語五十音圖的時候,絕想不到若干年后,會在日本的千葉大學派上用場……
在大學,她研究的課題是“二戰時期殘留在中國的日本歸國者們回到日本后在日本法律、經濟上存在的問題及改進辦法”。她進行了大量的采訪調查,采訪回日本認親、定居的日本殘留孤兒,還深入到日本的最基層,調查、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資料。
讀書期間,她和很多留學生一樣,走出家門去打工。在飯館端過盤子刷過碗、在鋼窗廠當過搬運工、在火腿廠貼過標簽、在貓狗美容店給人家洗過狗……這也讓她真正接觸到了日本的真實生活。
在日本的時間,她停下了創作,沒有動筆寫過小說。
而后來,回到國內的她,將這些資料篩選、消化、吸收,又在東北地區走訪了國內的殘留孤兒和他們的家庭,寫出了以日本殘留孤兒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戰爭孤兒》和《霧》《霜》《霞》等作品。
“1968年我來到陜西,使我有了與北京完全不同的生存環境和人生體驗;后來我到日本去學習,研究二戰,這對我是完全陌生的領域,就是這樣使我與中國文化拉開了距離,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我們的民族與文化,無異給我開辟了一片更為廣闊的視野。這段生活對我也是非常重要。”
4.
時間: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
地點:陜西
人物:作家葉廣芩
90年代中期,我從國外回來后,許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變,當然,這之中更大的是我個人觀念的改變。1994年我成了“待業中年”,這與我不受羈絆、桀驁狂猖的性情有關,看似是被人推上了絕路,其實不啻是另一種生機的轉折。——《采桑子》后記
“從日本回來,原單位的工作沒了。像我這樣傳統的人,總還希望有個單位管著你。忽然沒人管你了,在我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去找(賈)平凹,他那時在西安市文聯。我說我現在沒工作了、也沒工資了,我想到你這兒來,你要救我。后來我進入文聯創研室,省作協的(陳)忠實給我做了推薦人。我一生都感念他們的知遇之恩。”
從報社跨入文聯,是1995年的1月1日。新來的她,被安排在元旦那天值班。“文聯是個窮單位,破桌子爛板凳,窗戶碎了,糊著破報紙。沒有暖氣,我就裹著棉大衣坐在電話旁邊,透過爛玻璃,看窗外的風吹著枯樹枝,麻雀在樹上跳來跳去,一上午靜悄悄的,連個電話也沒有……”
文聯值班室的冷和靜讓她對以后的生活狀態有了最好的認識,現在她是一個職業作家了,她明白自己需要沉下心,多思考。
調入文聯后,時間充裕了,沒有任何顧慮的她,創作有了新的突破。
“但寫真情并實境,任他埋沒與流傳。”家族小說《本是同根生》發表后,產生很大反響,爾后是《祖墳》和一系列的小說,“如樹上的果子一樣,人大約也是到了該熟的時候,我寫的一些作品開始受到了讀者的關注,那些塵封已久的人和事,個人的一些難忘的體驗,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筆端,這似乎不是我的主觀意志所能左右的。”
48歲,她寫出點名堂來了。
5.
時間:二十一世紀
地點:北京
人物:葉廣芩
身在北京的人不會理解我,北京的家是殘存在我心深處可望不可即的情愫,敏感、柔軟、脆弱、永遠的怕人提及。離家四十多年,人有了太多的改變,不變的惟有這情……所以我必須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家,以彌補我多年的心理缺失。——《鳳還巢》
采訪前電話她,問去她家拜訪會不會不方便?
她說:沒什么不方便的。
前幾年她退休了,退休之前,她未雨綢繆地在北京買了房,建立了自己的家。2013年底,她榮獲“《十月》創刊35周年最具影響力作品獎”和第十屆“十月文學獎”,回來領獎,她在北京住一陣子。
戶口在陜西,退休工資是陜西發她,她從形式到內容都該是陜西作家,可她總覺得游離和隔膜。就在她去《十月》雜志領獎的前幾天,一個名為“文學陜軍再出發”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會上介紹到她,總有點不大好描述,雖然她的作品也有不少是寫陜西的,可談到她的代表作,大家先想的常常是她的“京味兒”。
為了找到在北京的歸屬感,她讓妹妹去給她辦北京的暫住證。為了能辦這個暫住證,她申請加入北京作協,“我和北京作協說,我是北京的女兒,你們得收留我。說個不恰當的比喻,曹操成就事業后還知道把蔡文姬重金贖回來呢,我不要你們贖,收留我就好了。”話是玩笑著說的,內心卻認真而嚴肅。
“雖然不辦暫住證在北京也一樣生活,這些都像是形式,可老太太需要這個形式。暫住證一辦,我就盼著,半年以后我坐車呀去公園呀,就和北京人一樣了。”由此說,這樣的形式確也是一種實質內容,尋找故鄉對自己的認可,也確認自己和根的關聯。
四五歲的時候,父母照顧不過來她,她便和三哥三嫂一起住在頤和園里的一個小院里。平常他們上班,她就一個人在偌大的頤和園里呆著,走遍了園中的角角落落,甚至園中的每一個季節,尋找著也許根本就不存在的叫“哈拉悶”的精靈。
六歲她失去父親,也失去了經濟來源。貧困的生活,靠典當為生的屈辱,在她心上刻下深深的傷痕。19歲,她離開身患絕癥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妹,把家里最后一張波斯毯換成一床棉被只身去陜西,一去經年。
插過隊、上過山、在各種磨難中體味著生命的脆弱和命運的殘酷。雖在陜西多年,她的根卻無法改變,說話還是京腔,愛吃的還是北京口味。
然而再回到北京,記憶里的感覺卻已難尋。站在樓上看北京的夜,燈火一片,有點深入不下去,也不知道往哪深入,于是在書里找,在書里寫,在書里回憶。有時候半夜醒來,不知自己在哪睡著,也不知是在小時候還是已經老了。
她常想人生是悲涼的、寂寞的,即便是在熱鬧的人群里,內心的孤單也是無可替代。但這些年,許多的情感水分都變作淚水蒸發,她漸漸不再為自己過去的經歷過多感傷了。
有工資有稿費衣食無憂,她很知足。讓她覺得幸福的,是她有一群年輕的知她懂她的讀者。
中秋節時候,她和他們一塊兒到頤和園景福閣賞月,初冬時候,她和他們一塊兒到國家大劇院聽昆曲;在網上,他們和她交流看戲,討論美食,期盼等待她的新作,也積極而有建設性地給她的寫作提供思路和素材。
“昨天在群里(她有個叫豆汁記的QQ群),他們問我晚上吃什么,我說就熬點紅豆粥吧。過了半小時,聽見有人敲我家的門,一開門,原來是群里的朋友,他說聽您說煮了紅豆粥,給您帶點醬肘子來,配著吃正好!特別好,這幫年輕人。他們中好些個戲也唱得好,不是那種不著調的。有一次還邀請我一起來著,我說我要唱也行,但得買青衣的練功服老生的髯口然后唱花臉……他們就笑我,說您和金家老五一樣荒唐了……”說著,大笑起來,陽光盈在兩個酒窩里。
“問問您,通常是什么樣的寫作習慣呢?有的作家早晨從中午開始。”
“我生活很規律,早晨六點起來,要是沒事不出門就寫,晚上7點多就休息,看看電視,我不熬夜。他們喜歡晚上寫,也許是因為白天太亂,事情多,靜不下來。我不存在,我一個人,很安靜。”
聊著說著,已近中午。向她告辭,問她自己在家怎么吃午飯。
“剛才不是說了,昨晚熬了紅豆粥。好多呢,繼續喝。”
這個美食家對自己的照顧實在稱不上周到,吃三頓粥也許還是她比較正常的生活狀態。聽說,有時候她在電腦前頭敲字,一敲一整天,只吃一頓早點。寫字的時候,一頭進去,什么都顧不上了,實在餓得夠嗆,就去妹妹家里吃頓好的。
穿鞋出門,回頭看迎門的八仙桌上,光影長腳已挪了地兒。
“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唯見月寒日暖,來煎人壽。”想起她寫進《瘦盡燈花又一宵》中的句子。
她送出門來,按好電梯。
電梯下行,她的笑容疊合在許多文字里,竟有些恍惚。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