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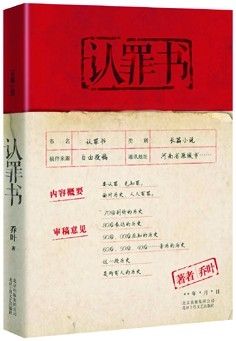
在面對當下的寫作中,人性往往是無法繞過的話題。急躁的社會氛圍、游移不定的心態,使得不少人隱藏起自己的內心,帶著面具生活。對于這些善于矯飾、長于辯駁的人而言,“知罪”與“認罪”儼然成為避之而不及的“陌生詞匯”。近期,河南女作家喬葉推出了她的長篇小說新作《認罪書》,作品從女主人公“金金”的敘述展開,由“現有之罪”回溯“原初之罪”,以交叉敘事結構展開,在現實與記憶的交錯中探討特殊歷史時期中社會畸變對于人性隱秘而漫長的侵蝕。
“由面對個人的‘小內’,轉向了面對群體的‘大內’”
記者:在您的許多作品中,女性敘事不僅是故事發展的基本構架,也構成了文本本身充滿情感特質的推動力。雖然以一種相對獨立的“書中書”的方式來形成結構,但您的新作《認罪書》在情節設置上可以說也沿用了這一特質。對您來說,這種第一人稱視角的女性敘事策略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
喬葉:對讀者而言,閱讀時第一人稱更有貼近感。作為寫作者,對我而言,第一人稱是可以相對穩定的敘述角度。第一人稱有很多局限性,我喜歡這種局限性。對于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我一直缺乏強有力的敘述自信。因為我知道,我不是上帝,我本身是那么有局限性,我不能無視自己的局限性。而在《認罪書》中,因為“我”也就是女主人公金金的局限性,小說的懸念和張力才得以慢慢展開和延伸。她不知道的是那么多,所以她會一步步走向真相深處。至于女性敘事策略,因為我是女性,所以這就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記者:與您以往的作品相比,《認罪書》似乎有意識地在做一種由內向外的轉變,從以前對于個人心靈的探索逐漸向對于群體心理、時代心理的探索,這方面的轉變由何而來?
喬葉:你覺得是在由內向外嗎?我覺得是在由內向內,不過是從一種內轉向了另一種內,是由面對個人的‘小內’,轉向了面對群體的‘大內’。至于轉變的原因,很簡單地說,是因為年齡的增長,因為文學經驗的豐富,因為思考面的拓寬……各種因素作用下,逐漸不滿足于所謂的日常生活書寫,想要探究更深層的領域,做出更有質量的表達。而施戰軍先生在談及《認罪書》時曾說過一段話,我覺得是很好的典型的評論家式的總結:“隨著視野的擴張和寫作的成熟,青年作家定會建構出自己的話語世界。置身其中的生活,何嘗不是個人與歷史血肉相連的旅程。言語、動作、神情、感觸……一經沉淀和梳理,‘個人’便不再孤立和單薄,自我的人生、經歷和經驗,不能不和他人的心思以及繁多的關系交織纏繞,從而再自然不過地參與了對生命、時代、歷史的精神整合。”
記者:作為長篇小說,《認罪書》的交叉敘事結構無疑對寫作者提出了很高要求。多線交叉、多重敘事口吻的敘述結構,并造成了一定的閱讀難度。這樣的寫法在您以往的作品中很少會出現,為什么會采取這樣的結構?
喬葉:決定結構的只能是內容。因為小說中的多重敘述口吻,也因為小說里的多重故事情節以及多層次的時間段落,所以我衡量再三,決定采用交叉敘事結構。這是必然的選擇。閱讀難度是必須的,也是我想要的。我知道這個小說故事性很強,所以擔心讀者讀得過于順暢,只被故事的洪流裹挾而下。我希望這些難度的存在能夠使得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時時稍作停頓,想一想,靜一靜,然后再繼續閱讀下去。
記者:就閱讀感覺而言,這種多線交叉的結構對讀者的注意力也有很高的要求,事件、人物繁多,再加上類似獨白的“碎片”和穿插著的“編者注”,難免會讓讀者有一些零碎、無從下手的感覺。身為作者,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喬葉:“碎片”和“編者注”是我刻意設置的,“碎片”是金金在講述往昔告一段落時回到當下的獨白,呈現著與往昔相比她心態和心智的鮮明變化。“編者注”是象征最冷漠、最沒有溫度、最沒有感情色彩的官方話語,用來與那些濃重的個人敘述形成對照關系。這兩種形式確實看起來都是零碎,沒有耐心的讀者可以跳過去不讀,只讀故事本身。事件也并不算多,只是比較有歷史縱深度。參與主體故事敘述的不到十個人,對于一個三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而言,我覺得也不算繁多。如果有讀者覺得這都算問題,那當然首先可能是我寫得不好,筆力太淺。但話說回來,如果閱讀的時候注意力不高,耐心不夠,這樣的讀者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讀者———如果沒有能力進行深閱讀,那么無論讀什么作品,閱讀質量都很值得懷疑。
“如果不反思和警惕,我們一步就可以回到從前”
記者:在一個訪談中,您曾表示文學需要穿透新聞事件的表面,幫助讀者看到人性深處的東西。在《認罪書》的創作過程中,這方面的嘗試似乎沒有過多深入,夾雜了大量對于社會當下問題乃至新聞事件的錄入,甚至搬出對于專家反思“文革”的虛構式訪談,想請教一下這些要素對于作品本身的意義是什么?
喬葉:如果我要以一個新聞事件為主體來寫小說,那么我一定會努力讓讀者從新聞事件中去看到人性深處的東西,但《認罪書》 的故事主體不是新聞事件,而是金金、梁知、梅梅、梅好等系列人物的酷烈命運和罪責深究,這些才是小說的主干。一些社會當下問題和新聞事件的錄入不過是主干之外的旁逸斜出,它們的作用是側證主干,當然不能太費筆墨。第359頁的訪談是整個小說最重要的那個核。作為小說的一部分,它當然是虛構的,但它所言說的東西又最真實不過了,我覺得。
記者:在閱讀作品時,前半部作品對于情感、倫理的筆墨渲染較多,而后半部作品隨著“金金”對于過往的執著探索,對于多人物的回溯以一個個片段的形式展開,如果說是突出“罪”,就閱讀來說,似乎有些刻意,并沖淡了故事性,打亂了原本的敘事節奏。不知您如何理解?
喬葉:我跟朋友開玩笑說過,《認罪書》就是借殼上市。借的是婚外戀的殼,上的認罪的市。因為要借殼,所以前半部要寫情感,寫倫理,借過了殼,后半部就深入認罪。而所謂的“罪”,在作品中是處處都有的,只是需要智慧的讀者跟隨著金金去認知、認證、認定,就是這樣。整個小說的故事性太強,能如此沖淡一些也好。我覺得自己做得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太過刻意。有眼力毒辣的朋友一語中的:“你用力過度。”可要我用力不夠我也做不到。
記者:在這部作品中,作為故事的主角、陳述者和情節發展的牽引者,“金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也有讀者提出,作為一個人物而言,“金金”并不“在場”,似乎她的所作所為都是為推動故事發展而服務,而并非傳統意義上“故事為塑造人物服務”,您如何看待?
喬葉:金金并不在場嗎?我覺得她處處在場。她沒有在歷史的場,在的是當下的場。這個當下在場的人一步步推動故事發展,就是我的初衷所在。我不覺得一定得“故事為塑造人物服務”,我覺得故事和人物可以互相服務。金金固然在推動故事發展,不過故事發展到最后,金金不是也脫胎換骨了嗎?
記者:《認罪書》并非明確指出“原罪”,但作品直指“文革”。書寫“文革”,卻并不站在“文革”當場,而是在當代情景下反思“文革”所帶來的持續影響,這在當下的書寫中相當罕見且難能可貴。為什么會選擇這樣的切入角度?
喬葉:“書寫‘文革’,卻并不站在‘文革’當場”,一方面這是我作為寫作者的局限決定的。我并不曾親歷“文革”,所以進行在場敘述總是覺得膽怯。另一方面,從當下切入也是尋思很久的選擇。“文革”已經遠去,但正如陳毅之子陳小魯所言:“其實當下社會還充斥著暴戾之氣,‘文革’ 的基因從來沒有離我們遠去。”亦如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韓敬群先生所言:“路漫漫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對橫行與潛伏于歷史與我們內心中的罪與惡,更當如是。我曾經以為我們已經度越了從前,其實我們一步就可以回到從前。”正是因為對他們的話有很深的體認,所以我選擇了當下角度切入。———我們當下的許多問題不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一切都有源可尋。而我認為,“文革”就是比較切近的一個源頭。
記者:從一定程度上說,所“認”的“罪”其實都很難說是實際所陳述的罪狀,而是歷史特殊時期對于人心和人性造成的畸變。這種畸變潛移默化,可以說間接影響和改變了這一輩人甚至并未受“文革”沖擊的下一輩人的思想和行為。不知道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您如何闡釋在作品中的這一層蘊意?
喬葉:我覺得您的理解非常正確,這個問題問得也真好,我嘗試著來回答一下:正因為這些罪都很難說是上條上款的實際罪狀,所以這也正是我想探究和表達的。寫這個小說前,我在網上看過一個人物紀錄片,叫《我是殺人犯》,主角是在16歲那年殺人的,那一年是1967年。我寫的時候想起了這個人,我想:是從那些人直接殺人的角度寫呢?還是從誰都沒有親自動手殺人所以誰都可以覺得自己無辜這個角度寫呢?最終,我決定,就從后一種角度寫。———我堅信,“文革”中盡管很多人都殺了人,但是和自認為沒有殺人實際上也在殺人的人相比,殺人的人還是少的。自認為沒有罪的人一定是絕大多數。這絕大多數是最容易被人原諒和自我原諒的絕大多數,當然也是最愛遺忘的對“文革”最保持沉默的絕大多數。從這個角度寫,更微妙,更繁復,也更有我自己認為的意義。———這種對自身應當承擔的責任去回避、推脫、否定和遺忘的習慣作為我們國民性的一種病毒,一直運行在無數人的血液里,從過去流到今天,還會流向明天。如果不去反思和警惕它的存在,那么,真的,我們一步就可以回到從前。也因此,每當看到“80后”、“90后”對《認罪書》進行閱讀和評判的時候,我會尤其感覺欣慰和驚喜。
喬葉,河南省文學院專業作家,河南省作協副主席。出版散文集《天使路過》等十二部,小說專著《最慢的是活著》等八部。多篇小說及散文作品獲莊重文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十月文學獎、北京文學獎、首屆錦繡文學獎、首屆郁達夫小說獎、中國原創小說年度大獎等多個文學獎項。中篇小說《最慢的是活著》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