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楊君磊:寫詩是用文字來完成不可能的事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12月17日10:43 來源:文學報 何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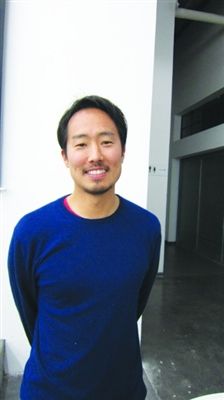 楊君磊
楊君磊 在美國怎樣做一個詩人?美籍華裔詩人楊君磊這樣說:“美國所有的詩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們也要謀生。”楊君磊,在美國出生長大,詩集《水族館》曾在2008年獲得“國際筆會喬伊斯·奧斯特韋爾詩歌獎”,現任《紐約書評》的編輯。編輯和詩人的雙重身份,正是他所說的“詩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日前,他來到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談自己的寫作、翻譯、美國的詩壇和它當下的詩歌出版現狀。
“我對自己的詩歌才能沒那么肯定,因為總有不滿足”
對于楊君磊而言,成為詩人不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而是“長期積累起來的習慣”。小時候他喜歡讀詩,他把這看作自己詩歌生涯的開端。高中時他的詩歌寫作真正開始,最初的目的只是為了好玩,“做一些文字游戲寫著試試看”,最終,文字游戲變成了專業的詩歌寫作。盡管寫了很多年,楊君磊卻說“從來沒有對我的詩歌才能那么肯定,因為總有不滿足的地方”。在他看來,寫詩本身就是要用文字來完成不可能的事情,它是一個不斷往前進的過程。
與許多移民一樣,楊君磊的文化因襲是混合的,父母的中國文化背景激發了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興趣。這種興趣反映在翻譯上,他翻譯了《千家詩》和一些唐宋詩集,還有一部詩集《東坡》。這本《東坡》,最初源自于楊君磊在蘇格蘭做交換留學生時的經歷。大學里有一個小型的詩歌圖書館,某天他在里面閱讀詩歌時發現有一排明信片,其中一張上印著翻譯成英文的蘇東坡的詩,“那首詩翻譯得非常驚艷,讓我感觸特別深,我以前也讀過蘇東坡的詩,現在就更感興趣了。”之后,楊君磊閱讀翻譯了很多蘇軾的詩,集成了這部《東坡》。
詩歌翻譯很困難,中國古典詩詞有格律、韻腳、有規定的長度,但它被翻譯成英文時都不存在了,但楊君磊想出了一些方法:“我翻譯的詩句都構成了比較規整的長方形,這是我在視覺上想模仿古典詩詞的效果;而且每一句中有空格,以此來代表語意的停頓;還用了內部押韻的手法來呈現中國古典詩詞的韻律。”中國古典詩沒有標點,楊君磊用大寫字母來表示每一句的開始,“這是英文這種語言提供我使用的資源”。
“活躍的美國公共空間詩歌推廣”
在美國,似乎找不到一個時期,詩歌顯現出像在上世紀80代中國那樣的重要性。但楊君磊說,這也正是美國詩壇的特點,“美國詩人一直在寫作,即使在經濟衰退時期,詩歌創作也沒有受到任何阻礙”。這幾年,美國詩壇更是有了一些新的變化,“有點類似于當下中國詩壇活躍的狀態,在很多城市里,詩人們常常在一起聊詩讀詩”。尤其是在文化藝術非常發達的紐約,大學、博物館、咖啡廳里不斷會有一些詩歌朗誦會、詩歌問答交流活動,同時還有持續了很多年的“詩在啟動計劃”。
紐約有一個屬于政府的公交管理中心,它下面有一個藝術部門,專門負責在地鐵、車站以及城市的其他地方的藝術裝飾的工作。“詩在啟動計劃”就是其與美國詩歌協會一起合作策劃的活動,“公交管理中心邀請一些詩人,把他們的詩歌放在在公交、地鐵、出租車上,同時請一些藝術家做一些視覺藝術放在上面”,在公共空間里做詩歌的推廣。活動10年前開始,中間曾因經費原因也停過一段時間,“但最近又開始了”。
楊君磊詩集《漸褪的線》中的一首詩最近在活動中展出,他收到許多讀者的回應。有趣的是,有人看到他的詩后,想將其用在電影里,并且在詩歌的基礎上寫了一首歌。“當你的詩歌在公共空間里出現的時候,會發生很多這樣的事情。”楊君磊說。
詩歌繁榮表現:小型出版社涌現
在楊君磊看來,當下美國詩歌的繁榮,最突出的一個表現是涌現了許多小的出版社,出版美國詩人的詩歌和國外譯介詩。“雖然經濟衰退,卻反而給了一些小的出版社以契機,因為成立和維護一個小的出版社并不需要很多的經費,也許會需要一些外部的資助,但主要依靠的并不是經濟上的支持。”而且一些以盈利為目的的出版社,會出版大眾化的讀物,以這些書的收益來支持詩歌出版。
這些小型出版社常常有許多詩人在里面工作,出版的詩集一部分來自自由來稿,還有一部分是編輯本身認識和欣賞的一些詩人的詩歌。印數并不多,“非常非常小的出版社也許一年也就出版2至6本詩集,開印500至1000冊左右”,楊君磊現在工作的《紐約時報》出版社屬于中等大小,出的詩集更多一些,一般開印2000至5000冊。幾年前,《紐約書評》出了一個“詩人系列”,選取全世界各地優秀詩人的詩歌出版,一年四冊,做成口袋書的大小。而楊君磊曾經工作過的新方向出版社,也曾經出版了詩人系列的小冊子,他做過其中李商隱的一冊。
在美國,詩歌的讀者其實并不是很多,相比中國可能更遜色一點,“畢竟中國的人口基數相對較大,而且有閱讀購買文學書籍的傳統”。但在美國,詩歌有自己固定的讀者群,這與歐洲類似,“盡管不是很大眾,但總有人喜歡”。(感謝復旦大學英語系副教授金雯翻譯)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