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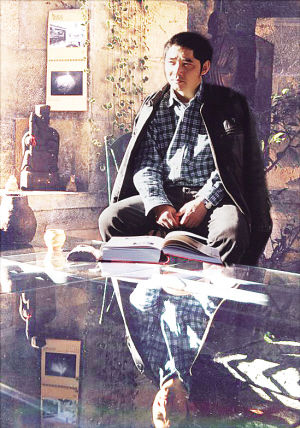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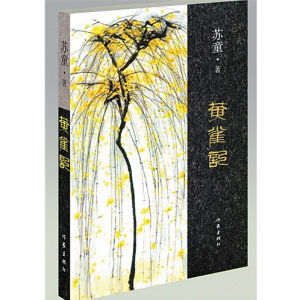
蘇童,中國當代文學先鋒作家代表之一。本名童忠貴,1963年生于蘇州。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著有中短篇小說《園藝》《紅粉》《離婚指南》等,長篇小說《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帶》《河岸》等。今年8月1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黃雀記》延續了蘇童慣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敘事風格和節奏。故事并不復雜,就是一樁上世紀80年代發生的青少年刑事案。分為三章:保潤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
“《黃雀記》是造街運動的一項大工程,我借它探索香椿樹街的魂靈。”
傅小平:讀《黃雀記》通篇沒有讀到“黃雀”;書名呼應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諺語,卻有著非常嚴肅的主題;關注青春期成長等社會問題,但顯然體現了更為宏大的關注和追求。對這樣一部堪為奇特的小說,相信讀者都想知道它究竟是怎么“煉成”的。
蘇童:我的一部分寫作行動,可以說是一場持續的造街行動。造的當然是香椿樹街。以前的好多中短篇文本,包括九十年代的長篇《城北地帶》,都是香椿樹街系列,都是我造的街景。而這次的《黃雀記》,是造街運動的一項大工程,我為這條街道修建了一個廣場,還有一座隱隱約約的廟堂,更多的居民停留在此,獻上他們卑微的香火,以及卑微的祈愿,我借《黃雀記》探索香椿樹街的魂靈。
傅小平:小說有所交叉地分章寫了保潤、柳生、白小姐三個主要人物。特別聯想到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也是以人物對應章節切入敘述。不同之處在于,福克納基本上使用第一人稱視角,他摹寫了不同人物的獨一的語調,讓每個章節都“著”上了完全不同的色彩,雖然我們知道這些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黃雀記》使用的是第三人稱,你盡管提供了三種視角,但透過他們的視角,能直接而清楚感覺到作者的“在場”。我感興趣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怎樣讓各個人物都擁有那種“獨一”的語調,并且讓三種視角有一種“對立而統一”的呈現?
蘇童:說是敘事也好,人物塑造也好,如果做得足夠好,會有神奇的魅力,你能夠傾聽到人物的呼吸,能夠聞到人物嘴里噴發的口氣,在寫作的過程中還會有其他奇跡,比如,你能夠看著人物在你筆下一點點成長,最后比你更有威信,更有力量,變成你的老大。
我想象《黃雀記》的結構是三段體的,如果說形狀,很像一個三角形。保潤、柳生和白小姐是三個角,當然是銳角,失魂的祖父,則是這三角形的中心,或者底色。如果這三角形確實架構成功了,它理應是對立而統一的。
“生活的本相從來不在作家掌控之中,只能靠文本去發現,去辨析。”
傅小平:保潤是這部小說最重要的主角。他經受的冤案,連帶著讓一個家庭陷入分崩離析、萬劫不復的深淵。出乎我預想的是,在小說里,讀不到你的同情。保潤出獄后也是乖戾而邪門的,甚至有點面目可憎。我總感覺在你筆下,很少能感受到你對被命運捉弄的小人物,對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底層人物的同情,有時甚至會明顯感覺到你的憎厭。你是否認為這就是生活的本相?或者在你看來,作家在寫作中只要尊重事實即可,不必表現出個人在道德倫理上的傾向性?
蘇童:我自己覺得在保潤與白小姐身上,我的同情心已經明顯地流露出來了。我只是控制自己,堅決不捅淚腺,以免讓讀者流下任何廉價的即時性的眼淚。生活的本相或事實,從來不在作家的掌控之中,都是靠文本去發現,去辨析的。而作家道德倫理的傾向會以最自然的方式滲透在文本中,不必刻意表現,當然更不必去大喊大叫。
傅小平:某種意義上看,白小姐是小說故事的誘因。事件因她而始,也因她而終。你的女性人物群像,也由此增添了一抹別樣的色調。事實上,你正因為寫了眾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而為人稱道。這些女性盡管個性各異,但能找到隱秘的關聯。她們世俗卻不脫孤絕的氣質;她們甚至可惡但總有可恕之處。面對這些落入凡間的“精靈”,你是有悲憫之情的。這是否能代表你對女性總體的某種認知?
蘇童:我從來不認為我善于寫女性。假如你沒有寫出《包法利夫人》那樣的經典,假如你沒創造過愛瑪這樣的女性形象,你不可以認為自己擅長寫女性。《黃雀記》里的白小姐,大概是我作品中最接“地氣”的一個女性形象。她的身上集合了人與社會的諸種矛盾,在創傷中成長,還未能遺忘創傷,未能解決矛盾,已經隨波逐流,與現實握手言歡了。
“我所信奉的作家與現實生活的美好關系,是高度三公尺的飛行。”
傅小平:很多作家寫當下會不可避免地會將其妖魔化、荒誕化。比如你寫到的暴發戶鄭姐、鄭老板,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離奇古怪的事件,就體現出了這一特點。我想,據此簡單地批評作家無法把握現實會有失偏頗。這大約類似于西方繪畫史上的印象派,作家們要摹寫的是他們“看”到的,感受到的現實,未必是客觀事實層面上的現實。但這樣的真實往往不符合讀者對“作家要直面現實”的期待。那么,把生活中一些原生態的素材經過綜合轉化寫進小說,就是對現實的“正面強攻”嗎?把寫當下認同為作家是否直面現實的依據標準,又有多少合理性?顯見地,真實的、深沉的歷史或許比虛假的、表象的現實更有現實性。
蘇童:對于作家該用什么樣的姿態擁抱現實這個話題,我已經說得太多了。不妨再說一遍,我所信奉的作家與現實生活的美好關系,其實從來不是親密的擁抱,也不是攻擊性的炮火,而是高度三公尺的飛行。這個距離可以想象為一種標準的若即若離的距離,而所謂的飛行姿勢,當然是主張作家關照現實的創造性,以及表達的自由性和排他性,只不過這種飛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其實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地“飛起來”過,更沒計算過那距離是否符合三公尺的理想。
“對我而言,做可持續的小說家的意義大于一個先鋒小說家的意義。”
傅小平:對于“先鋒”這個詞,我一直感到困惑。它是相對于傳統而說的嗎?那么它與傳統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它代表的是一種顛覆和解構的姿態嗎?對于創作而言,僅止于此就顯得過于單薄了。眼下,“先鋒”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具有壟斷性的特權,進而成了創作“進步”與否的標尺。你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先鋒作家。但相比余華、格非他們,從你早年的文學實驗及后來的轉型等看,實際上都不是那么激烈。也因為此,我想你對“先鋒”一說或許會有更客觀的看法。
蘇童:先鋒與古典,其實在文學意義上是平等的,不存在進步與落后之分。作為我個人來說,不同時期的創作面目有很大的不同,恰巧有個階段被納入了先鋒陣營,我不覺得是誤會,只不過對于我而言,做一個可持續的小說家的意義大于一個先鋒小說家的意義,所以,我現在不在先鋒的江湖上,但那個江湖的血氣方剛,于我是一種美好的懷念。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