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徐懷中,原名懷忠,河北邯鄲人,作家。歷任西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研究員、解放軍報社編輯、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員、昆明軍區文化部副部長、八一電影制片廠編劇、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委員。曾獲三級解放勛章。
徐懷中,原名懷忠,河北邯鄲人,作家。歷任西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研究員、解放軍報社編輯、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員、昆明軍區文化部副部長、八一電影制片廠編劇、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委員。曾獲三級解放勛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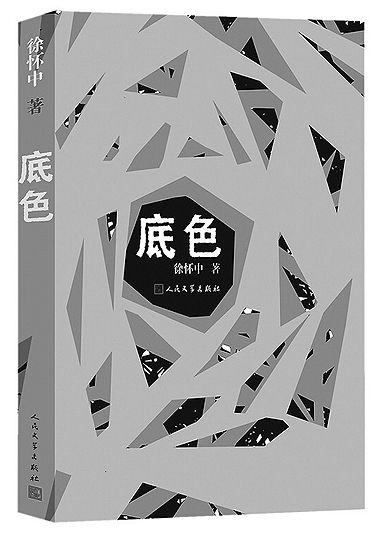 徐懷中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徐懷中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徐懷中(右)在中國作家記者組
徐懷中(右)在中國作家記者組 徐懷中(左)在解放軍藝術學院
徐懷中(左)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蘇軾說他素不解棋,只是喜好看別人對弈,在一旁安坐竟日不以為厭。偶而步入黑白世界,全不在意勝負,“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作家徐懷中也是如此,看高段位的國手們在電視大棋盤旁邊講棋,不到節目結束不離開座位。
圍棋有“打譜”一說,對照棋譜,把前人的名局一著著擺下來,捕捉盤面上此消彼長的每一個玄機,以觸發自己的靈感。或者可以說,長篇非虛構文學《底色》是徐懷中為越戰“打譜”,是他對于“越南流”所作的獨特注腳。“略觀圍棋兮,法于用兵”,戰爭與圍棋同理同義。不僅圍棋,中國的琴棋書畫,都是“觀夫天地萬象之端而為之”,含有東方古老文化深厚的底蘊,透著人生智慧哲理的光輝。而徐懷中說,他雖然在《底色》中多處以棋理評點戰爭風云,仿佛深諳此道,其實只不過是借用了圍棋的一點皮毛而已。
1966年初,徐懷中作為“中國作家記者組”組長,率組從金邊秘密進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總部,自1965年冬至次年春,經歷了四個多月戰地采訪,多次近距離領教過美軍B-52戰略轟炸機“地毯式”轟炸。少年時代,徐懷中曾經在太行山經歷了日軍的“二月大掃蕩”,接著又是“五月大掃蕩”,日軍連續實施鐵壁合圍和篦梳式清剿。沒想到20年多年后,徐懷中又同越南南方軍民一起,見識了美軍陸、海、空立體化的“一月大掃蕩”……
對戰爭的親歷未見得就可以轉化為文學作品,但是徐懷中做到了。他曾經寫出《西線軼事》《阮氏丁香》等具有廣泛影響的作品,《西線軼事》以九萬余讀者直接票選獲得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一名,被譽為“啟蒙了整個軍旅文學的春天”,無愧于“當代戰爭小說的換代之作”的美譽。48年之后,他根據當年的“戰地日記”完成了長篇非虛構作品《底色》(人民文學出版社),真實記錄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位中國軍人作家、記者,在戰火紛飛中的種種情感閱歷與生命體驗,記錄了他對戰爭冷靜客觀而富于哲理的觀察思考。因為有“抗美援越”以及1979年“對越還擊”兩次參戰經歷的“換位”經歷,加之拉開了近半個世紀的時空距離,他獲得的是在以往戰爭中從未有過的深思明悟。
寫作《西線軼事》,徐懷中并沒有過多描繪那場戰爭的“樹冠”,而是著力于地面以下的“根須”部分。
作為一位軍旅作家,只有爭取到最前線去經受種種考驗,積累豐富的戰場體驗,才可能進入文學寫作的殿堂。以往每次去前線,徐懷中像小孩子過新年穿新衣,滿懷激情躍躍欲試。但奔赴“對越還擊作戰”前線,以及寫作《西線軼事》,他的心態要復雜得多、沉重得多。在接受記者采訪的過程中,徐懷中提及當年寫到某些人物和生活細節時,仍禁不住潸然淚下。
突然接到電話通知,領導決定讓他參加戰地采訪小組趕赴云南前線。那時,他剛剛大病初愈,身體非常虛弱,一度出現休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是提著幾大包中藥丸子上的飛機,看上去完全不在狀態。1979年2月17日“對越還擊戰”打響,3月16日戰爭結束,部隊采用“倒卷簾”(即交替掩護)戰術撤回國,徐懷中又隨著作戰部隊到四川樂山訪問某師通信連女子電話班。在連隊寫出了小說《西線軼事》的一部分,他讀給女電話兵們聽,征求她們的意見和建議,姑娘們誰都不說話,一個個低下頭在笑個不停。那笑聲含有女孩子的羞怯與抑制不住的歡樂,顯然她們給予了完全認可。
初稿為中篇,6萬多字,徐懷中是把中越兩方面人物交叉在一起寫的。那時《人民文學》只登載短篇,編輯建議把描寫我方人物故事的章節抽出,緊縮為不超過3萬字的短篇。從初稿中抽出的描寫越方的另一部分文字,經作者重新整理,擬題為《阮氏丁香》,作為《西線軼事》的姊妹篇,發表在《十月》雜志。這一來,倒形成了一種鮮明的效果,對比之下,能夠清晰地看出中越兩國是在怎樣一種特定社會背景下投入這場戰爭的:中國剛剛從十年動亂的夢魘中掙扎出來,是最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越南則是連綿二、三十年遍地烽火剛剛熄滅,未及療治創傷。兩個社會主義鄰國雞犬相聞,他們的戰士卻用對方的語言彼此大叫“繳槍不殺”。
文革剛剛結束,思想解放運動隨之潮涌般到來,《西線軼事》的寫作,實際上是十年浩劫后在心中積郁已久的沉思憤懣,以那場邊界戰爭為井口噴發而出。如果將戰爭比作一株大樹的樹冠,引發戰爭的社會原因就是深扎在泥土中大樹的根須。徐懷中并沒有過多描繪那場戰爭的樹冠,而是著力于地面以下的根須部分。作者寫到,“文革”中有關部門竟發出通知,征集新的國歌歌詞,隨即他發現周圍的一些詞作者興高采烈地投入創作;徐懷中覺得又可笑又可氣:國歌是可以隨便修改的嗎?雖然聶耳、田漢的《義勇軍進行曲》是電影插曲,卻正像是預先為新中國準備好的一首國歌。建國多年,徐懷中仍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所謂“文革”,即是中國害的一場政治天花,但上帝沒把免疫性給予我們。一個國家混亂、落后、貧困,是要挨打的,我們再經受不起了。
徐懷中謙虛地說,“不是《西線軼事》《阮化丁香》寫得多么好,也并非自視頗高,但這兩篇戰爭題材小說,包括刊載于1966年3月3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一篇通訊——《堅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我都十分珍視,誠可謂敝帚自珍。”他說,這篇通訊拿給現在的年輕讀者,他們會感覺枯燥無味,難以下咽。但通訊被譯為越語,在戰火紛飛的南方叢林中廣為傳播,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總部以及各地軍民,每天傍晚準時集體收聽連續廣播。這令徐懷中感動不已。作為一名戰地記者,還要什么?這兩次戰爭,他都是親歷者,自然會在感情上產生某種特殊聯系。他總是自作多情地想:我的這些文字,是為在戰爭中失去生命者和茍活至今的人,保留下來的他們彼此相通的一線信息。
對作者而言,在越南南方的一段生活經歷,是“一頁翻不過去的歷史”。
一次搬家時,偶然找到了近40年前在越南南方作戰地采訪時的兩個日記本,這使徐懷中獲得意外的驚喜。翻閱舊時日記,他似乎可以伸手觸及時空縱深,俯拾流云逝水。從越南南方最高軍事指揮員阮志清大將、越南的“圣女貞德”女副司令員阮氏定,到普通士兵,以及城市武裝的女“交通員”們,徐懷中在他的塑料封面小本上記錄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記錄下戰地生活中那些平平常常又頗有聲色的逸聞趣事,也描述了炸沉美軍“卡德號”航母之役、布林克飯店之戰、公理橋伏擊失敗之憾等重大事件……
徐懷中決定放下其它創作,先著手寫一部長篇非虛構文學《底色》。若以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為順序,這一部新作《底色》在前,本應該列為“上集”,《西線軼事》《阮氏丁香》在后,本應作為“下集”。也就是說,在推延了三、四十年之后,作者才來補寫了“上集”。
上世紀下半葉,以意識形態為分野,世界進入了一個兩極對峙的“冷戰”冰河期,越南戰爭便是在“冷戰”格局中的一場局部“熱戰”。越南這片焦土上撒播的是中、美、蘇彼此牽制激烈競逐的火種,這個“等邊大三角”內部的一壟一畦間,又生發出了中、蘇、越三個社會主義國家形成的“小三角”;就像玉米地里常常套種豆角,高梁地里往往套種倭瓜。比之“大三角”,中、蘇、越“小三角”錯綜復雜的“內部游戲”則是更尖銳、更復雜、更激化。
“中國作家記者組”是在中蘇論戰高潮時出去的,大家學習了“九評”,用“防修反修”理論武裝到了牙齒,隨時準備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但實際上當時尚不能很清晰地觀察那場戰爭和國際關系。在寫作《底色》的前后,徐懷中閱讀了國內外大量關于冷戰史研究的文章以及有關解密檔案,受到啟發,才真正認識到當年這場戰爭是怎樣的多變詭異。
正是在抗美援越激戰猶酣之時,基辛格秘密從南苑機場進入了釣魚臺國賓館,“小球轉動大球”的進程開始了。中美歷來是針尖對麥芒,情勢急轉直下之際倒啟動了建交談判,“栽刺栽刺栽出了一朵花”。徐懷中說,除了“菊香書屋”的主人外,沒有人想得出這一步棋,就是想到了,也未必就敢主動提出來。越南被擠在幾大國的夾縫里,自會施展他們的生存哲學和外交智巧,雖是謙恭低調,卻也時時期待著國際戰略上的超常發揮。“我不能就此得出‘春秋無義戰’的結論,但套種在冷戰中的這場熱戰,決不是以正義或非正義戰爭這種簡單邏輯解釋得清楚的。”
《底色》的寫法,融小說、散文、通訊、政論于一體,同時又顯示出作家長期的知識儲備、文化修養和戰爭思考的底蘊。他確定要用非虛構形式出現,做到觀察高度真實、客觀、公正,強調作者的親歷性,作為自己戎馬半生的一行足印;同時又希望在宏觀展現上更開闊,揭示復雜多變的冷戰國際格局,既有一條時間順序的線索,又力爭突破呆板的回憶,盡可能適應敘事的需要。現在看來,基本上達到了預期效果,但徐懷中也坦言尚有不足:“還應該寫得更活脫靈動一些。有關冷戰與大國關系的議論部分還應該更加鮮明犀利,進一步強化思辨意義。”
一部戰爭史往往講不清楚,究竟是因為什么,兩國之間或是多國之間竟至于妄動干戈。天下興亡系于一身的最高決策者們,不論多么偉大英明,也不免在這里留下敗筆。
在越南南方的四個多月,給徐懷中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記憶。在他看來,越戰和抗日戰爭及抗美援朝有根本的不同。現在到處都在講“非對稱性戰爭”,一個陌生的軍事學術語。其實,越南南方抗擊美國大舉入侵不就是典型的“非對稱性戰爭”嗎?交戰雙方軍力以及支援能力差距之大根本不成比例,使得這個差距已不能說明什么問題。說明問題的是什么呢?是越南人的加重腳踏車,是綁在車座和車把上的兩根木棒棒。直到越戰結束,美國的補給物資還在海港碼頭堆放如山,而越南人多是靠光著腳丫子推著腳踏車馱運大米,來支撐這一場戰爭。
徐懷中在《底色》后記中寫到,1979年中越兩國兵戎相見,這一頁歷史插曲過于沉重,道理上可以講得清楚,但從感情上翻過去這一頁絕不是那么容易。在戰爭生活中,徐懷中不僅看到毀滅和絕望,也看到無限希望和光明,看到永不泯滅的人性光輝。他到南線收容所訪問越南女俘,炮火停息沒幾天,越南女孩子已經在向中方小衛生員遞紙條了:“我覺得你的性格特別好,你可以寫紙條給我嗎?”她全然忘記了不久前她們如何爭先恐后報名參加青年沖鋒隊,誓與“北寇”戰斗到底。
一部戰爭史,往往講不清楚究竟是因為什么,兩國之間或是多國之間竟至于妄動干戈。天下興亡系于一身的最高決策者們,不論多么偉大英明,也不免在這里留下敗筆。所幸的是,人們世世代代經歷多了,也便懂得了拋卻仇恨,越過種種有形無形的警戒線走到一起來,彼此給予同情,給予友善,給予援助。而那個越南女俘,更是不顧一切,把寄托著她無限遐想的一張小紙條遞過去了。她是何等癡心,不受任何觀念的束縛與驅使,僅憑一縷傾慕之情,就足以抵消國家戰爭動員令。人的純粹感情屬于天性,不是任何戰爭力量所能阻擋所能改變得了的。
作為一位具有廣泛影響的戰爭文學作家,徐懷中從未停止對戰爭的反思,也未停止對自己思想感情的反思,他甚至說自己仍沒有真正感知在越南南方土地上進行的那一場曠日持久而又極端殘酷的戰爭。
澳大利亞記者貝卻迪在越南待了十多年,以第一手新聞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加拿大廣播公司駐遠東記者邁克爾·麥克利爾也在越南待了十年,寫下了《越戰10000天》。這些戰地記者的職業精神對徐懷中有很大的觸動,他發自內心地感到欽佩。“我們與西方記者不同,我們只能集中時間做戰地采訪。他們是從始至終跟蹤越戰,追求歷史觀察,著重從戰爭各方領導層的決策謀篇加以宏觀把握,對態勢發展有透徹的了解,這是我們做不到的。”美國記者在前線以身殉職的就有135名,多數是攝影記者。全世界戰地攝影家,國籍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到頭來卻總是不可避免地相聚在同一個陌生的“故鄉”。
在徐懷中他們之前,有“中國新聞工作團”一行九人經胡志明小道,行軍九個月才到達南方。徐懷中出訪的時候,我方已經和金邊打通了關系,徐懷中之行已不必由河內南下走胡志明小道,而是直接從金邊潛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總部。正因為對胡志明小道沒有親歷生活,感同身受欠著一層,導致了他順水推舟的描寫,說什么在戰爭后期,“胡志明小道上的女志愿者們,已經悄無聲息地度過了青春期,發育成熟,成為健壯俊美的南方婦女了。”而事實上,在極端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女志愿者們身體受盡摧殘,不可挽回。“胡志明小道”作為一個無法仿制的戰爭品牌保留了下來,而留給十多萬女志愿者的只能是無盡的苦難和悲慘。
好在《底色》初稿中這段文字得到及時改正,但徐懷中一直感到很愧疚。他坦言:“我不能不承認,自己并沒有真正感知這一場戰爭,并沒有真正感知越南南方。作為一名戰地記者,我缺少內心情感的充分投入,我太麻木,太冷漠,我太輕松愉快了。”又說:“根本上講,還是有做客思想,畢竟戰爭是在人家國土上打,真情投入不能與越方人員相比。我回敬人家的是低度酒,兌了水的。”老作家的自我反思令人感動。
以《底色》為書名,是徐懷中的一聲呼喊,是他對于這個世界發出的一個獨特的“警告”。
美軍駐越司令、四星上將威廉·威斯特摩蘭曾說,在“越共”高級將領中,“阮志清是唯一具有第一手知識的人,只有他懂得,面對美國火力進行常規戰爭是多么大的不幸。”正因為阮志清痛切意識到了美軍的火力超常強大,他打定主意,迫使對方不得不分散兵力,疲于奔命。“逼美國人用筷子吃飯”,阮志清大將的言語通俗化、生活化,充滿軍事辯證法。最基本、最高的作戰原則,被他一語道破:趨利避害,把握主動。遠起冷兵器時代,及至現代戰爭條件下,這個原則始終為兵家之圭臬。
“中國作家記者組”南方之行分量最重的一項安排,就是采訪最高軍事指揮員阮志清大將。在徐懷中的印象中,阮志清就像一團火,極端熱情,兩眼穿透力很強,好像能洞悉人的一切。阮志清被認為是越南勞動黨上層的一個“親華派”,他口無遮攔,講了一大段完全是同情中國的話,令徐懷中非常吃驚。訪問沒有做記錄,機密性太高,徐懷中害怕丟失,后來他憑記憶寫出阮志清的原話,再三跟同去越南的戰友核對,以求準確。
戰爭,無論規模大小或時間長短,也無論內戰還是對外戰爭,無論是最神圣的保衛戰爭還是最不韙的非正義之戰,最終都是以人的個體生命來結算的。在《底色》中,徐懷中以凝重與激越的筆觸記述了阮志清之死。這位大將并非如河內訃告中所稱死于突發心臟病,而是同眾多“越共”官兵一樣,也是在B-52轟炸機的機翼之下定格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一位將帥,無論你怎樣大智大勇,怎樣久經歷練沉穩老到,也無論你建立了怎樣的豐功偉績,在某種必要情況下,個人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個動作,和所有參戰士兵們一樣,那便是交出自己活撲棱棱的一條性命。”
徐懷中對戰地攝影大師卡帕懷有深深的敬意。卡帕的作品被譽為“戰地攝影不朽之作”,他總是擅于捕捉戰爭中稍縱即逝的動感形象,將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間定格為永恒。徐懷中說,卡帕以他無聲的語言塑造了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他的鏡頭縱深無限,他攝取到的是人類戰爭的“底色”。
所以徐懷中決定,自己的新作就以《底色》為書名。戰爭是人類歷史的永動機,無論以何種名義發動這一部機器,它的“底色”不會有任何區別,那就是死亡,是毀滅,是殘酷,是絕望。卡帕本人也沒有逃出戰地攝影者的宿命,他正是在越南戰地觸雷身亡的。他原希望出現在他鏡頭下的種種慘劇有一天能夠停止上演,看來卡帕的一番苦心恐怕也只能是付諸東流。正如卡帕的摯友唐·麥庫里所說:“我不再生活在幻影中,人類只能一直遭受苦難,直到時間盡頭。”
采訪的最后,我問徐懷中,能否評價一下自己在創作上的理想和遺憾。他說,翻查自己的文學流水賬,其中寫滿了遺憾和沮喪。由于種種原因,荒廢了很多時間,加之有寫作習慣上的弊病,總是要把一段段文字背誦下來,才能落筆到紙上,這就決定了他的“爬行姿態”,寫不了幾篇東西。他說,“我讀過這樣一段箴言:‘一個被揉皺的紙團兒,浸泡在清水中,漸漸平展開來,直到恢復為一張潔白的紙。人的一生一世,也應作如是觀。’現在對我而言,時間很有限了,但我還是會在文學寫作這一汩清澈的泉水中浸泡下去,直至重新平復為一張白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