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wǎng)>>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麥家:我現(xiàn)在跟影視圈關系很淡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7月02日09:06 來源:南方日報 周豫 劉揚 麥家 ◎人物名片: 麥家,作家、編劇。1964年生于浙江富陽,曾從軍17年,輾轉6個省市,歷任軍校學員、技術偵察員、宣傳干事、處長等職。1986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解密》、《暗算》、《風聲》、《風語》、《刀尖》等,《暗算》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他被稱為中國“特情”小說第一人,也被稱為“諜戰(zhàn)
麥家 ◎人物名片: 麥家,作家、編劇。1964年生于浙江富陽,曾從軍17年,輾轉6個省市,歷任軍校學員、技術偵察員、宣傳干事、處長等職。1986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解密》、《暗算》、《風聲》、《風語》、《刀尖》等,《暗算》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他被稱為中國“特情”小說第一人,也被稱為“諜戰(zhà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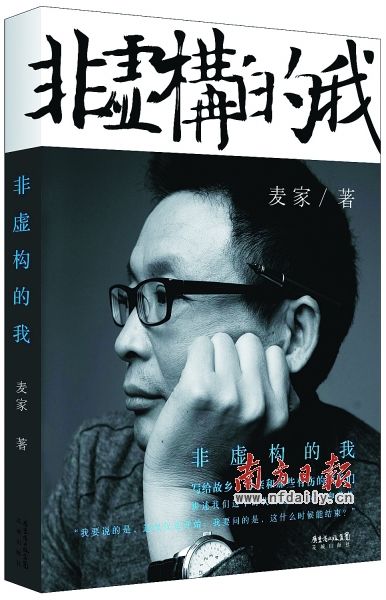 《非虛構的我》 麥家 著 花城出版社 2013年6月 定價:32.00元
《非虛構的我》 麥家 著 花城出版社 2013年6月 定價:32.00元◎核心提示
見到麥家,第一印象是他的那雙眼睛,犀利而懷疑,令人有點無所適從。但接觸下來,那個黑黑硬硬的漢子卻有著一種與硬朗外形不相稱的靦腆。他說,他不太喜歡在公共場所發(fā)言,“作家應該是孤獨的”;他說,自己的寫作和生活狀態(tài)格外簡單,是一個內向甚至是孤僻的“宅男”;他被中國讀者稱作“諜戰(zhàn)之父”,卻一直認為自己的小說不應該被“類型化”;他既是一個成都美女的丈夫,也是一個15歲男孩的父親,在“非虛構”的生活中,他會因為初為人父而“無法瀟灑”,會在安靜的時候做一個讀博爾赫斯的“書鬼”,他用“大腦”寫作,卻常常感慨“作家就是那頭可憐的‘豹子’”。
在花城出版社的《非虛構的我》這本麥家的散文集中,他談己、談人、談話、談事、談博爾赫斯,談“文學的創(chuàng)新”和“小說的責任”,談著父母、故鄉(xiāng)至愛親朋,談著自己的讀書寫作和文學大師,相比那個小說中“虛構”世界的殘酷,這個“非虛構”的麥家以及他的文字則顯得格外溫暖。從文學到現(xiàn)實,從書店“理想谷”的大膽“試水”到《風語3》的幾乎“難產(chǎn)”,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獨家專訪時,他往沙發(fā)里一仰,閉上眼睛,故事娓娓道來,細節(jié)毫發(fā)畢現(xiàn)。
【談生活】
上軍校重寫命運
“我有局限,不會寫‘非虛構’”
南方日報:為什么給這本書命名“非虛構的我”?相比之前寫小說的狀態(tài)有什么不同之處?書中的文字相當溫暖,是否也展現(xiàn)了你不為人知的另外一面?
麥家:顧名思義,就是一個真實的我,我的小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全都是虛構的,但這本書有些甚至是我的微縮版自傳,是對我過去走過的路的一種檢點。如果你對我這個人比較好奇,那么這本書能夠滿足你一點點好奇心。當然,很遺憾的是,這本書里沒有緋聞和任何可以炒作的東西,我的成長之路是很常規(guī)的,17年的軍旅生涯、11年的電視臺編劇到現(xiàn)在做了10年的專業(yè)作家,生活比較單調,經(jīng)歷也并不復雜,但是我內心的經(jīng)歷還是有特色的。
這本書不是策劃的,有些是應命之作,有些是自己有那種表達的欲望。這里面有五個系列,有的談人、有的談事,還有的純粹是談話,我已經(jīng)經(jīng)歷的人生當中8個重要的時間,對我影響最大的是1981年考上軍校那一天,如果說出生是一種“天命”,它讓你無法選擇,那么考上軍校則讓我的命運“重寫”了,它讓我真正體會到鄉(xiāng)下和城市完全是“兩重天”,如果沒有讀書的機會,可能現(xiàn)在的我正在某個工地上打工。
南方日報:從丈夫到父親,這種角色的轉變是否也曾經(jīng)不適應過?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和他相關的一切會不會影響你對生命的觀念?給你帶來一些不同的感觸?
麥家:在獨生子女的體制下,孩子都是被放大的,但當你憐惜他的時候,他又不給你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孩子的期待會很高,一旦期待高了就會有恐懼。孩子就是你的“尾巴”,既然“長”出來了就要對他負責。他很強烈地影響到我,這是毫無疑問的,我33歲得子,生命意識已經(jīng)很強烈了,孩子出門會擔心他會不會被自行車撞,去游泳會不會出現(xiàn)危險等等,但是當你23歲時根本不會考慮這些問題,因為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珍惜生命。
這種對“生命”的感受在2008年地震的時格外強烈,旁觀者和親歷者完全是不同的,眼看著那么多生命消失,讓人對生命的感受和刺激是很深的。我當時本打算去北京發(fā)展、尋找更多機會,但發(fā)生災難以后真正覺得人生平安是第一,名利都是假的。也算是命中注定,幾乎在同一時間,我的父親突然得了老年癡呆癥,當時我毅然決然地決定不去北京回杭州,想法很簡單——盡量多陪陪老人,其實名利確實沒有想象那么重要。我一直想寫一個和地震有關的作品,但畢竟直接表達不是我的擅長,記者和報告文學作家肯定會比我寫得好,我曾有意識悄悄地去過都江堰、映秀,想多看、多些感受,尋找表達的沖動。
南方日報:書中你專門給李敬澤寫了個詞條,評價說“他正與文學暗暗離婚”,如何理解?他作為《人民文學》的主編,你是否有關注他開辟的“非虛構”專欄?
麥家:2010年,李敬澤出了一本書《小春秋》,那一年他本人包括職務、面對公眾的腔調和形象等都有很多變化,我便給他寫了個詞條。可以說,李敬澤的文學評論的知名度在某種程度上是傳媒造就的,他有一陣子在《南方周末》副刊上寫專欄,那個時候文學還沒有像現(xiàn)在這么邊緣,另外他的文學評論獨具一格——用詩意的語言、散文化的形式來寫文學評論,時而溫情脈脈、時而激情澎湃,這種文學評論不僅在思想上有先鋒性,在文體上也很有追求,一時間,他成為文學評論界一個偶像級人物。《小春秋》咋一看,他離開了現(xiàn)代,回歸了傳統(tǒng)。但我認為,他實際上最先擯棄的就是傳統(tǒng)——是深入而出之后的擯棄,而非粗暴的閹割。無疑,李敬澤對當代文壇有太多的失望,所以他選擇抽離出來,從源頭梳理出一條本相之路。總的說,2010年的李敬澤讓我感到孤獨和憂傷。數(shù)年前,朱大可高調宣稱與文學離婚,2010的李敬澤通過《小春秋》,正面和背面都透出一種信息:他正在暗暗地與文學離婚。
談及非虛構文學,它是介于小說和報告文學之間的新的文學品種,比報告文學更文學,比小說更紀實。現(xiàn)代人喜歡探究真實的東西,對虛構的東西越來越不關心,它是一個比較貼近現(xiàn)代人期待的閱讀品種。搞非虛構文學肯定不能跟我一樣“宅”在家里,你必須要走出去、直面人生、直面社會,否則寫出來的非虛構文學肯定是很蒼白的。我本人不會嘗試“非虛構”文學,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不能什么文體都去嘗試。
【談純文學】
借通俗拓疆土
“當代很多小說可讀性太差”
南方日報:有人評價你是純文學領域最暢銷的作家之一,“純文學”的頭銜會不會對你的創(chuàng)作有限制?你剛剛提到在今天“文學更加邊緣化”了,但為什么又會投入那么高的熱情在“理想谷”這樣一個給文學青年創(chuàng)造“夢想”的地方?
麥家:客觀來說,今天我們的傳統(tǒng)文學更邊緣化了,但文學本身其實并不邊緣,甚至比10年前更熱鬧了。由于網(wǎng)絡文學、電子閱讀的興盛,現(xiàn)在看小說的人絕對比任何時候都多。其實,不管我的年齡、寫作方式、涉及的題材,毫無疑問我寫的肯定是傳統(tǒng)文學。現(xiàn)在傳統(tǒng)文學一本書要做到10萬冊已經(jīng)很難了,我的書雖然沒有出版社本身期待的那么好,但這2年我出了4本書,最少的一本也有31萬的銷量,不是說我的東西寫得多么好,這里面有各種機緣巧合,我的書被炒作起來主要是影視的原因,《暗算》掀起了一種特殊產(chǎn)業(yè),大家生產(chǎn)制造“諜戰(zhàn)影視劇”,在這方面我是最先吃螃蟹的人。
至于“理想谷”所希望構建的,是一個飽含文學氧氣和正面精神能量的場所,它具備書店的功用,也有文化沙龍和寫作營,選址在我的故鄉(xiāng)杭州富陽,周圍有五韻峰的七山三湖,寫作者可以在創(chuàng)作之余看看書、喝喝咖啡、欣賞風景。我免費給他們提供吃住,唯一的要求就是最后落款“寫于理想谷”就可以了,那里有個書吧,大約150平米,我配了90萬元的書,3個房間提供給寫作的人,不可能太多,多了以后就成開筆會的地方了。
南方日報:國外的智力小說更注重的是對知識的密集型呈現(xiàn),而你的小說給人的感覺是語言下的解密和探秘,什么樣的敘述是“麥家式的敘述”?你的小說密碼我們應該怎樣去解讀?正如劉慈欣的《三體》讓我們對“科幻小說”重新下定義,你的小說是否也開辟了一種新寫法?
麥家:外界盛傳我的小說是“諜戰(zhàn)小說”,但是我從來都不承認。有些東西是不能去類型化的,我在寫的時候也沒有刻意去類型化。但是回頭一看,我的小說確實是有一些標示性的動作——我寫的都是天才,他們都有特殊稟賦,從事的工作是非常態(tài)的,可以統(tǒng)稱為“特工”,最終都以悲劇收場,也算是有一些類型。其實,“類型化”很明顯的東西有時候并不是最好的,相反“雜生”的可能會很好。我的小說寫法完全是純文學的,但題材、涉及的領域、筆下的人物都是通俗的,可謂“兩邊討好”。
我的寫法雖然爭議很大,但是茅盾文學獎還是讓我得了,為什么?在這一點上我可以毫不自卑地說,我的寫法是純文學的,我表達的不是一種職業(yè),而是從事這個職業(yè)的人的命運,我覺得這就是純文學的概念。可以說,這是我對中國當代小說做了研究之后的一種選擇。當代的很多小說可讀性太差了,既沒有情節(jié)性,也沒有趣味性,那種沉悶的敘述、那種復雜的人物關系、那種很深邃的心理描寫對當代讀者來說,成了一種“受刑”,我們專業(yè)的讀者有時候都讀不下去,更何況普通大眾?把這種粗糙的文本丟給讀者,是對讀者的懲罰。小說想恢復讀者對小說的信心,唯一的辦法就是講好故事。小說最大的文學性是故事性,但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是不容易的。
南方日報:您提倡“用腦寫作”,從傳統(tǒng)意義來說,一篇傳世的文章需要用心去寫,怎么理解您說的用腦寫作?在你的小說里可以看到一些上世紀80年代一些先鋒作家的敘述手法,比如第一人稱敘述策略、非道德化分析視角等,您也受他們的影響?
麥家:其實小說也是有技巧的,現(xiàn)在很多小說太不講究技巧,我相信很多好作品確實是用心寫作的,但是“心”是很模糊的概念。小說作為藝術的品種之一,還是要練好基本功,最簡單的就是小說的語言、結構,有什么樣的結構就可能出現(xiàn)什么樣的文體。我強調用大腦寫作就要對小說的技巧做一些探索和研究。上世紀80年代,世界文學剛剛對我們開放,大家都在寫先鋒小說,我覺得那種先鋒小說大都是對國外文學的一種模仿,那時以先鋒小說成名的作家到現(xiàn)在也有很多并沒有保持那種“先鋒性”,都在重新安家,我還更多地還是受國外文學的影響。
在講故事的技巧上,博爾赫斯、納博科夫都是我非常欣賞的作家,他們在講故事時,首先把故事的外延擴展,所講的故事、關心的人群是以前傳統(tǒng)文學不太關心的,他們把文學的疆域拓展了,包括我的小說現(xiàn)在在文學界被認可也是因為我拓展了中國純文學的疆域。以前沒有哪個純文學作家會去寫這種破譯密碼的人,農民、土地、工人等那些很貼近大地的人是傳統(tǒng)文學要表達的對象,武俠、言情、間諜都被納入通俗小說的范疇,純文學是“瞧不起”那些通俗小說的,而我恰恰是從那個領域尋找我的寫作題材,但我完全用純文學的方式寫,這也是一種嘗試。
【談跨界】
《解密》5年被退稿17次
“我是個宅男,現(xiàn)在跟影視圈的關系很淡”
南方日報:談到《風聲》,難免會讓人好奇你是如何處理小說與影視、編劇與導演信念和責任這些關系的。你的小說里大多是天才或者英雄式的人物,但最終還是有一種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無奈,這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種寫作立場?最近郭敬明也去做導演了,往后你有沒有做導演的計劃?
麥家:這輩子我能把字寫好就不錯了,我怎么能跟郭敬明比?郭敬明他才30歲左右,我卻已經(jīng)年近半百,不會再去跨界做任何事情。相比編劇,我更想寫小說,以后如果有合適的題材我也不妨繼續(xù)做編劇,但是導演我是不會去做的。我倒是覺得,小說家天生是個導演,因為寫作的過程是充滿畫面感的,某種意義上說,小說是作家一個人的電影,別人看不到。現(xiàn)在,好幾個導演原來都是寫小說的,有的愿意去嘗試,但其實大多數(shù)人是不愿意的,很多作家只想給自己的生活做減法,不想做加法,因為寫作這種生活方式注定了要內心安靜一點,涉獵的東西太多可能會影響到寫作。
我雖然經(jīng)常和影視圈合作,但那僅限于我的作品,我現(xiàn)在跟影視圈的關系很淡,他們都希望我去當編劇,但是我拒絕了,一方面是我沒時間,另一方面自己當編劇有自己的局限,很難跳出小說的框框。在生活中,我本身對日常有一種畏懼感,寫作上的成功給我增加了一些自信心。我就是一個“宅男”,在盡量回避和現(xiàn)實社會打交道,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情商比較低。我的寫作狀態(tài)就是我的日常狀態(tài),寫作早已經(jīng)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南方日報:《暗算》最開始是怎么在影視圈被人發(fā)現(xiàn)目標的?當年寫《解密》時的寫作心態(tài)跟現(xiàn)在是一樣的嗎?
麥家:《解密》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把我?guī)衔膲淖髌罚?jīng)被人退過無數(shù)次稿,我不停退、不停改,前后折騰了10年,我再也舍不得對它動刀子了,更何況很多人也拍出來了。年輕時我渴望成名,第一稿寫完是1997年,但真正出版是2002年,5年內《解密》曾被退過17次稿。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大家》雜志的一個編輯曾很誠懇地跟我談:“麥家,你這個小說不能這么寫。現(xiàn)在誰關心歷史啊?誰還看塑造英雄的東西?”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是很多編輯的意見,那時候大家都寫私話小說。
其實《暗算》之前我已經(jīng)寫完《解密》了,通過《解密》我已經(jīng)跟很多影視公司建立了聯(lián)系,包括后來買《暗算》的那家公司。當初我對《解密》的心理期待的版權費是5萬,但最后漲到了35萬,在2002年是很貴的。我現(xiàn)在非常懷念寫作《解密》的寫作狀態(tài),沒人打擾你,現(xiàn)在都是別人追著你寫,寫作的時候會人為地增加很多雙眼睛好像在注視著你。
南方日報:進入影視圈后對你的寫作有負面影響嗎?
麥家:負面影響太大了,在《風語》這件事上,我走了一條不規(guī)矩的路,沒有經(jīng)得起誘惑。還是應該小說寫完之后再來改寫,現(xiàn)在電視劇先完成了,我想把它全部推倒,但題材已經(jīng)固定了,要避開它有很大難度,所以現(xiàn)在我很累。但別人都睜大眼睛在看我的東西,我不敢怠慢。現(xiàn)在在寫《風語》第3部,自己的寫作已經(jīng)進入了難產(chǎn)的狀態(tài),第一部寫完影視公司就介入買走了它的影視版權,邀請我當編劇,但我的小說實際上沒寫完就被強制中斷。我現(xiàn)在寫東西就想跟電視劇完全不搭界,把《風語》完成后我肯定不會再寫這種題材了,想寫武俠或者愛情。
網(wǎng)友評論
專 題


網(wǎng)上學術論壇


網(wǎng)上期刊社


博 客


網(wǎng)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