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葉曙明:我所做的都是與歷史聊天而已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6月24日10:07 來源:南方日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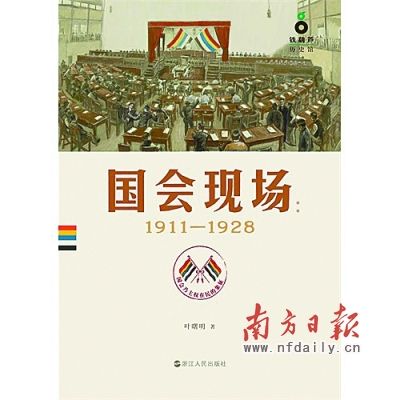 《國會現場》 葉曙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定價:42.80元
《國會現場》 葉曙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定價:42.80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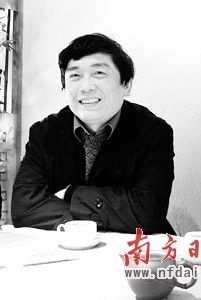 葉曙明
葉曙明◎人物名片:
葉曙明,廣東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創作以歷史、散文、小說為主,著作包括“近代史三部曲”——《大變局:1911》、《重返五四現場: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中國1927:誰主沉浮》,以及《大國的迷失》、《軍閥》、《草莽中國》、《共和將軍》、《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三卷)、《其實你不懂廣東人》、《萬花之城》、《廣州舊事》等二十多部。
◎核心提示
30多年里,葉曙明有了越來越多的側面像:從曾經瘋狂迷戀寫小說的那位先鋒小說作家,到輾轉多家知名出版社的出版人;從熱衷于清末民初歷史的近代史研究者,到因一本《其實你不懂廣東人》在國內掀起廣東人現象討論、從而被譽為廣東文化代言人的寫書者。
日子久了,來自出版商的邀約也就紛至沓來。
已經出版的非小說類歷史書里,葉曙明自行命題的只有兩本,一本是24年前的《草莽中國》,一本是最近出版的《國會現場》。其他均是應邀而作,也就是“命題作文”。
很多人認為,“命題作文”是御用文人才會去做的事情,但在葉曙明看來,是否“命題”實在無關緊要,“這世界上沒有不值得寫、不可以寫的題目,關鍵看怎么寫。”
到了現在,葉曙明更愿意將自己定位為“歷史說書人”。
他覺得自己所寫的,都是與歷史人物對話的結果。在與歷史的聊天中,他也收獲了很多朋友——無論是陳炯明、梁啟超、孫中山,抑或是章太炎、陳獨秀。“我也可以說‘我的朋友胡適之’、‘我的朋友陳競公’了,只不過在他們的朋友里沒有我葉曙明而已。”
關于青春
在工廠的四年里
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南方日報:1980年您到花城出版社工作,能談談您此前的情況嗎?
葉曙明:我是1974年高中畢業的,但后來聽說國家不承認文革時期的畢業文憑,要重新考試,我沒有參加,所以我的學歷應該是幼兒園畢業。我1974年去了從化民樂茶場種茶葉。那時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做一個職業革命家,便整天躲在被窩讀《列寧選集》,在世界地圖上標記黑海艦隊、波羅的海艦隊的駐地。1976年我離開茶場,去工廠當了一名車工。在工廠的四年里,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職業革命家的夢想蕩然無存。工人階級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比如出工不出力,做車間金魚,遲到早退,裝病騙假條。我一個月幾乎曠工20天,有時發工資時只有幾塊錢。曠工不敢呆在家里,也沒地方去,就整天待在中山圖書館南館看書,看《東華錄》、民國報紙和各種歷史書,一邊看一邊做筆記,那四年做的筆記估計有幾百萬字,后來全扔掉了。我對清末民初歷史的興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1980年底,因為我寫了一篇《賣假藥的老頭》,被花城出版社總編李士非先生看中,就調到了花城,我總算找到了自己合適的位置,就是當編輯。這篇小說寫一個人從年輕時開始收集茶葉渣,一直到老,卻忘了自己當初收集茶葉渣是有什么用了,最后只好把一生的收集當垃圾全倒掉。這也許可以作為我自己人生的一個寓言吧。
南方日報:您在這段時期的創作是怎樣的?1988年您發表了第一篇長篇小說《軍閥》,這給您的生活帶來了哪些改變?
葉曙明:四年工廠生活對我影響非常深。1980年我第一次接觸卡夫卡小說時,便完全被他迷住了,我覺得我就是他小說中的人物。所以那時我非常迷“現代派小說”,像卡夫卡、杜拉斯、加繆這些人的小說,每個標點符號都能引起我的共鳴。當時有人說,意識流小說是因為一句話不能完整地說,所以要打碎來說。其實并非如此,而是因為這句話只能這樣說,用任何其他形式都不是這句話了。1980年代以后,我已基本不看國內作家所寫的“現實主義”作品了,但我并不排斥它們,《軍閥》就是我的一次現實主義嘗試或者說是模仿,初稿甚至是章回體的。我當時頗為自得,覺得自己雖然討厭現實主義小說,但還是能寫得出來的,但現在回過頭看,基本上是失敗的。
南方日報:作為那個文學潮流迭起時代的見證者,能談一下當時文化圈那些人和那種氛圍嗎?很多人覺得,80年代被過分“符號化”了。
葉曙明:那是一個激情四溢的年代,當然是與50、60、70年代比較而言的。把前三十年的蘊結一次性噴發出來,隨后又在短短十年里揮霍殆盡,這種情景自然很華麗、很壯觀。我到出版社時,很幸運還能與最后一代的文人編輯共事。他們身上依然保持著四五十年代老文化人的“范兒”,學識豐富,能詩善文,有性格,有風骨,現在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到處充斥著被成功學訓練出來的人。現在做出版,開口閉口都是能贏多少虧多少,有沒有企業贊助,能不能申請政府資助,能不能評國家級大獎。與80年代相比,已經是另一個世界了。所以我不知道80年代有沒有被符號化,不關心有沒有被符號化,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符號化,我只知道,作為一個過來人,我十分懷念那個有激情有夢想的年代,尤其是編輯上班不用在攝像頭下打卡。
南方日報:后來您開始了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這緣于怎樣的契機?
葉曙明:1980年代我寫了不少小說,主角大多是精神病人,越寫越覺得語言蒼白無力,到最后有一種崩潰感,文字已經沒法表達出我內心的想法了,寫出來的每句話都不是我想說的,我覺得再寫下去就要瘋了。那時我經常每寫完一篇小說就發一場高燒。1980年代結束時,我有一種從九萬尺高空直墜深淵的感覺。我決定不再寫小說了。于是我重拾起歷史,與歷史人物對話,這能讓我獲得一點平靜。
我愛好歷史,但從不在意它的學術性,我讀正史不多,讀論文更少,我寧愿讀原始檔案。直接讀奏章、上諭、文告、書札之類,好過讀什么通史、全史。因為讀原始檔案有一種與古人直接對話的感覺;讀通史、“略論”、“試論”的話只是在看別人的聊天記錄,試問除了想要揪辮子之外誰有興趣讀別人聊天記錄?我在微博上把自己定位為“歷史說書人”,因為我寫的都是我與歷史人物對話的結果。我沒打算推翻什么,也沒打算建構什么,一切都是與歷史聊天而已。
關于寫作
任何題目都可以寫
關鍵是怎么寫
南方日報:為什么會想到寫這本《國會現場》?以“國會”為寫作對象詮釋告別帝制后的中國歷史有什么特別之處?
葉曙明:我把我的“現代史三部曲”《大變局:1911》、《重返五四現場》和《中國1927:誰主沉浮》概括為:第一部是出發,第二部是轉向,第三部是鎖定。中國未來的走向,在1927年的國民革命中就基本鎖定了。在“三部曲”后我感覺意猶未盡,因為在現代中國始終有兩條線并行:立憲與革命。革命這條線從同盟會那兒傳下來,還有另一條線,就是立憲、民權、自治這條線,從清末新政那兒傳下來。我想理清這條線在民國時代是怎樣延續、嬗變的。我原來的構想是寫一部“民國制憲史”,從1912年的約法寫到1947年的憲法。但后來考慮出版會有困難,便只寫了北洋時代的制憲。在我看來,民國的真義在于“主權在民”;而“主權在民”的最高體現在于國會。民國初年的紛爭,都是圍繞著國會的。
南方日報:我注意到您在新作中用了很細節的描寫,文獻“愈近愈繁”,您對史料的價值有著怎樣的甄別態度?
葉曙明:歷史本來就沒有什么絕對的真相,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找出相反的“證據”都是輕而易舉的,區別只在于你采信誰的證據而已。我并不是一個考據家,我很少旁征博引地去考證一條史料的真偽。
我甄別史料的辦法,基本就是靠海量的閱讀,讀官方檔案、稗官野史、私人筆記,一直讀到我對這個人像老朋友一樣熟悉,對他的舉止言行,已沒有什么意外了,他會不會說這句話?會不會做這件事?他是怎么想的?動機是什么?我憑對他的了解就能判斷。我承認這樣取舍史料,會帶有很強的感情色彩,但歷史本身就是帶感情色彩的,不是顯微鏡下的毛毛蟲。我的原則是我不捏造史料,不虛構情節,但我采信哪條史料,則是根據我對這個歷史人物的了解,作出的純主觀判斷。如果有誰想改變我的看法,最好不要以史料的真偽來質疑我,因為你也無法證明你掌握的史料就是真的,你只能說:我還有別的史料,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版本呢。這樣,我會非常樂意聽,然后再作出我的主觀判斷。
南方日報:近幾年您出版的著作數量與前些年相比更密集,這可否理解為您在大量前期準備基礎上的厚積薄發?
葉曙明:在我已經出版的非小說類歷史書里,只有兩本是我自己定題目想寫的,一本是后來改編為《大國的迷失》的《草莽中國》,一本是《國會現場》,其他都是應出版商的邀約而寫的,也可以說是“命題作文”。這幾年出版商約得多,所以就寫得多。很多人不屑于命題作文,好像那是御用文人干的事情,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其實我覺得任何題目都可以寫,這世界上沒有不值得寫、不可以寫的題目,關鍵看怎么寫。
以為寫命題作文就一定要順著命題者的意愿去寫,那是作者的無能;如果自我設限,即使不是命題作文,估計也難寫出什么好東西。比如2008年廣州市文聯約我寫一本有關廣州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書,這是命題作文之中最主旋律的題目了,但我覺得一樣可以寫,于是寫了《萬花之城》,對廣州的城市建設提出我的觀察和憂思,說想說的話。是否“命題”,實在無關緊要。
關于研究
我不太清楚
“主流學術圈”在哪里
南方日報:從近代史到廣東地方史,您關注的這兩個領域有什么關聯嗎?
葉曙明:中國要轉型為一個現代國家,關鍵不在于戊戌變法,不在于朝廷的預備立憲,甚至不在于同盟會革命,而在于地方自治。自治是國家邁入現代化的一個門檻,一個突破點,清末民初談立憲也好,談改良抑或革命也罷,能否實行地方自治是這個國家健康與否的一個基本指標。廣東有悠久與深厚的自治歷史。廣東的自治,既不像湖南以傳統的士紳為主,也不像上海以洋買辦為主,它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它一向是由商人主導的。我對廣東地方史的興趣,實際上是受著對地方自治史的興趣驅使。
南方日報:在寫關于廣東的著作時如何避免傷害別人的地方感情?您又如何看待地域歧視這一現象?
葉曙明:我寫廣東地方史只是為了喚起人們的地方自豪感,保持一點點的地方意識,從來不想去傷害別人的地方感情。我想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它值得自豪的地方,我希望都有人把這種感情發掘出來,好好培育。與其把宏大的國家觀念高唱入云,倒不如先養成淳樸的鄉土觀念。打個比方,什么是中國菜?就是由粵菜、湘菜、魯菜、川菜、京菜等等地方菜組成的,如果把這些地方菜都抽走,中國菜還剩下什么?什么也沒有了。你在廣東生活,不了解四川、安徽、貴州都情有可原,但你至少應該了解廣東,應該對它有感情,一個對自己生活之地都毫無感情的人,說對國家有感情,那都是假話。
中國最可寶貴之處就是地方文化的多元性,飲食、語言、習俗五花八門。地域歧視是一種幼稚的心態,其智力大約在三歲左右。試想還有什么比“只準我自豪,不準你自豪”更幼稚的呢?曾經有出版商邀請我寫老北京,我父親是北京人,我對老北京也有很深的感情,很想去寫,可惜我沒法去北京生活一段時間,感受不到現在的北京,所以不敢去寫老北京。我寫《國會現場》時,對聯省自治運動中的湖南,心懷敬意;我寫《李鴻章傳》時,對安徽也充滿了神往之情。這些地方,有機會我都想去朝拜。
南方日報:研究歷史過程中,時常會遇到這么一句話:“某人某事在歷史上已有定論”。在您看來,為什么大眾覺得歷史有定論?
葉曙明:歷史是什么?就是一堆史料。誰都可以去翻一翻,讀一讀。對同一條史料,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沒有誰的手里握有終極真理,正如沒有誰可以規定酒一定是香的,更沒人可以規定甜一定比辣好吃一樣。打個比方,對康有為,有人把他捧得很高,有人貶得很低,我覺得都很正常。可怕的是只準捧或只準貶,或者只準捧多高,高一分不行,低一分也不行。他說辣好吃,誰說不好吃就是想抹黑川菜、打倒川菜,這個罪名也太大了吧?所以,一切聲稱歷史定論不容質疑的,百分百是為了維護現實利益,與歷史根本無關。
南方日報:有人認為,您似乎刻意在心理上保持一種與“主流學術圈”的距離來分析中國近現代史的走向,您贊同嗎?
葉曙明:我在寫《草莽中國》的時候,就是試圖從地域的角度去解讀中國近代史的演變,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為什么東南打不贏西北?蔣介石與馮玉祥、李宗仁、陳濟棠、閻錫山這些人的矛盾,到底是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還是東南與西北、西南的矛盾?中國的很多疑難雜癥,用正統的學院理論說不清,最后只能歸結為生理結構、內分泌、飲食習慣以及這個地區的降水量、氣溫等原因了。
我并沒有刻意與“主流學術圈”保持距離,因為我不太清楚這個主流學術圈在哪里,所以談不上親疏。我說過,我讀學術研究文章不多,這不是對學術抱有什么成見,而是純屬個人興趣而已。今人寫的“主流學術作品”中,我唯一愛讀的,也許只有年譜。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劉長欣 實習生 欒相科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