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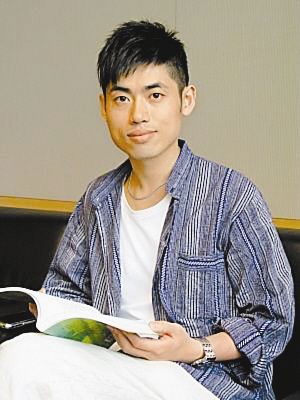 葛亮
葛亮相信很多人,談起香港文學,頭腦中還是固化一個概念,那就是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或者梁鳳儀的財經小說。包括去年香港書展評出的年度作家也斯,內地的媒體都覺得陌生。那么,香港文學,尤其是近些年,香港、內地交流溝通大大方便、密切之后,它的特質在哪里,變化在哪里?作家在香港這個城市的寫作與表達,狀態如何?
記者專訪了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著名作家葛亮。作為寫作者兼研究者,他對香港文學的觀察更直觀,也更立體。
香港文學強調語言的方言化
“我們對香港文學大概還是存在成見,傾向將之定義為一種地域文學。比方說,似乎只有談及‘九七’,談及文化身份認同,李碧華小說《胭脂扣》等作品的文學意義才得以凸顯。”談到香港文學的特質,葛亮說,香港文學有自己獨特的敘事模式﹐包括強調題材的“在地化”和語言的風格化與方言化 ;同時,他們的作品中有些普世性的人文關懷存在,大概不能用“傷城”與“我城”等語境性詞匯概括其全部價值,“香港作家西西的批判力與黃碧云的鋒利,不見得只放在香港才成立。后工業化時代帶來的種種都市癥候乃至異變,在當下中國放之四海而皆準。”
同時,葛亮并不否認香港是個更重地域性的地方:“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它中西交匯的特質。另一方面也是關乎它作為城市的獨立性。‘中環價值’固然是一個層面,但是,‘老香港’的部分,特別是殖民文化的歷史遺留也讓香港人念念不忘。”葛亮說,香港近年來有個非常熱的概念,叫做“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 ,一個皇后碼頭的拆遷,可以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其實是一種歷史危機感的寄托。就文字而言,也是如此。隨意一份香港報紙,都是和現代白話文相去甚遠的 “粵方言書寫體”。但對香港本地人,是非常親切的。文學的呈現,就是地方甚至身份認同感的直接體現。
在香港堅持寫作,需要勇氣
香港的文學從業者生存狀況如何?葛亮說,在言說空間上,在香港也許更自由。但從個人生存的角度,在香港堅持寫作,需要勇氣,因為有時間與生活的雙重壓力。但的確有相當一批人致力于此,“在這個環境里寫作,我心里還是踏實的。因為沒有什么包袱,寫作更多是一種表達上的需要。這就使我的寫作行為變得相對簡單。”
葛亮結合自己最近完成的一本以香港做題材的小說為例,進一步談道:“這本新書叫《浣熊》,這個暑期同時在內地與港臺出版,與讀者見面。《浣熊》更為關注香港本土民間社會的現實。為此在撰寫過程中,作了很多的資料收集和訪談,應該說是一本落在實處的小說。”如在書中所寫:“這城市的繁華﹐轉過身去﹐仍然有許多的故事﹐是在華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黯淡。當然也有許多的和暖﹐隱約其間﹐等待你去觸摸。任憑中環﹑尖沙咀如何‘忽然’﹐這里還是漸行漸遠的悠長天光。山下德輔道上電車盤桓﹐仍然也聽得見一些市聲。”
港臺文學進入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
近年來,隨著香港和內地交流、溝通日益密切、便利,越來越多的香港作家在內地出版作品、參加活動,香港文學進入了一個更開闊的時空。“這兩年的港臺文學出版狀況,大概一方面表現了華語文學界日益開放的大氣候。這不僅指意識形態層面的,而更多是一種文化視野的表達。很多資深港臺作家的作品得以在內地出版,實際將中國當代文學軌跡中相對模糊的部分、我們一直以來認為是支流的部分明晰化了。如果將當代文學譜系比喻成一棵family tree,無疑港臺文學近年規模化的出版,令這棵樹更為枝繁葉茂。”葛亮說。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 鐠侇噣顣介敍锟�鐠ф澘鎮滄稉鏍櫕閻ㄥ嫪鑵戦崶鐣岊潠楠炵粯鏋冪€涳拷
- 閸㈠顔曢敍锟�閸掓ɑ鍘涘▎锝冣偓鈧棅鈺傛緱閵嗏偓閸氭潙鍗�
- 閵嗘劒瀵岄弮銊b偓鎴窗缁楋拷73鐏炲﹪娲﹂弸婊冾殯8閺堬拷23閺冦儱婀紘搴℃禇閹活厽妾介妴鍌欒厬閸ユ垝缍旂€硅泛鍨幈鍫燁偩閸戭厼鈧喓顫栭獮璇茬毈鐠囨番鈧﹣绗佹担鎾扁偓瀣箯瀵版娓舵担鎶芥毐缁″洦鏅犳禍瀣殯閿涘矁绻栨稊鐔告Ц娴滄碍搴婃禍娲浕濞喡ゅ箯瀵版娲﹂弸婊冾殯閵嗗倽绻庨獮瀛樻降閿涘奔浜掗妴濠佺瑏娴f挶鈧璐熸禒锝堛€冮惃鍕厬閸ョ晫顫栭獮缁樻瀮鐎涳箒鎽ら崟鍐ㄥ絺鐏炴洩绱濋崷銊ユ禇閸愬懎顦诲鏇℃崳娴滃棔绱径姘愁嚢閼板懐娈戦崗铏暈閵嗭拷 [閻愮懓鍤潻娑樺弳]


網上期刊社
- 娴滅儤鐨弬鍥ь劅
- <鐠囨鍨�
- 濮樻垶妫岄弬鍥ь劅
- 娑擃厼娴楁担婊冾啀
- 鐏忓繗顕╅柅澶婂灁
- 闂€璺ㄧ槖鐏忓繗顕╅柅澶婂灁
- 娴f粌顔嶉弬鍥ㄦ喅閹讹拷
- 娑擃厼娴楅弽鈥虫疮閺傚洤顒�
- 娴f粌顔嶉崙铏瑰缁€锟�
- 娴f粌顔嶉柅姘愁唵


博 客
缁儳鍍甸崡姘瀮
- 閼规儳鍘犻幏婊冪毜: 鐠愮绻庢禍鐑樼毌 閸掓稐缍旈弴鏉戭樋閺囨潙銈介惃鍕稊閸濓拷
- 瀵娀娉ら弬锟�:閺冦儲婀伴幏鎺嶇瑝鐠併倗濮滈垾鏂衡偓鏃€鍨拹銉﹀灇閺堫剙銇婃担锟�
- 閻楀洭鈹堥敍姘卞閺堛劍鍨氶弸锟�
- 闂娾晝绶ㄩ弸妤嬬窗閺夊海鎲洪悳顖滄暏娑撱倓閲滅€涙鑸扮€硅鍨�
- 閺夈劍妾介弫蹇ョ窗濮圭喎鍝洪垾婊堢矋濞夈儲鍜曢垾婵嗙毈鐏忓繗顕╃化璇插灙閵嗕胶绮ㄩ弸鍕挤閸忚泛鐣�
- 闁厽鏋冮弬宀嬬窗鐠囧懎鎷婚敍宀冪箷閺勵垳顨㈢粋锟�
- 閸熷棝娓块敍姘冲壖缁愭繈鍣烽惃鍕槻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