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作家應關注社會而非市場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5月02日10:16 來源:齊魯晚報 師文靜[提要] 今年是長篇小說創作大年,賈平凹、蘇童、韓少功、王蒙、梁曉聲、馬原和方方都有長篇小說面世。年輕人應從知青故事中吸取人生動力 齊魯晚報:有人說,知青一代也在當今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時代的補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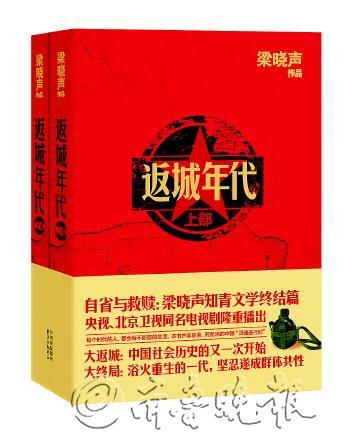
今年是長篇小說創作大年,賈平凹、蘇童、韓少功、王蒙、梁曉聲、馬原和方方都有長篇小說面世。此外,王安憶、余華、阿來、孫甘露、葉兆言、閻連科等名家的長篇也計劃于今年上市。相信這些沉寂了幾年甚至十幾年的作家一旦拿出一部長篇,必將讓文壇掀起波瀾。本報推出“關注長篇小說創作大年”欄目,將對多位名家進行專訪,希望對文學創作有所推動。 ——編者
近日,作家梁曉聲的新作《返城年代》面世。梁曉聲表示,寫《返城年代》最初只是政治任務,不太情愿動筆,后來發現自己需要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個題材,并且給現在的年輕人補上歷史記憶,不僅讓他們了解那一代人,更要讓他們知道那段歷史。談到當下的文化與娛樂,梁曉聲稱作家應關注社會的需要,而非市場的需要。
“我們這一代人
缺少懺悔的教化”
齊魯晚報:從《雪城》開始您的知青小說寫到了“返城”這個命題,而您最近的新作是《返城年代》,同寫知青“返城”,時隔多年,兩者在塑造知青的精神時有何不同?
梁曉聲:《雪城》里的知青有韌性,這種堅韌就像現在的打工青年融入到城市的韌性。我肯定青年人為了生存都有堅韌的精神,在京漂族、蟻族、蝸居族身上都體現著。《雪城》實際上是對理想主義的一種解構,生活變得實在了,就是工作、房子、工資,而且在《雪城》里人們的關系也發生變化,以前是宿舍生活,這里則由各個家庭把人們分開了。
《返城年代》中呈現的是一種向著自然而美好的人性的回歸,《返城年代》與我其他所有的知青題材小說所不一樣的是它塑造了一個懺悔型的知青——羅一民。羅一民上中學時寫紙條被告密,遭到父親打罵。“文革”時他報復女生,讓對方用噴壺來噴出一片冰場。返城后,他做了十把壺,當他敲打壺時不可避免就有了一種懺悔的夙愿。這個形象我覺得非常重要,我們說“回歸”,當他沒有懺悔時,他就沒有達成一種自我救贖。當他懺悔了之后,他的整個人才完全變成了另外的樣子,他才感覺到從身上擺脫了十字架。這個人是我在其他知青作品中所沒有的。
齊魯晚報:為什么要面對“懺悔”這個沉重的話題?
梁曉聲:知青一代的前身是紅衛兵,在“文革”中很多人受過紅衛兵的傷害。我們可以認為,紅衛兵是因為年輕而被政治所擺布和利用了,但是被利用就可以不懺悔了嗎?被利用不是不懺悔的理由。
“文革”結束后,相當多的中國人身上都留下了互相傷害的痕跡,文藝界、作家隊伍中很難找到誰受過傷害同時又沒傷害過別人的人,包括我們提起來耳熟能詳的人物,當我們翻開“文革”那段歷史時才發現原來他們也傷害了誰誰。當知青成為成年人后,事實上很少有人主動懺悔。
我們這一代人缺少懺悔的教化,羅一民來懺悔,應該給他機會。在西方,懺悔作為普世價值觀是不成為大問題的,但在中國,我依然覺得這課沒有補上,補上這課僅靠教化是不夠的,靠文學或影視的形象可能對我們的青少年多少會有一定的影響。
年輕人應從知青故事中
吸取人生動力
齊魯晚報:有人說,知青一代也在當今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時代的補償。您認同嗎?
梁曉聲:當我們說“一代人”的時候,不能只舉出這一代中的名人、成功者、政治家,假如這些人合在一起不過是百分之幾的話,他們不能作為這一代人總體命運的體現者,我們要看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情況。
這一代人首先是被時代耽誤的。返城年代也是“文革”結束后的幾年,在最初這些年知青一無所有、傷痕累累、疲憊不堪。他們都是結束“文革”的擁護者,結束了命運對他們的拋擲。改革開放強調解放思想,反對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這代青年不管上沒上大學的一概擁護,這代年輕人由于親歷了,他們對眼前的重新開始的機會表現出一種韌性。
齊魯晚報:如果說知青歲月是困苦歲月的話,也是當時整個民族的困苦。是不是年輕人更需要關注這段歲月?
梁曉聲:我確實還有一種意愿,今天一無所有的年輕人,看看知青的經歷是不是會有一點人生的動力?因為今天年輕人所經受的和我這代年輕時所經受的有相似之處,都有壓力,壓力不同而已。“勿忘我們走過的困苦歲月,戒除浮躁和虛無主義,同時恪守良知。”這是對的。
我剛返城時,在十一平米的房子里結婚,住了十年,在筒子樓里做飯。中間調房時,從十一平米變成十四平米。返城那代人也會因為房子造成手足之間鬧意見,就像我們在法制節目里看到的,這種傷痕甚至會很深。讓今天的年輕人來看這些故事,會不會有共同的堅韌經歷的體驗?
作家應該給予善良
而不是商業價值鏈
齊魯晚報:您的上一部書是《郁悶的中國人》,您如何看待當下人的郁悶?如何抒發郁悶?
梁曉聲:我是從極度物質匱乏的時代成長起來的,談到戀愛結婚,標準相當低。不是說我崇高、懂得愛情,這是整個社會大環境決定的。而目前這一代年輕人在對于生存、在對于幸福概念的理解上,比我們所受的誘惑、刺激更大,比照維度也更大,你自己不想比照都會被比照。這也是當代年輕人的困惑和郁悶。
以我看來,網絡中國和現實中國是不完全一樣的兩種圖景。從網上,時常看到的是郁悶或憤懣的中國,但正因為有這么多情緒都集中消解在網絡中,發泄情緒后,人們回歸現實又自覺納入秩序、規則甚至包括潛規則中。因此,網絡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成了高壓鍋的氣閥。我們也可以將這種大眾的郁悶看成“積雨云”。
齊魯晚報:您說,不能讓文化領域變成浮躁的全民娛樂場,不能做娛樂場的看客。為何您會有這樣的感觸?
梁曉聲:娛樂這一種習性是連動物都有的,人類是整個地球上娛樂習性最牢固的一類。娛樂很容易使人成為看客,娛樂本身就是看熱鬧,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極其可怕。這個習性可以推到羅馬角斗場,羅馬都有初級的民主了,但人性還處在那么低的階段。
在20年前的報紙上,會有女孩被當街凌辱被圍得里三層外三層的現象,這是不是看熱鬧?看熱鬧是不是一種最原始的娛樂?文化就是既給予娛樂又克服娛樂,作家要管社會需要什么,而不是市場需要什么,社會需要人性需要懺悔需要善良……作家就通過作品來給予這些,而不僅僅是給予商業價值鏈。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