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出版人訪談 >> 正文
黃雋青暢談出版業:傳統出版業早晚得出大問題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4月15日10:36 來源:廣州日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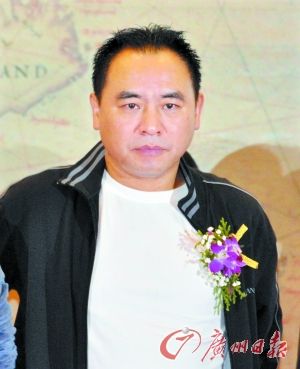 黃雋青
黃雋青第四屆中國圖書勢力榜金推手獲得者黃雋青暢談出版業:“傳統出版業早晚得出大問題”
黃雋青偶爾會懷念2008年前的“美好時光”。那個時候,他還沒有遭遇“杜拉拉”帶來的巨大成功,中南博集天卷圖書發行有限公司也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
今天的中南博集天卷已經成長為中國民營書業最具競爭力的企業之一。作為董事長,黃雋青的壓力也史無前例的大。在他看來,國內空前繁榮的出版市場實則亂象叢生。數字出版、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帶來的巨大沖擊以及不知何時又會出現的新技術,讓他充滿危機意識。本專題采寫記者吳波
談文學:對純文學敬而遠之
從策劃《杜拉拉升職記》、到運作蔡駿的懸疑小說《天機》、再到引進《不抱怨的世界》、《正能量》掀起勵志風潮……中南博集天卷的書似乎成了暢銷的代名詞。它的掌門人黃雋青,以敏銳的商人嗅覺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忽視了他身上早年間的另外一個“標簽”:文學青年。
黃雋青1988年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他進入某出版社供職十余年,升至副社長。2002 年,卻從體制內跳出,成為北京博集天卷圖書發行有限公司董事長。
“可以說,打從創業之后,我就距離純文學漸行漸遠了。”曾經對每一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如數家珍的黃雋青告訴記者,在2000年之后,這已經成為他知識體系中的盲區所在。
去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關于純文學是否可借這個契機重新壯大,出版圈、文學圈都在非常熱烈地討論。“我當時就說,該怎樣還是怎樣,莫言得獎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改變。”
黃雋青告訴記者,從他個人的價值觀和感情上講,他太希望莫言得獎能給市場帶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力,太希望這個市場能夠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狀況。但理智告訴他這不可能。“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純文學市場份額下降得特別大。這跟我們的市場轉型有關系。純文學需要內心非常安寧地去進行。而現在從整個社會大背景,到每個人的內心,都是浮躁和功利的。”
“好的純文學作家,在國內不過就是賣五六萬冊的市場。當年的莫言、蘇童,寫好了可以直接進入作協,拿到的工資足以過一種體面的生活。這對現在的作家來說是不可能了。你必須得面對市場,才可以靠寫作謀生。”
因此,黃雋青并不諱言,在實踐操作中,他對出版純文學作品是有一定畏難情緒的。現在并沒有什么特別讓人心動的純文學創作者,讓他愿意拋棄市場巨大的誘惑,為之鋌而走險。
“坦白地講,我們公司的產品,至少有50%并不符合我本人的理想和價值觀,但我也得支持它們,因為市場對它們有需求,它們能讓我的企業生存下去。我盡量讓我的東西能長遠一些,有價值一些。但必須得承認其中很多東西是快速消費品。”
談轉型:內容為王
在黃雋青看來,出版市場“表面繁榮”,內在問題卻非常多,“傳統出版業一定會出現特別大的問題。我不知道會是什么時候,只知道它一定會降臨。也許就像百年老店瞬間倒掉一樣,會有一個技術上的革新,突然間宣告傳統出版業的末日就要到來。”
因為有這樣的危機意識,中南博集天卷在堅持自己傳統的核心業務的同時,開始不斷做一些新的嘗試。“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人類落實到紙面的閱讀習慣可能會大受沖擊,但是對于‘內容’的需求卻會長期存在。”對于這個“內容輸出”的理念,目前或許沒有比“杜拉拉”更好的范本:從發現網絡上流傳的一個2000字的職場故事、到策劃《杜拉拉升職記》的創作及上市、再到逐漸衍生至影視、話劇、相關廣告等領域,杜拉拉的故事迄今已經創造了幾個億的市場價值。
但黃雋青并不僅僅滿足于內容向影視及數字出版方面的輸出。
“去年開始我們已經在開發一些新的產品,比如以一些高端客戶作為服務對象,組織文化之旅。區別于旅行社的是我們有更多的文化附加值。我們將來還會策劃一些海外的博物館之旅,同樣會有學者型的作者陪同前往。”
黃雋青深信,好的“內容”永遠都是值錢的。這個內容不一定停留在紙面上,也不見得就只能變成影視圖像。它可能隨著技術的不斷革新,不斷衍化成各種超出我們想象的形式,這也正是傳統出版業尋求突圍的方向。
黃雋青:
“缺乏創新,一窩蜂的模仿,在當下的市場上不被認為是恥辱、反而成了一種榮耀——因為來錢快。某一個題材,本來是一塊肥沃的土地,通過精耕細作并假以時日,完全可以長出參天大樹,但因為大家的瘋狂模仿和抄襲,居然可以把它快速地變成一塊鹽堿地。”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