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遲子建:不是所有愛情都能開花 也不是所有開花的愛情都會結果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4月09日10:07 來源:羊城晚報 何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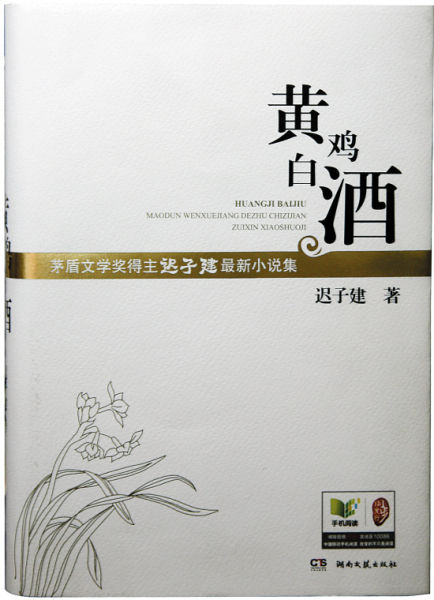

當代文壇“全能選手”談新作《黃雞白酒》《晚安玫瑰》
遲子建:
不是所有愛情都能開花
也不是所有開花的愛情
都會結果
從1983年開始寫作,到今年,遲子建整整寫了30個春秋,出版80余部單行本,共計五百余萬字。近來,她又新出版了小說集《黃雞白酒》,即將問世的還有新作《晚安玫瑰》。遲子建的作品囊括散文、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各個類型,被稱為當代文壇“全能選手”。
遲子建的作品大多以黑龍江為背景,盡管那是嚴寒的北中國,可她的文字卻總能在冰雪世界中加上一抹亮色。她說自己早期的作品純凈、憂傷,近年的作品則明顯有了悲涼氣息,但有生之艱辛,也有苦之快樂。她的文字,猶如在黑暗世界中舉起微暗的火,細小,卻讓人溫暖。
或許,正如遲子建所言:“人肯定會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蒼涼感,那么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這個蒼涼的世界上多給自己和他人一點溫暖。在離去的時候,心里不至于后悔來到這個蒼涼的世上一回。”
那時的文學氣息清新不俗
羊城晚報:據說你父親也是文學愛好者,走上寫作這條路,父親是啟蒙老師嗎?
遲子建:父親喜歡曹植的《洛神賦》,曹植字“子建”,所以他才給我取了這個名字。父親愛好文學,我的確受到他的影響,但他并未具體指點過我什么。聽我母親說,文革時很多書被禁,父親離開學校的崗位,去糧庫勞動鍛煉。怕書籍惹麻煩,于是父親把從哈爾濱千里迢迢帶到大興安嶺的書,全都用麻袋裝了,背到松樹林,一把火燒了,而書中大部分是小說作品。所以我長大以后,沒在家里看到什么書。
羊城晚報:莫言、余華、劉震云、畢淑敏都是你的研究生班同學,當時大家的交流多嗎?
遲子建:的確,你提到的這幾位作家當時都是魯院第一期研究生班的學員。那時我們開設了一些專題課程,都是與文學有關的。我記得那時還學過一段時間英語,很初級的,但大家興趣不高,這門課后來就不了了之。當時同學中只要有人有重要作品發表,我們都會互相傳看,文學氣氛很濃。那時大家都愛談文學,不像現在,大家對文學都不屑談了。
魯院那時會不定期召開一些作家作品研討會,有時還會讓我們到電影資料館觀摩一些藝術電影。我印象較深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我去紫光影院看電影,看完電影買了一支牙膏,擠上公共汽車返校,由于中途不斷上人,下車的少,我兜里的牙膏被擠爆了,滿車散發的都是那股清涼的牙膏味。那股味兒,很像那個時代的文學氣息,清新不俗。
羊城晚報:當時整個大的文學環境是怎樣的?
遲子建:大的文學環境不錯,各種文學思潮風起云涌,各路豪杰輪番登場,總有令人激動的作品出現。每個人都在埋頭寫作,沒特別富的作家,大家生活也都簡單,吃食堂,很少去飯館改善生活。
市井人物是我文學天空的星星
羊城晚報:去年,您的短篇小說結集出版,共四卷,您也曾說,編輯這套短篇文集,讀第一卷和第四卷時的感覺不同,作品的氣象變了。
遲子建:人的皺紋不是一夜之間生成的,心也不會是三兩天就變得滄桑的。早期的作品純凈,憂傷,而近些年的作品明顯有了悲涼氣息,雖然說骨子里的詩意還在。寫作的過程,就是生命的過程。而生命的過程,印在了文字里。
羊城晚報:那怎么安排中短篇和長篇?寫長篇和中短篇的節奏是怎樣的?會計劃自己今年要寫多少嗎?
遲子建:我從不計劃每年要寫多少,總是有了激情和扎實的準備后,才進入寫作。我這個人比較笨,不能同時做兩件事,所以不能同時寫幾篇小說,必須要一篇一篇地來。我的寫作速度不算快,如果寫長篇,每天不過一兩千字。
羊城晚報:談談新書《黃雞白酒》,我特別喜歡春婆婆這個人物,她有原型嗎?
遲子建:《黃雞白酒》的背景是哈爾濱,我在小說所描寫的街區生活了七八年,而且“分戶供暖”引發的供暖糾紛,也是我親歷的。我把故事放在一個老人身上,因為在玉門街那一帶,確實有這樣一位年邁老人,她常揀些易拉罐、廢紙盒之類可以賣的廢品,生活想必是艱辛的,可她臉上的神色卻是怡然自得,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每天坐的黃雞白酒那樣的小酒館,我也非常熟悉。在寫這部小說時,她自然就成了主角。在我眼里,每個市井人物都像一面多棱鏡,折射著我們這個時代,更折射著他們不同的生活側面。這里有生之艱辛和不平,也有苦中的快樂和詩意。
羊城晚報:這部小說的市井味兒十足,您平常喜歡和人打交道?
遲子建:我的確是個熱愛生活的人,哪怕一個人的小日子,也不馬虎。我很喜歡市井生活,在哈爾濱時我常逛夜市,喜歡買菜時和人聊上幾句,夜市就是生活的大舞臺,也是文學的舞臺。而我在故鄉,可以更近距離地接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他們滋養著我的寫作。
市井人物是我文學天空的星星,每一顆都有閃光點,就看作家有沒有一雙發現的眼睛。有的作家認為虛構能解決文學的一切問題,但我還是認為,生活永遠是作家重要的寫作資源,雖說不是唯一資源。
這種拒絕讓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是獨特的
羊城晚報:即將出版的新作《晚安玫瑰》,是你寫給哈爾濱的情書?
遲子建:你的這個說法很詩意啊!《晚安玫瑰》是我的近作,寫它差不多花掉三個月的時間,是我寫的篇幅最長、注入思考最多的中篇,也是我個人比較偏愛的一部作品。
小說塑造的吉蓮娜,也圓了我的一個夢,我講了哈爾濱的另一段歷史,那就是流亡到這里的猶太人的故事。《晚安玫瑰》中的每一個人,都在欲望中掙扎,通過神靈或自我救贖,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時代的風云變幻,對個人的命運的影響。
迄今為止,我寫了三部關于哈爾濱的中篇,《起舞》、《黃雞白酒》和《晚安玫瑰》,從中也可以看到這些年來,我一方面仍然在開掘故鄉的土地,也將筆觸轉向城市轉向當下的生活。前陣子有人問我對愛情的看法,我說不是所有的愛情都能開花的,也不是所有開花的愛情都會結果的。《晚安玫瑰》中的吉蓮娜和趙小娥的愛情故事,從不同方面證明了這一點。
羊城晚報:您的作品經常寫到童年和故鄉,故鄉對你的創作有何影響?
遲子建:故鄉對我來說,是生活領地,也是永遠的精神領地。我對它的認識,逐漸深入到內里,看到它的陽光,也看到了它的陰暗。一個明暗相交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學是特別世俗、樸素又特別天籟的東西,我生活的土地給予了我創作的一切。不管是在故鄉還是都市,我都愿意融入到生活中,我的心靈是向生活敞開的。
羊城晚報:你的寫作資源有過匱乏的時候嗎?
遲子建:我一直生活在最基層,所以寫作資源沒有匱乏過。如果寫不好,不是資源的問題,而是心智的問題,也就是創作能力的問題。目前來說,我還有一些儲存的故事沒有動用。
羊城晚報:那有過沮喪和挫敗的時候嗎?曾對寫作有過怎樣的疑惑?
遲子建:當然有過沮喪的時期。比如九十年代中期,我沉下心來寫出《白銀那》、《日落碗窯》兩部中篇,卻雙雙遭遇退稿,那時這類作品歸不到任何“思潮”類下,顯得不入流。
但恰恰是這種“拒絕”,讓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是獨特的,更堅定地寫自己的東西。
文學不能改變世界,但能拯救心靈
羊城晚報:回頭看,這幾十年,寫作給你帶來最多的是什么?你希冀自己的文字對這個世界有所改變嗎?
遲子建:我是1983年開始寫作的,今年剛好三十年。我還記得最初寫作《北極村童話》時,心中的那種憂傷和美好。雖然歲月讓我有了白發,霜雪也由外部浸入到內心,讓我感受到世態的寒涼,但只要進入文學,那種憂傷和美好的感覺依然在。文學不能改變世界,但它能拯救心靈。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好作家就是一個牧師。牧師用經義布道,作家用的是從心靈流淌出的文字。
我覺得,對當代作家來講,我們所經歷的時代是前所未有的,人性也從來沒有這么復雜過。我說過,小時候我覺得滿世界都是神靈,現在我卻在人間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鬼。
羊城晚報:現在對自己的寫作還有怎樣的期待?理想的寫作境界是怎樣的?
遲子建: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文藝報》發表了一篇《遙遠的境界》,以一顆年輕的心,闡述我的寫作理想。我在結尾寫道:“真正的藝術是腐爛之后的一個骨架,一個純粹的骨架,它離我們看似很切近,其實十分遙遠”,我想“遙遠”這個詞,依然是我今天要說的,雖然我已不再年輕,雖然我在這二十多年間,寫出了幾百萬字的作品,但我依然覺得,好的寫作還在前方。
熱點
談蕭紅:我為她那些寂寞憂傷的文字難過得慌
羊城晚報:談談蕭紅吧,您怎么看她的作品?她的作品對您有過怎樣的影響?有人說最近上映的電影《蕭紅》“只見情史,不見寫作”,您怎么看?
遲子建:關于蕭紅,談得實在太多了!去年在首屆“蕭紅文學獎”頒獎晚會上,我在致辭中說了這樣一段話:“一百年前,也是這樣的春天,在清澈的呼蘭河畔,一朵來自天堂的花兒——蕭紅,在人間萌芽,生長,開始了她生命和寫作的行旅。她在短暫的生命里怒放,讓一百年后的我們,能夠在今天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體味這個名字永不消散的芬芳,感受她的作品帶給我們的藝術光輝!在那個人間多寒露的年代,在動蕩漂泊之中,蕭紅以她柔弱的身軀,頑強地抵御著外部世界的風寒,并以一顆敏感而善良的心,用她那支絢麗的筆,記錄下舊中國人民的苦難,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物畫廊。王阿嫂、翠姨、馬伯樂、小團圓媳婦、馮歪嘴子等經典形象,令讀者過目不忘;蕭紅還以她的筆,抒寫內心的憂傷、愛戀與悲涼,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個性鮮明的蕭紅,一個不屈的蕭紅,一個在坎坷命運中依然緊握著筆,向那渾噩世事發出獨特吶喊的偉大作家,一個一生都在渴望幸福與安寧的女性”。
因為在北京開兩會,我錯過了去影院觀看電影《蕭紅》,但那句電影廣告詞“蕭紅——點燃了六個男人的激情”,讓我為蕭紅那些寂寞憂傷的文字難過得慌!
羊城晚報:雖然您開了微博,但很少寫,你怎么看網絡對作家的影響?
遲子建:我沒有博客,但曾經有人冒我名開了,還在博客里大談寫作經驗,新浪知道不是我開的博客,關閉了這個冒名的博客。博主是個比較喜歡我作品的讀者,也沒惡意,但冒我名來談寫作,就不好。
開微博也是出于這個考慮,這樣就不會有人冒我的名開微博了。我不常上微博,覺得耽誤時間。我更愿意把上微博的時間用來讀書。我也不在網上讀書,喜歡紙質閱讀。也許我傳統,還是覺得讀電子書和紙質書的感覺不一樣。
鏈接
遲子建,女,1964年元宵節出生于漠河。1984年畢業于大興安嶺師范學校。1987年入北京師范大學與魯迅文學院聯辦的研究生班學習,1990年畢業后到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工作至今。1983年開始寫作,已發表以小說為主的文學作品五百余萬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單行本。主要作品有:《偽滿洲國》、《額爾古納河右岸》、《北極村童話》、《清水洗塵》、《霧月牛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我的世界下雪了》等。
曾獲得第一、二、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等多種文學獎勵。作品有英、法、日、意、韓等海外譯本。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