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作家寧肯:世外桃源并不存在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4月01日10:00 來源:魯北晚報 作家寧肯近照 ▲
作家寧肯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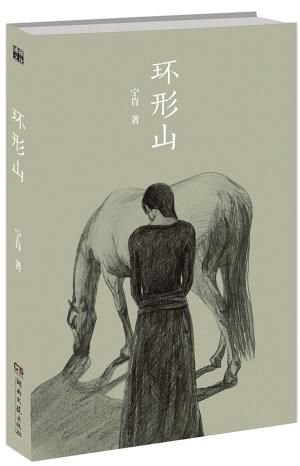 《環形山》 寧肯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環形山》 寧肯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寧肯:當代最具探索意識的作家之一。1959年生于北京,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西藏生活多年,現為《十月》雜志副主編。2001年《蒙面之城》出版,轟動文壇,榮獲老舍文學獎、《當代》文學拉力賽總冠軍、全球中文網最佳小說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提名。此后十多年,相繼出版了《沉默之門》《環形山》《天·藏》三部長篇,每部長篇都深受好評。《沉默之門》獲得紅樓夢文學獎、鼎均文學獎等多項提名。《環形山》因其獨特的風格,被評論界認為是“一部為中國文學增加異質的小說”。《天·藏》再次獲得老舍文學獎、首屆施耐庵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提名,被認為是一部無論形式內容都“可以反哺歐洲的小說”。《環形山》通過描繪奇異的社會景觀,呈現出人們病態的心理和極端的行為,暗示了現代人在物質武裝下的精神荒蕪,是當代文學的新收獲。
寧肯:世外桃源并不存在
>>環形山是美與荒涼的分裂
盛文強:“環形山”給人的直觀感受是星體的劇烈碰撞、荒涼、死寂,還有一種來自外太空異質空間的神秘,您為什么以“環形山”作為小說的題目?
寧肯:因為“環形山”符合我的小說的整體感覺,環形山所傳遞的荒涼、神秘以及激烈的碰撞,在風格上也和我的小說接近。環形山是月球上的典型地貌,月亮上的陰影就是環形山,在我們看來,夜晚的月亮很美,但那里實際上卻很荒涼,死氣沉沉,沒有任何生命,這也符合小說女主人公簡女士的分裂性格:白天她是意氣風發的環保主義者,到了晚上,她就成了情感虐戀的主角,從隱喻的角度來看,用“環形山”這一意象比較準確,環形山與簡女士同屬美與荒涼的兩級分裂。另外,簡女士本身也住在一個山谷里,她在這里建造了美麗的莊園,整個故事的外部地貌環境也和環形山相似,所以我用“環形山”作為小說題目。
盛文強:通過閱讀《環形山》不難發現,您的小說邏輯精準、文字輕盈,帶有幽暗而又不羈的調子,讀完頓感滿目蒼涼,這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寧肯:這種風格的形成,有兩種原因,一是由題材所決定的,需要幽微、懸疑、神秘的哥特式風格來處理現有的題材,風格應當符合題材的需要;二是個人修養問題,在能力上是否能抵達,是否具備技術上的條件,這些對寫作者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需要讀和寫的長期訓練來完成。《簡愛》、《呼嘯山莊》也具備哥特式風格的某些特點,這兩部書算是在我早年的閱讀生活中比較有影響的。另外,希區柯克、卡夫卡、蒲松齡可以看做是我寫作上的師承譜系,希區柯克在懸疑電影中加入了精神分析,和大眾式的懸疑拉開了距離,而卡夫卡的荒誕、蒲松齡的魔幻都是可貴的精神背景。
>>絕望的來處多數是相通的
盛文強:《環形山》的奇異故事,以及主人公的病態心理、極端行為,直指當下物質年代的精神荒蕪。人生是一團欲望,滿足了就空虛,未滿足就痛苦。在物欲橫流的年代,空虛日漸成為普遍的圖景,這時還有沒有重建精神家園的可能?
寧肯:大方向上是有這種可能,但只能停留在藍圖層面。對簡女士而言,如果沒有密室,她已經擁有了精神家園——她的莊園出產綠色環保的水果、雞肉等等,“山莊寂靜,小鳥美好”,她平時閱讀、每天早上散步,莊園的生活就是簡女士的精神家園,但出現了密室,就構成了對精神家園的直接挑戰,密室里藏著三位被簡女士制作成活標本的男人,種種秘密堆積,世外桃源在這里轟然塌陷。重建精神家園,目的是有,道路卻無,很難有一條徹底的明確途徑來重建精神家園,因為世外桃源并不存在。尋找家園之路需要探索,不能盲目排他。
盛文強:在《環形山》的《后記》里,您指出:“這是一本絕望之書,某種徹骨的絕望情緒至今揮之不去,而且事實上越來越密不透風。”這種絕望是否自有其來處和去處?它來自何處,又當如何安置?
寧肯:絕望的來處,是主人公對生活的感受。簡女士的絕望來自社會,她幾次戀愛都被騙,首先被一個軍人騙了,然后又交往了一個來自底層的男人,抱著“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的期望,但他卻利用了她。經歷種種情感的失敗,簡女士原有的價值觀被顛覆了,由此而來的是深深的絕望,她甚至把絕望擴展到對整個人類的絕望。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常有類似的挫敗與絕望,其來處多是相通的。至于絕望的最終去處,也是模糊不清,只能靠修正現有機制的問題,通過改革、改善來實現,比如腐敗,比如種種不公,都迫切需要制度的完善。
>>寫作是我存在的一種方式
盛文強:您做雜志編輯多年,工作事務是否會影響到寫作,如何看工作與寫作的關系?
寧肯:我的寫作屬于業余寫作,我對這種生活狀態基本適應。從事編輯工作有利的一面是,可以及時和當下文壇保持聯系,建立對照關系。我最近編發了一篇方方的小說,她的底層情懷讓我感觸頗深。相對于我們的事不關己的淡漠和麻木,方方對現實的責任感是可敬的,她在這篇小說里寫到了一個來自農村的大學生,沒有社會資源,畢業就失業,生病,死去,觸目驚心。這是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和擔當,拷問現實的精神令人震撼。如果不是做編輯,就難有與同時代作家的交流溝通,寫作不能脫離現實。在寫作上當然需要大塊時間,但大塊時間很難有,我的寫作時常被日常事務打斷,現在看來,被打斷也有被打斷的好處,可以不斷回頭發現問題,不斷思考、審視,避免因誤入歧途而越走越遠。
盛文強:怎樣看待當今年代寫作的意義?
寧肯:對我來說,寫作的意義大致有兩種。一是對讀者的意義,即寫給哪一部分人看,對哪些人構成影響,作品有人欣賞、評論、溝通,這是寫作的一種重要意義。雖然我的讀者不一定很多,但確實有和我氣質相近的特別群體存在,這是精神上的同類,我為這一部分讀者而寫作;二是對個人的意義。寫作是我存在的一種方式,如果不寫作,我將會是誰?那我將是一個編輯,是一個父親,是一個丈夫……社會角色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身份,如果和別人區分不開,怎樣才能成為自己?從寫作角度來講,如果和別人區分不開,就難以抵達屬于自己的個性化寫作。哲人說“我思故我在”,對我而言,我寫作,我存在。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