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賈平凹:寫“帶燈”心情沉重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1月17日10:07 來源:新京報 姜妍新作《帶燈》源于一個鄉鎮女干部的短信,講述鄉鎮政府日常工作——救災、上訪、計劃生育、選舉……
賈平凹:寫“帶燈”心情沉重
 賈平凹:陜西省作協主席,1952年生于陜西。主要作品包括《廢都》、《秦腔》、《古爐》等,曾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和首屆紅樓夢獎。新作《帶燈》日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業余喜歡看足球,喜歡的運動員包括梅西和C羅。 孫純霞 攝
賈平凹:陜西省作協主席,1952年生于陜西。主要作品包括《廢都》、《秦腔》、《古爐》等,曾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和首屆紅樓夢獎。新作《帶燈》日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業余喜歡看足球,喜歡的運動員包括梅西和C羅。 孫純霞 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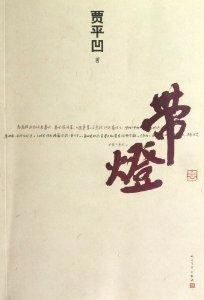 《帶燈》講述一個名叫“帶燈”的女鄉鎮干部,原名叫“螢”,即螢火蟲,這個名字也顯示了她的命運。作為鎮綜合治理辦公室的主任,她主要負責處理糾紛和上訪事件,農村的瑣事讓人心煩又讓人同情,帶燈在矛盾中完成著自己鄉鎮干部的職責,她既不愿意傷害百姓,又要維持基層社會的穩定。在現實中無處可逃時,她把精神寄托放在了遠方的情感上。
《帶燈》講述一個名叫“帶燈”的女鄉鎮干部,原名叫“螢”,即螢火蟲,這個名字也顯示了她的命運。作為鎮綜合治理辦公室的主任,她主要負責處理糾紛和上訪事件,農村的瑣事讓人心煩又讓人同情,帶燈在矛盾中完成著自己鄉鎮干部的職責,她既不愿意傷害百姓,又要維持基層社會的穩定。在現實中無處可逃時,她把精神寄托放在了遠方的情感上。《帶燈》故事緣自賈平凹兩年多前偶然收到的一條短信,來自帶燈的原型人物,這也開啟了賈平凹了解鄉鎮干部生活的一扇門。螢火蟲成為了帶燈這個人物的各種隱喻,努力用自帶的微弱燈光照亮四周。
但她真的能夠成功嗎?
在1989年,加西亞·馬爾克斯在《迷宮中的將軍》中也有一段關于螢火蟲的描寫。到底怎樣才能讓螢火蟲活下去并在下一個夜晚繼續發出光芒?馬爾克斯書中那位把螢火蟲當首飾的美麗女生給出的答案是,把螢火蟲放入隨身攜帶的一小截挖空的甘蔗里面。就是這么簡單,可以讓微弱短暫的光點活下去。
多希望“帶燈”也能讀過這樣一本書。
緣起
一個鄉鎮女干部的短信
新京報:你在書的后記里面說,寫《帶燈》的緣起是因為一個鄉鎮女干部偶然給你發短信。你第一次收到她的短信是什么時候?
賈平凹:兩年多了,她不知在哪兒得到我的電話,我以為是個業余作者,后來我發現她短信寫得很有意思。短信里面啥都說,工作問題、心里的苦悶、今天都干啥了……后來我們成了朋友,啥都交流。
新京報:有人說《帶燈》是一部上訪小說,這樣說是不是就把這本小說窄化了?
賈平凹:里面接觸到一些上訪內容,但實際上《帶燈》講的是鄉鎮政府日常工作,包括了救災、上訪、計劃生育、選舉……上訪只是其中一方面。
新京報:在《帶燈》的后記里,你提到了小說結構和踢足球的關系。《帶燈》的結構有點特別,小標題非常密集。
賈平凹:小說的結構和題材有關,寫《廢都》時就一章,不分段。到《秦腔》和《古爐》,細節很多。后來我看巴塞羅那隊踢球,覺得消解了傳統的陣型和戰術的踢法,和不倚重故事情節的這兩部小說一樣。踢球其實大腳開最容易,但是在人窩里傳球要求就高很多,必須要戰術清晰、技術熟練,在細節調配上特別講究。《帶燈》里面有一些基層上訪黑暗的東西,怕讀者讀久了厭煩,必須不停地分小節,讓讀者有個空間。
新京報:分節有什么規律?
賈平凹:一般作家的分節是一個故事完了以后分一節,《帶燈》不是,有時是一個故事,有時是一段時間,隨意性特別大。這種形式感,慢慢玩味很有意義。其實這樣寫我是受了《舊約圣經》的啟發,里面“創世紀”也是偶然分節,也是穿插了很多生活感悟、智慧的東西。
隱喻
好多人不一定看得出
新京報:《帶燈》里面寫到了皮虱,這也是一種隱喻?
賈平凹:虱子隱喻了很多,包括環境的污染,也隱喻了開發可能帶來的別的災難,比如水污染等等。到底是開發好還是不開發好?書里面有句話是我曾經寫給貴州銅陵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不開發其實是大開發。”你保護住了這里,多少年后大家都要來參觀。
新京報:在《帶燈》的開頭,帶燈一開始想要治理虱子,但沒成功,最后自己也染上了虱子,這也是一種暗示?
賈平凹:在這種環境,必然你要異化。帶燈很善良,想給農民辦事,但是辦不了的時候她就用些非正常手段來幫助農民。而且她同時對農民也很厲害,連欺騙帶威脅。書封二頁有這樣一句話——“我的命運就是佛桌邊燃燒的紅蠟,火焰向上,淚流向下。”我覺得這句話很符合帶燈的命運。螢火蟲,黑暗中才帶燈,但燈必然微弱,而且這個燈發自身體。螢火蟲還有兇殘習性,它吃蝸牛肉。帶燈和農民打交道,面對無理取鬧的人時,她得用強硬手段。帶燈與老上訪戶王后生有段對話,帶燈問他“你怎么那么壞!”王后生說“你怎么那么兇。”“我兇還不是你逼出來的。”他倆扯平了,其實是一回事,沒有魔就沒有佛。
新京報:他們是相互依存的?
賈平凹:就是。大轉型時期發生這么多事情,城鄉差距、干部危機、能源搶占,為什么政府層層勾結的事情十多年解決不了?這些都是中國特有文化下面發生的事情。全球都在改革,但是我選的材料,都是中國文化下面呈現的東西,里面好多人情世故都是中國人的思維,好面子啊,開會時不允許上訪,這些外國人理解不來。看了我這本書,右派可能會說,你看中國這個樣子,不改革怎么能行。左派可能會說,你看,不改革哪有這樣的事情。這些都不準確。
新京報:都把問題看得太簡單。
賈平凹:對,只看到問題一面。我把問題提出,讓大家思考,這是我想的最多的。好像外國人眼中這不是問題,但往往就發生了,但我估計好多人不一定能看到其中的隱喻。我的作品不是表面特別激烈,我都是淡淡地來寫,但是隱藏的是激烈的事情。我想留下更多空間。現在好多讀者喜歡刺激性東西,喜歡夸張、暴力的寫法,其實那種寫法更好寫,刀光劍影,但是過后就過去了。我希望水面平靜,但下面是暗流。有人說我寫的不黑暗,但黑就好嗎?寫作有水和火的關系,我傾向水。水微弱,但進去就容易被淹死,火遠遠看就不敢靠近。我這種寫法有人悟性不高悟不出來你在寫啥東西,而且也不好翻譯,里面隱喻好多東西。
人生
到了深秋還得往前走
新京報:但是在結尾你還是給出了一些希望。
賈平凹:最后給大家一些向上的積極的東西,看到一大片螢火蟲的光,其實只要每個人能發一點點微光就可以了。
新京報:都是有用的。
賈平凹:對,能照亮多少是另一回事,但起碼壯觀起來了。
新京報:在小說里,帶燈給元天亮一直寫信,但是元天亮始終沒有在小說里面露面,這是你刻意為之?
賈平凹:很多人覺得元天亮肯定要出現,要和帶燈發生好多故事,那就成了愛情小說了。他始終不露面,對帶燈來說他就是一種向往。帶燈在那種環境里,她沒有精神支撐就沒辦法活了。必須靠這種幻想、追求支撐。
新京報:那你在小說里給出帶燈一個并不美好的結局,你自己難過嗎?
賈平凹:這個結局是必然的,我寫的時候心情也比較沉重,有些凄涼。這女的那么聰明,那么有想法,但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就那么被消磨。她只能是個螢火蟲,就發那么一點光。她能照亮路嗎?只能在黑暗里自己給自己照亮一點光。
新京報:這本書完成的時候,你也跨過了60歲的門檻,你在后記里也提到了這一點,60歲對你意味著什么?
賈平凹:我覺得臉紅,怎么一下子60了。人畢竟也就是活100歲之內,而我已經活這么多了。我哀嘆生命太短暫,人太渺小。現在就像到了深秋,以前春天、夏天的時候你不會想到葉子快掉落的事情,現在會感受到古人詩詞里的蒼涼調子,無奈、虛無,但是你還得往前走。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