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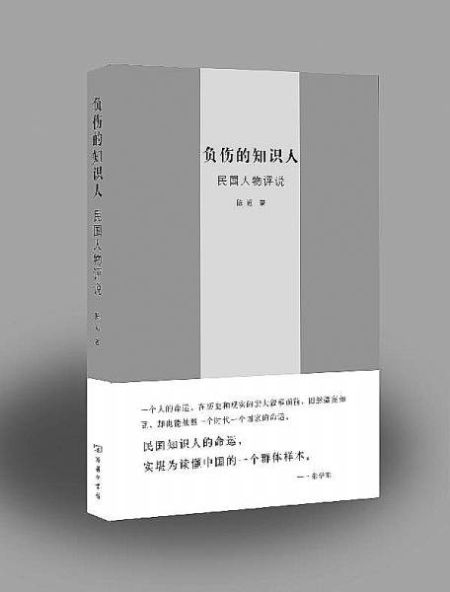
“民國”最近很熱,“民國范兒”也成了品評知識分子“熱愛自由,尋求獨立”的最高評價。然而,民國知識分子胡適、梅貽琦、梁漱溟、馮友蘭等在近代史學者陳遠的筆下,卻落得了“負傷”之評。最近,陳遠新書《負傷的知識人:民國人物評說》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波瀾與暗流
跳出了當事人“口述歷史”必然出現的感情糾葛,避開了跟隨各種史說的人云亦云路數,十多年的媒體從業經歷,令陳遠的史學研究工作留下了濃厚的“調查”痕跡。他搜集各方原始資料,著力還原民國知識分子“原生態”,探究歷史在他們身上留下的波瀾與暗流。
為什么會對民國知識分子產生研究的興趣?陳遠自述,這來源于祖父的影響。陳遠的祖父在“文革”時期歷遭劫難,這使陳遠對這段歷史十分好奇。但因在十多年前研究當代史比較困難,于是便往前追溯到了民國。
“我希望在解讀那一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同時,可以讓我更多地理解祖父在非常時期所遭遇的苦難。”陳遠說,“從舊時代到新時代,民國知識分子走過了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該書書名是其中的一篇同名文章,我覺得很貼切,就拿來用了。”
最初,陳遠只是根據自己的思考對史料重新梳理。從事記者工作后,編輯常常要求文章要有別家沒有的“料”。此時,他才意識到研究歷史也同此理。“我的第一手材料除了檔案之外,還得益于記者生涯帶來的大量來自當事人的口述實錄和他們提供的一些原始文字。這些年,給我講過故事的老人們有不少已經過世。他們留下的記憶彌足珍貴。”
陳遠在書中燭照了民國知識分子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刷新了人們以往對歷史人物的認知。比如胡適。人人皆知胡適有“寬容比自由更重要”的名言,陳遠卻發現他也有“不寬容”的一面——老同學出書請胡適寫推薦,照理不好推辭,但胡適卻因其內容的質量不高而完全拒絕,絲毫不講情面。
馮友蘭:識時務者?
再比如馮友蘭。陳寅恪曾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開頭寫道:“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這句話被后人引用甚多,而對于馮友蘭本人的“了解之同情”似乎更是不可缺少:《負傷的知識人》中有兩篇文章寫馮友蘭。《在學術和氣節的蹺蹺板上》和《被辜負的愛國心》。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界之影響無人能出其右,但對一些事件的反應卻被認為“缺少氣節”。何兆武曾在《上學記》中評價道:“馮友蘭對當權者所倡導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后一篇《應帝王》等,都是給蔣介石捧場的。”更多的指責是針對馮友蘭在“文革”時期“批林批孔運動”中的“識時務”的表現。
然而,陳遠根據自己所掌握的史料,發現馮友蘭在“文革”中從未主動批判過誰、揭發過誰、陷害過誰。而那些將其與梁漱溟相較的人,又可曾注意到一個不容忽略的細節——梁漱溟在1949年之前曾任民盟秘書長,有著特殊的政治優勢。而馮友蘭是參加過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與梁漱溟顯然不在一條起跑線上。
陳遠寫道:“那些以‘缺少氣節’指責馮先生的人,可曾想過政治的馮友蘭和學術的馮友蘭分別坐在氣節和學術的蹺蹺板上這一境遇背后的歷史情境?歷史是一面鏡子,照別人的時候,首先要照一下自己。道德也是如此。”
吳晗:迷失與良心
吳晗早年作為歷史學家為人熟知,他對政治并不感興趣。轉變發生在1940年。吳晗自己說:“1940年以后,政治來過問我了。”他因為生活艱難,甚至沒錢治病而對現實不滿,并越來越多地把歷史與現實聯系起來。但在1955年批胡適的運動中,他始終沒有去批判自己早年的導師。陳遠的朋友、廈門大學教授謝泳對此評價:“有過失誤、有過迷失,但良心還在。”
這樣的故事在書中很多。陳遠說:“每個時代的人,面對自己的時代,都有困惑。回過頭來看歷史與身在局中,完全是兩種處境。這也是我特別強調‘同情之理解’的原因所在。”
陳遠說自己并沒有刻意為歷史人物“翻案”,只是按照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對這些人物做了還原。“我會考慮人物性格和性格形成的環境。‘歷史的必然性’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歷史也充滿了偶然——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每個個體在不同歷史情境下所作出的反應是不同的。”
《負傷的知識人》是一本歷史隨筆,雖然話題和故事都略嫌沉重,但陳遠研究歷史的樂趣“更多的是與歷史人物對話,體察他們的艱辛與苦難,感受他們的光榮與理想,洞悉他們的狡黠與躲閃……這些樂趣大于‘以史為鑒’”。
“民國知識分子有著共同的氣質,一是自由精神,二是極富理想。這種氣質,是我極為向往的。”陳遠說。雖然風流人物已被雨打風吹去,但讀這本書,民國知識人的氣質依稀可辨。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