ųąć°(gu©«)ū„╝ęŠW(w©Żng)>> įLšä >> ū„╝ęįLšä >> š²╬─
±TŲõė╣:▓╗£ńŪ¾īW(xu©”)Ū¾šµų«ą─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2─Ļ12į┬05╚š10:02 üĒ(l©ói)į┤Ż║╬─ģRł¾(b©żo) └ŅōP(y©óng)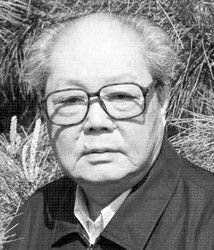 łDŲ¼ū„š▀Ż║ČĪ║═ łDŲ¼šf(shu©Ł)├„Ż║±TŲõė╣Ž╚╔·Į³ė░ĪŻ
łDŲ¼ū„š▀Ż║ČĪ║═ łDŲ¼šf(shu©Ł)├„Ż║±TŲõė╣Ž╚╔·Į³ė░ĪŻ  łDŲ¼ū„š▀Ż║ČĪ║═ łDŲ¼šf(shu©Ł)├„Ż║╬╗ė┌¤o(w©▓)ÕaĄ─±TŲõė╣īW(xu©”)ąg(sh©┤)^īóė┌12į┬9╚šķ_(k©Īi)^ĪŻłD×ķ═ŌŠ░ĪŻ Š∙ČĪ║═öz
łDŲ¼ū„š▀Ż║ČĪ║═ łDŲ¼šf(shu©Ł)├„Ż║╬╗ė┌¤o(w©▓)ÕaĄ─±TŲõė╣īW(xu©”)ąg(sh©┤)^īóė┌12į┬9╚šķ_(k©Īi)^ĪŻłD×ķ═ŌŠ░ĪŻ Š∙ČĪ║═özĪĪĪĪī”(du©¼)ė┌90ÜqĖ▀²gĄ─±TŲõė╣Ž╚╔·üĒ(l©ói)šf(shu©Ł)Ż¼Į±─Ļ╩ŪĖ±═Ō├”┬ĄČ°ėų┴Ņ╚╦Ž▓ÉéĄ─ę╗─ĻĪŻ─Ļ│§Ż¼ģRŠ█┴╦Ž╚╔·ę╗╔·īW(xu©”)ąg(sh©┤)Š½╚AĄ─1700╚f(w©żn)ūųĪó35ŠĒāį(c©©)Ą─ĪČ╣Ž’łśŪģ▓ĖÕĪĘĖČĶ„│÷░µŻ¼╗═╗═Š▐ų°Ż¼║±ųž▓®č┼Ż╗5į┬Ż¼ęÄ(gu©®)─Ż║Ļ┤¾Ą─Ī░±TŲõė╣Š┼╩«įŖ(sh©®)Ģ°(sh©▒)«ŗ(hu©ż)š╣Ī▒į┌ųąć°(gu©«)├└ąg(sh©┤)^┼eąąŻ¼įŖ(sh©®)╬─┼cĢ°(sh©▒)«ŗ(hu©ż)╣▓├└Ż¼╗©╗▄┼c╔Į╦«Ėé(j©¼ng)ąŃŻ╗╩«į┬ć°(gu©«)æcŻ¼Ž╚╔·śsŌ▀╩ū┤╬ŅC░l(f©Ī)Ą─Ī░ģŪė±š┬╚╦╬─╔ńĢ■(hu©¼)┐ŲīW(xu©”)ĮK╔Ē│╔Š═¬ä(ji©Żng)Ī▒Ż¼▀@śsūu(y©┤)╩Ū▒Ēš├Ž╚╔·į┌╚╦╬─╔ńĢ■(hu©¼)┐ŲīW(xu©”)ŅI(l©½ng)ė“ū÷│÷Ą─ū┐įĮžĢ½I(xi©żn)ĪŻ
ĪĪĪĪČ°┤╦Ģr(sh©¬)┤╦┐╠Ż¼╝ęÓl(xi©Īng)¤o(w©▓)Õa×ķ±TŽ╚╔·╗Iéõ┴╦3─Ļų«Š├Ą─Ī░±TŲõė╣īW(xu©”)ąg(sh©┤)^Ī▒▀M(j©¼n)╚ļ┴╦ūŅ║¾Ą─Ą╣ėŗ(j©¼)Ģr(sh©¬)Ż¼12į┬9╚šŻ¼▀@éĆ(g©©)╩š▓žų°±TŽ╚╔·ūŅ×ķšõ┘FĄ─╩ųĖÕĪóĢ°(sh©▒)«ŗ(hu©ż)Īó╬─╬’Ą─īW(xu©”)ąg(sh©┤)^īó┼c╩└╚╦ęŖ(ji©żn)├µĪŻ
ĪĪĪĪ±TŲõė╣īW(xu©”)ąg(sh©┤)^Ą─5éĆ(g©©)š╣Åd▒╗├³├¹×ķĪ░ĄŠÓl(xi©Īng)╝ę╩└Ī▒ĪóĪ░ŲDļyīW(xu©”)│╠Ī▒ĪóĪ░║▓─½ėÓŽŃĪ▒ĪóĪ░Õ½║Ż╣┬š„Ī▒ĪóĪ░ĘŠē▀z█EĪ▒Ż¼┤·▒Ēų°Ž╚╔·Ą─│╔ķL(zh©Żng)Üv│╠ĪóīW(xu©”)ąg(sh©┤)│╔Š═ĪóĢ°(sh©▒)Ę©└L«ŗ(hu©ż)Īó╬„▓┐╬─╗»özė░Ż¼ęį╝░╣┼┤·╩»┐╠╩š▓žĪŻ
ĪĪĪĪ±TŲõė╣Ž╚╔·╦žęį╝tīW(xu©”)蹊┐ōP(y©óng)├¹ė┌╩└Ż¼ģs║▄ļyė├ę╗éĆ(g©©)į~šZ(y©│)├Ķ╩÷Ųõ╔ĒĘ▌Ż¼ę“?y©żn)ķŽ╚╔·▓╗āHØōą─ė┌īW(xu©”)å¢(w©©n)Ż¼Č°Ūę╝─Ūķė┌įŖ(sh©®)Ģ°(sh©▒)Ż¼ĮY(ji©”)Šēė┌║▓─½Ż¼Ę┼┬├ė┌╠ņŽ┬Ż¼╚╬│ųūįąįŻ¼▓╗Šąę╗Ė±ĪŻ╗©╝ūų«─Ļ║¾Ż¼ÜvĢr(sh©¬)20─ĻŻ¼╩«▀M(j©¼n)ą┬Į«Ż¼╚²╔Ž┼┴├ūĀ¢Ė▀įŁŻ¼┤®įĮ┴_▓╝▓┤Ż¼Ąų▀_(d©ó)║Ż░╬4900├ūĄ─╝tŲõ└ŁĖ”║═║Ż░╬4700├ūĄ─├„ĶF╔w╔Į┐┌Ż¼īŹ(sh©¬)Ąž┐╝ėåą■▐╩╚ĪĮø(j©®ng)¢|Üw┬ĘŠĆŻ╗╣┼ŽĪų«─Ļ║¾Ż¼╚²Č╚į┌ųąć°(gu©«)├└ąg(sh©┤)^┼e▐kĪ░±TŲõė╣«ŗ(hu©ż)š╣Ī▒Ż¼▒╗ūu(y©┤)×ķĪ░šµš²Ą─╬─╚╦«ŗ(hu©ż)Ī▒Ż╗ļŻ±¾ų«─ĻŻ¼│÷╚╬ųąć°(gu©«)╚╦├±┤¾īW(xu©”)ć°(gu©«)īW(xu©”)į║į║ķL(zh©Żng)Ż¼äō(chu©żng)▐kĪ░╬„ė“Üv╩ĘšZ(y©│)čį蹊┐╦∙Ī▒Ż¼╠ß│÷Ī░┤¾ć°(gu©«)īW(xu©”)Ī▒Ė┼─ŅŻ¼īó╬„ė“?q©▒)W╝{╚ļć°(gu©«)īW(xu©”)蹊┐ęĢę░ĪŻ
ĪĪĪĪį┌╝┤īóåó│╠╗ž?z©”)oÕa×ķīW(xu©”)ąg(sh©┤)^Įę─╗Ū░Ž”Ż¼±TŽ╚╔·│ķ│÷┴╦ā╔éĆ(g©©)╔Ž╬ńĄ─Ģr(sh©¬)ķgŻ¼ą└╚╗Įė╩▄┴╦╬ęĄ─▓╔įLŻ¼╗žŅÖūį╝║ū▀▀^(gu©░)Ą─īW(xu©”)ąg(sh©┤)ų«┬ĘĪŻ
ĪĪĪĪŪ¾Ą└ų«┬ĘŻ¼Ė╣ėąĢ°(sh©▒)įŖ(sh©®)ÜŌūįź
ĪĪĪĪ±TŲõė╣Ž╚╔·░ߥĮ▒▒Š®═©ų▌Åł╝ę×│Ą─ąĪį║ęčĮø(j©®ng)16─Ļ┴╦Ż¼į║ųąŽ╚╔·«ö(d©Īng)─Ļ╩ųų▓Ą─ę╗┐├ę╗╚╦Ė▀Ą─║Ż╠─Ż¼╚ńĮ±ęč╩Ū═ż═ż╚ń╔wĪŻĪ░╣Ž’łśŪĪ▒Ż¼─╦Ž╚╔·═Ē─ĻūĪ╦∙Ą─č┼╠¢(h©żo)Ż¼╩Ū×ķėøūĪį°Įø(j©®ng)ęį╣Ž┤·’łĄ─┐ÓļyÜqį┬ĪŻį┌±T└ŽĄ─╝ęųą▀ĆšµĄ─┐┤ĄĮ┴╦ū└╔ŽĄž╔Žö[ų°Ą─┤¾─Ž╣ŽŻ¼║═ē”╔ŽĪ░╣Ž’łśŪĪ▒╚²éĆ(g©©)śŃśŃīŹ(sh©¬)īŹ(sh©¬)Ą─┤¾ūųŽÓė││╔╚żŻ¼─Ū╩Ūäó║Ż╦┌Ž╚╔·94ÜqĢr(sh©¬)╦∙Ģ°(sh©▒)ĪŻ
ĪĪĪĪ90ÜqĄ─±TŲõė╣Ž╚╔·Ż¼ļm╚╗▓Į┬─▓╗╦ŲÅ─Ū░─Ū├┤│CĮĪŻ¼Ą½╩ŪŠ½╔±ę└╚╗╩«Ęų█ŪĶpŻ¼Ž±─Ļ▌pĢr(sh©¬)ę╗śėŻ¼├┐╠ņ╚į╚╗╣żū„ĄĮ╔Ņę╣ĪŻ±TŽ╚╔·Ą─Ę“╚╦Ž─ŪŖõĖŽ╚╔·ĖµįV╬ęŻ¼80Üqęį║¾Ż¼╝┤▒Ńį┌▓ĪųąŻ¼╝┤▒Ńį┌╔Ņę╣ę╗ā╔³c(di©Żn)ńŖŻ¼±TŽ╚╔·ų╗ꬎļĄĮ╩▓├┤īW(xu©”)ąg(sh©┤)╔ŽĄ─å¢(w©©n)Ņ}Ż¼ę▓Ģ■(hu©¼)┼¹ę┬Ž┬┤▓▓ķĢ°(sh©▒)Īó▓ķ┘Y┴ŽĪŻ
ĪĪĪĪ▓╔įL±TŽ╚╔·▀@ā╔╠ņŻ¼▒▒Š®ĒæŪńŻ¼£ž┼»Ą─Ļ¢(y©óng)╣Ōšš▀M(j©¼n)╬▌└’Ż¼ę╗▓óīó┤░═Ō║Ż╠─║═╦╔śõ(sh©┤)ōuęĘĄ─ų”ė░×ó▀M(j©¼n)╬▌└’Ż¼×óį┌±TŲõė╣Ž╚╔·Š½╔±’¢ØMĄ──ś╔ŽŻ¼Ž─Ž╚╔·×ķ╬ęéāĖ„┼▌┴╦ę╗▒ŁŪÕ▓ĶŻ¼░ķų°Ļ¢(y©óng)╣Ō║═▓ĶŽŃŻ¼±TŽ╚╔·╗žæøŲūį╝║Ą─ūxĢ°(sh©▒)┼cų╬īW(xu©”)ų«┬ĘŻ¼µĖµĖĄ└üĒ(l©ói)ĪŻ
ĪĪĪĪ±TŲõė╣Ž╚╔·│÷╔·į┌ĮŁ╠K¤o(w©▓)Õa▒▒Ól(xi©Īng)Ū░ų▐µé(zh©©n)Ą─ę╗éĆ(g©©)▐r(n©«ng)├±╝ę═źŻ¼ę“╝ęŠ│žÜ║«Ż¼╦¹Ą─ąĪīW(xu©”)ĪóųąīW(xu©”)Ż¼ūxūx═Ż═ŻŻ¼┐┐Ą─╩Ūę╗▀ģĘNĄžŻ¼ę╗▀ģ┐╠┐ÓūįīW(xu©”)Ż¼Ų┌ķgŻ¼ėųĮø(j©®ng)Üv┴╦░╦─Ļ┐╣æ(zh©żn)Ż¼’¢ćL╩“ļxų«▒»ĪŻĪ░─ŪĢr(sh©¬)╬ęĄ─ūxĢ°(sh©▒)Łh(hu©ón)Š│Ż¼Š═╩ŪĘNĄžĪóĘ┼č“ĪóČŃ╚š▒Š╣ĒūėĪŻĪ▒±T└Ž╗žæøĄ└ĪŻąĪīW(xu©”)5─Ļ╝ē(j©¬)╩¦īW(xu©”)║¾Ż¼į┌æ(zh©żn)üyĄ─┐ÓļyųąŻ¼╦¹ūĒą─ė┌ūxĢ°(sh©▒)Īóīæ(xi©¦)ūų║═«ŗ(hu©ż)«ŗ(hu©ż)Ż¼į┌ĘNĄžų«ėÓŻ¼│┴ūĒŲõųąĪŻø](m©”i)ÕX(qi©ón)┘I(m©Żi)Ģ°(sh©▒)Ż¼╦¹¢|ĮĶ╬„ĮĶŻ¼▓╗šōąĪšf(shu©Ł)æ“Ū·Ż¼╠ŲįŖ(sh©®)╦╬į~Ż¼╗“šōĪó├ŽĪóū¾Īó╩ĘŻ¼ų╗ę¬─▄ĮĶĄĮ╦¹Š═╚ńć╦Ų┐╩ĄžūxŻ¼Ī░╠ņ╠ņūxĄĮ╔Ņę╣Ż¼įń│┐Ž┬╠’ĄžŪ░ę▓ę¬ūxŻ¼Å─Ąž└’╗žüĒ(l©ói)Ż¼─Ó═╚ø](m©”i)Ž┤ā¶Š═▀M(j©¼n)╬▌┐┤Ģ°(sh©▒)Ī▒Ż¼±TŽ╚╔·æøĄ└ĪŻ╚ń┤╦3─ĻūįīW(xu©”)Ž┬üĒ(l©ói)Ż¼╦¹Š╣ūx┴╦įSČÓĢ°(sh©▒)Ż¼ėąĄ─╔§ų┴─▄▒│šbŻ¼Ī░ĪČĖĪ╔·┴∙ėøĪĘī”(du©¼)╬ę║¾üĒ(l©ói)īæ(xi©¦)╬─š┬ė░Ēæ║▄╔ŅŻ¼╦³Ą─╬─╣P╠½Ų»┴┴┴╦Ż¼▀Ćėą═Ē├„ąĪŲĘŻ¼ÅłßĘĪČ╬„║■ē¶(m©©ng)īżĪĘĪóĪČ╠šŌųē¶(m©©ng)æøĪĘĪóĪČ¼ś?g©░u)ų╬─╝»ĪĘŻ¼╩Ęš┴ųĪČ╬„ŪÓ╔óėøĪĘĪóĪČ╬„ŪÓ╣PėøĪĘĪóĪČ╚AĻ¢(y©óng)╔óĖÕĪĘŻ¼╬ęĄ─╬─š┬┴”Ū¾ŪÕ═©Īó×t×óŻ¼Š═╩Ū╩▄═Ē├„ąĪŲĘĄ─ė░ĒæĪŻĪ▒
ĪĪĪĪ±T└Ž▀Ć╗žæøŻ¼ūxĄĮĪČ┤¾┤╚Č„╦┬╚²▓žĘ©Ä¤é„ĪĘĢr(sh©¬)Ż¼╦¹▒╗▀@╬╗╩ź╔«ęį╚f(w©żn)╦└▓╗▐oĄ─ė┬ÜŌĖ░╬„╠ņ╚ĪĮø(j©®ng)Ą─Š½╔±╦∙š║│ĪóĖąäė(d©░ng)Ż¼▀@Š½╔±▓╗ų¬▓╗ėX(ju©”)į┌╦¹─Ļ╔┘Ą─ą─└’ĘNŽ┬┴╦Ū¾īW(xu©”)Ū¾šµĄ─ĘNūėĪŻ
ĪĪĪĪ±T└ŽĄ─ėøæø┴”╩«Ęų¾@╚╦Ż¼╠ßŲā║Ģr(sh©¬)ūx▀^(gu©░)Ą─Ģ°(sh©▒)Ģr(sh©¬)Ż¼─▄┴ó╝┤│÷┐┌│╔šbŻ¼į┌šä╝░įń─ĻĄ─┴╝ĤęµėčĢr(sh©¬)Ż¼Ė³╩Ūėøæø¬qą┬ĪŻ╦¹æøŲ20Üq─Ū─Ļį┌¤o(w©▓)Õa╣żśI(y©©)īŻ┐ŲīW(xu©”)ąŻĢr(sh©¬)Ż¼░▌ūR(sh©¬)┴╦╔Į╦««ŗ(hu©ż)╝ęųTĮĪŪ’Ż¼ųTŽ╚╔·╠žįS╦¹╚ļ«ŗ(hu©ż)╩ęė^Ųõū„«ŗ(hu©ż)Ż¼▀Ćšf(shu©Ł)Ī░┐┤Š═╩ŪīW(xu©”)Ī▒Ż¼ūį┤╦Ż¼±TŲõė╣į┌ųTŽ╚╔·«ŗ(hu©ż)╩ęė^─”░ļ─ĻŻ¼ė╔┤╦┬įų¬╔Į╦««ŗ(hu©ż)ų«ķT(m©”n)ÅĮĪŻ╦¹Ą─ā╔╬╗ć°(gu©«)╬─└ŽÄ¤Ż¼įŖ(sh©®)╚╦ŅÖÜJ▓«║═į~╚╦Åł│▒Ž¾Č╝┘pūR(sh©¬)╦¹Ą─╬─▓┼Ż¼«ö(d©Īng)╦¹éā┼cųTĮĪŪ’ę╗ŲĮM┐ŚĪ░║■╔ĮįŖ(sh©®)╔ńĪ▒Ż¼▒Ńč¹±TŲõė╣ū„įŖ(sh©®)Ż¼ė┌╩Ū╦¹īæ(xi©¦)Ž┬╔·ŲĮĄ┌ę╗╩ūįŖ(sh©®)Ż║Ī░¢|┴ų╩Żėą▓▌┐vÖMŻ¼║Żā╚(n©©i)║╬╚╦└m(x©┤)┼f├╦ĪŻĮ±╚š║■╔ĮųžĮY(ji©”)╔ńŻ¼š±┼dĮ^īW(xu©”)š╠Ž╚╔·ĪŻĪ▒ÅłŽ╚╔·┐┤║¾Ż¼┼·šZ(y©│)Ī░ŪÕ┐ņŻ¼ėąįŖ(sh©®)▓┼Ī▒ĪŻųTŽ╚╔·ätęį╦∙«ŗ(hu©ż)╔╚├µ┘ø(z©©ng)ų«ĪŻį┌¤o(w©▓)Õa╣żīŻ╦¹āHūx┴╦ę╗─ĻŻ¼╝┤ę“žÜ╩¦īW(xu©”)Ż¼Ą½╩Ū▀@ę╗─Ļģs╩Ū╦¹į┌įŖ(sh©®)į~║═└L«ŗ(hu©ż)╔Žåó├╔Ą─ę╗─ĻĪŻ
ĪĪĪĪ1946─Ļ┤║Ż¼╦¹┐╝╚ļ¤o(w©▓)Õać°(gu©«)īŻŻ¼±TŽ╚╔·šf(shu©Ł)Ż¼į┌¤o(w©▓)Õać°(gu©«)īŻūxĢ°(sh©▒)Ą─3─Ļ╩Ū╦¹╚╦╔·Ą─▐D(zhu©Żn)š█³c(di©Żn)Ī¬Ī¬į┌▀@└’Ż¼╦¹Ą├ė÷įSČÓ├¹Ä¤ųĖ³c(di©Żn)Ż¼×ķ╦¹ĄņČ©┴╦ū▀╔ŽīW(xu©”)å¢(w©©n)Ą└┬ĘĄ─╗∙ĄA(ch©│)ĪŻų▄╣╚│Ūųv╩┌ųąć°(gu©«)═©╩ĘŻ¼═»Ģ°(sh©▒)śI(y©©)ųv╩┌ŪžØh╩ĘŻ¼▓╠╔ą╦╝ųv╩┌ųąć°(gu©«)╦╝Žļ╩ĘŻ¼ųņ¢|ØÖ(r©┤n)ųvĪČ╩ĘėøĪĘĪóĪČČ┼įŖ(sh©®)ĪĘŻ¼äóįŖ(sh©®)╔pųvĪČ╝tśŪē¶(m©©ng)ĪĘŻ¼±Tš±ą─ųv╩┌╬─ūųīW(xu©”)Ą╚Ż¼╩╣╦¹č█ĮńąžĮ¾┤¾ķ_(k©Īi)ĪŻę╗┤╬Ż¼īW(xu©”)ąŻšł(q©½ng)üĒ(l©ói)ÕX(qi©ón)─┬Ž╚╔·ųvū∙Ż¼ÕX(qi©ón)Ž╚╔·ųvĄĮū÷īW(xu©”)å¢(w©©n)ę¬Å─┤¾╠Äų°č█Ż¼Ī░╬ęęŖ(ji©żn)Ųõ┤¾Ī▒Ż¼▓╗ę¬ę╗ķ_(k©Īi)╩╝Š═Ń@┼ŻĮŪ╝ŌĪŻĪ░▀@ī”(du©¼)╬ęė░Ēæ║▄┤¾Ż¼╬ęęį║¾ų╬īW(xu©”)Š═┴”łDššų°╚źū÷ĪŻĪ▒±TŽ╚╔·Ą└ĪŻ
ĪĪĪĪš²╩Ūį┌¤o(w©▓)Õać°(gu©«)īŻŲ┌ķgŻ¼±TŽ╚╔·┤“Ž┬┴╦╔Ņ║±Ą─ć°(gu©«)īW(xu©”)╗∙ĄA(ch©│)Ż¼ČÓ─Ļ║¾╦¹ų„ŠÄĄ─ĪČÜv┤·╬─▀xĪĘÅV×ķ╚╦ų¬Ż¼▓ó╩▄ĄĮ├½Ø╔¢|Ą─ĘQ┘ØĪŻ
ĪĪĪĪ═»─Ļ║═ŪÓ─ĻĄ─Įø(j©®ng)ÜvŻ¼╩Ūę╗éĆ(g©©)╚╦╔·├³ų«śõ(sh©┤)Ą─Ė∙╗∙Ż¼▓╗šō╚š║¾ķL(zh©Żng)Ą├ČÓĖ▀Ż¼čė╔ņĄ├ČÓ▀h(yu©Żn)Ż¼─ŪŅw╔Ņ┬±Ą─ĘNūė╩Ū╔·├³Ą─░l(f©Ī)Č╦┼cį┤Ņ^Ż¼╬─īW(xu©”)ĪóįŖ(sh©®)į~ĪóĢ°(sh©▒)Ę©Īó└L«ŗ(hu©ż)Īó╬„ė“蹊┐Ż¼▀@ą®─Ļ╔┘Ģr(sh©¬)╝┤┬±į┌±TŲõė╣ą─└’Ą─ųŠŽ“Ż¼Š═Ž±ę╗ŅwŅwĘNūėŻ¼į┌Įø(j©®ng)─Ļ▓╗öÓĄ─Ū┌Ŗ^Ė¹į┼║¾Ż¼ūŅĮKČ╝ĮY(ji©”)│÷┴╦žS┤TĄ─╣¹īŹ(sh©¬)ĪŻ
ĪĪĪĪ1954─ĻŻ¼į┌¤o(w©▓)ÕaĄ┌ę╗┼«ųą╚╬Į╠Ą─±TŲõė╣Ż¼ĘŅš{(di©żo)ĄĮųąć°(gu©«)╚╦├±┤¾īW(xu©”)╚╬ć°(gu©«)╬─Į╠ĤŻ¼ļxķ_(k©Īi)┴╦╝ęÓl(xi©Īng)¤o(w©▓)ÕaŻ¼üĒ(l©ói)ĄĮ▒▒Š®Ż¼ķ_(k©Īi)╩╝┴╦šµš²Ą─īW(xu©”)ąg(sh©┤)ų«┬ĘĪŻ
ĪĪĪĪØōą─╝tīW(xu©”)Ż¼ŲĮ╔·┐╔įS╩Ūų¬ę¶
ĪĪĪĪ1700╚f(w©żn)ūųĪó35ŠĒāį(c©©)Ą─±TŲõė╣╬─╝»ĪČ╣Ž’łśŪģ▓ĖÕĪĘĮ±─Ļ1į┬š²╩Į│÷░µŻ¼╗═╗═Š▐ų°Ż¼║±ųž▓®č┼Ż¼ģRŠ█┴╦Ž╚╔·ę╗╔·Ą─īW(xu©”)ąg(sh©┤)Š½╚AŻ¼Ųõā╚(n©©i)╚▌░³└©ĪȱTŲõė╣╬─╝»ĪĘĪóĪȱTŲõė╣įu(p©¬ng)┼·╝»ĪĘ║═ĪȱTŲõė╣▌ŗąŻ╝»ĪĘ╚²┤¾▓┐ĘųĪŻį┌×ķģ▓ĖÕ╦∙ū½┐éą“ųąŻ¼±TŲõė╣Ž╚╔·ė├║▄┤¾Ų¬Ę∙╗žŅÖ┴╦┼c╝tīW(xu©”)öĄ(sh©┤)╩«─ĻĄ─▓╗ĮŌų«ŠēĪŻ
ĪĪĪĪ╗žæøŲ蹊┐ĪČ╝tśŪē¶(m©©ng)ĪĘĄ─▀^(gu©░)│╠Ż¼±TŽ╚╔·šf(shu©Ł)Ż¼į┌╔Ž╩└╝o(j©¼)50─Ļ┤·Ą─┼·┼ąėßŲĮ▓«Īó║·▀mĄ─▀\(y©┤n)äė(d©░ng)ųąŻ¼╦¹ęčĮø(j©®ng)šJ(r©©n)šµčąūxĪČ╝tśŪē¶(m©©ng)ĪĘ┴╦ĪŻĪ░╬─Ė’Ī▒Ģr(sh©¬)Ż¼±TŲõė╣įŌĄĮ┼·┼ąŻ¼╦¹ńŖÉ█(©żi)Ą─ĪČ╝tśŪē¶(m©©ng)ĪĘę▓▒╗│Ł╝ę│Łū▀┴╦Ż¼▀Ć«ö(d©Īng)ū„³S╔½Ģ°(sh©▒)╝«╣½ķ_(k©Īi)š╣ė[Ż¼╦¹ō·(d©Īn)æn▀@▓┐Š▐ų°īóįŌų┬ܦ£ńŻ¼ė┌╩Ū═ą╚╦Å─łDĢ°(sh©▒)^ĮĶ│÷ę╗▓┐ė░ėĪĖ²│Į▒ŠĪČ╩»Ņ^ėøĪĘŻ¼ę└įŁų°ąą┐Ņųņ─½ā╔╔½│Łīæ(xi©¦)ĪŻ─ŪĢr(sh©¬)╦¹░ū╠ņ░ż┼·ČĘŻ¼╔Ņę╣├ž├▄│Łīæ(xi©¦)Ż¼š¹š¹│Ł┴╦ę╗─ĻŻ¼ąĪ┐¼└Ū║┴╣P│Łē─┴╦ę╗┤¾ČčŻ¼ģs╩╣╦¹ī”(du©¼)ĪČ╝tśŪē¶(m©©ng)ĪĘėą┴╦Ė³╔ŅĄ─└ĒĮŌĪŻ│Ł═Ļų«╚šŻ¼╦¹öS╣P┼Ū╗▓Ż¼░┘ĖąĮ╗╝»Ż¼ę„│╔ąĪįŖ(sh©®)ę╗╩ūŻ║Ī░ĪČ╝tśŪĪĘ│Ł┴TėĻĮzĮzŻ¼š²╩Ū┤║Üw╗©┬õĢr(sh©¬)ĪŻŪ¦╣┼╬─š┬ČÓč¬£IŻ¼é¹ą─ūŅ┤╦öÓ─c▐oĪŻĪ▒
ĪĪĪĪ▀@▓┐šõ┘FĄ─╩ų│ŁĖÕŻ¼ę▓īóį┌±TŲõė╣īW(xu©”)ąg(sh©┤)^┼c╩└╚╦ęŖ(ji©żn)├µĪŻ
ĪĪĪĪ1975─ĻŻ¼±TŲõė╣▒╗ĮĶš{(di©żo)ĄĮ╬─╗»▓┐ĪČ╝tśŪē¶(m©©ng)ĪĘąŻėåĮMŻ¼ō·(d©Īn)╚╬ĪČ╝tśŪē¶(m©©ng)ĪĘąŻėåĮMĄ─Ė▒ĮMķL(zh©Żng)Ż¼žō(f©┤)ž¤(z©”)ŅI(l©½ng)ī¦(d©Żo)ąŻūó╣żū„Ż¼Å──ŪĢr(sh©¬)ŲŻ¼╦¹š²╩Į═Č╚ļĪČ╝tśŪē¶(m©©ng)ĪĘĄ─蹊┐Ż¼ę╗ĖŃŠ═╩Ū40─ĻĪŻ╦Ń╔Ž50─Ļ┤·Ą─Ę║ūxŻ¼60─Ļ┤·Ą─│Łīæ(xi©¦)Ż¼±TŲõė╣┼cĪČ╝tśŪē¶(m©©ng)ĪĘĮY(ji©”)ŠēŻ¼╚ńĮ±ęčīóĮ³ę╗éĆ(g©©)╝ūūėĪŻ
ĪĪĪĪ±TŽ╚╔·čąŠ┐ĪČ╝tśŪē¶(m©©ng)ĪĘ╩ŪÅ─蹊┐▓▄č®Ū█╝ę╩└╚ļ╩ųŻ¼╦¹łį(ji©Īn)│ų╬─½I(xi©żn)蹊┐┼cĄž├µš{(di©żo)▓ķĪ󥞎┬░l(f©Ī)Š“ŽÓĮY(ji©”)║ŽĄ─蹊┐ĘĮĘ©Ż¼Č°▓▄č®Ū█Ą─╝ę╩└į┌▀@╚²ĘĮ├µČ╝ėąžSĖ╗Č°┐╔ą┼Ą─Ą┌ę╗╩ų╩Ę┴ŽŻ¼╠žäe╩Ū╦¹░l(f©Ī)¼F(xi©żn)┴╦ĪČ╬Õæc╠├ųžą▐▀|¢|▓▄╩Žū┌ūVĪĘŻ¼ī”(du©¼)╦³▀M(j©¼n)ąą┴╦ķL(zh©Żng)Ģr(sh©¬)ķgš{(di©żo)▓ķ║═┐╝ūCŻ¼šęĄĮ┴╦┤¾┼·ėąĻP(gu©Īn)▓▄╝ęĄ─įńŲ┌ą┼╩ĘŻ¼Å─Č°ī”(du©¼)▓▄č®Ū█Ą─ūµ╝«Ą├│÷┴╦┤_ĶŤo(w©▓)ę╔Ą─ĮY(ji©”)šōĪ¬Ī¬▀|īÄĄ─▀|Ļ¢(y©óng)ĪŻ±TŽ╚╔·×ķ▀@ę╗░l(f©Ī)¼F(xi©żn)╦∙īæ(xi©¦)Ą─ĪČ▓▄č®Ū█╝ę╩└ą┬┐╝ĪĘŻ¼ų┴Į±ęčį÷ėå┴╦╦─░µĪŻ
ĪĪĪĪĪ░ąŻūóĪČ╝tśŪē¶(m©©ng)ĪĘ║▄▓╗╚▌ęūŻ¼ę“?y©żn)ķįńŲ┌│Ł▒Š║▄ČÓŻ¼ęį──éĆ(g©©)▒Šūė×ķĄū▒Š│╔┴╦ūŅ┤¾Ą─å¢(w©©n)Ņ}Ī▒Ż¼±TŽ╚╔·╗žæøŻ¼«ö(d©Īng)Ģr(sh©¬)╦¹ų„Åłė├Ė²│Į▒ŠŻ¼Ą½Ųõ╦¹╚╦▓╗═¼ęŌŻ¼ė┌╩Ū×ķ┴╦ūC├„Ė²│Į▒ŠĄ─┐╔┐┐ąįŻ¼╦¹š╣ķ_(k©Īi)┴╦ī”(du©¼)ĪČ╩»Ņ^ėøĪĘ│Ł▒ŠĄ─蹊┐ĪŻ
ĪĪĪĪį┌ī”(du©¼)įńŲ┌│Ł▒ŠĄ─蹊┐ųąŻ¼ūŅ┴Ņ╦¹┼dŖ^Ą─╩Ū╔Ž╩└╝o(j©¼)70─Ļ┤·Ż¼╦¹┼cģŪČ„įŻŽ╚╔·ę╗Ų░l(f©Ī)¼F(xi©żn)┴╦╝║├«▒Š▒▄Ī░ŽķĪ▒ĪóĪ░ĢįĪ▒ā╔ūųĄ─ųMŻ¼Å─Č°┐╝│÷┴╦╦³╩ŪŌ∙ėH═§į╩Žķ║═║ļĢį╝ęĄ─│Ł▒ŠĪŻ▀@ę╗ĮY(ji©”)šōŻ¼╩ŪėąĪČŌ∙ėH═§Ė«▓žĢ°(sh©▒)Ģ°(sh©▒)─┐ĪĘįŁ╝■╔Ž═¼śėĄ─▒▄ųMüĒ(l©ói)┤_ūCĄ─Ż¼Č°▀@▓┐š┤ėąā╔┤·Ō∙ėH═§╩ųØ╔Ą─ĪČŌ∙Ė«Ģ°(sh©▒)─┐ĪĘ╔ŽŻ¼▀Ćėą§r╝tĄ─Ī░Ō∙ėH═§īÜĪ▒ĪóĪ░įG²Sšõ┘pĪ▒Ą╚ėĪš┬Ż¼Ė³╩Ū▓╗┐╔äė(d©░ng)ōuĄ─┤_ūCĪŻ═¼Ģr(sh©¬)Ż¼▀@ę╗┤_ūCę▓ķgĮėūC├„┴╦╝║├«▒Š┴¶Ž┬┴╦▓▄č®Ū█ĪČ╩»Ņ^ėøĪĘįŁ▒ŠĄ─┐Ņ╩ĮŻ¼┤¾┤¾į÷╝ė┴╦╝║├«▒ŠĪČ╩»Ņ^ėøĪĘĄ─šõ┘FąįĪŻ
ĪĪĪĪę“┤╦Ż¼╝║├«▒Š╩ŪŌ∙Ė«│Ł▒ŠĄ─░l(f©Ī)¼F(xi©żn)Ż¼Įęķ_(k©Īi)┴╦ĪČ╝tśŪē¶(m©©ng)ĪĘ│Ł▒ŠčąŠ┐╔ŽŹõą┬Ą─ę╗Ēō(y©©)Ż¼ķ_(k©Īi)äō(chu©żng)┴╦ĪČ╝tśŪē¶(m©©ng)ĪĘ│Ł▒ŠčąŠ┐Ą─ę╗éĆ(g©©)ą┬╠ņĄžĪóą┬┬ĘÅĮĪŻ
ĪĪĪĪļS║¾Ż¼±TŲõė╣Ž╚╔·į┌ūą╝Ü(x©¼)蹊┐Ė²│Į▒ŠĪČ╩»Ņ^ėøĪĘĢr(sh©¬)Ż¼ėųėą┴╦ęŌ═Ō░l(f©Ī)¼F(xi©żn)Ż¼▀@Š═╩Ū░l(f©Ī)¼F(xi©żn)┴╦Ė²│Į▒Š╩Ūšš╝║├«▒Š│ŁĄ─ĪŻĪ░Ė²│Į▒ŠĄ─ąą┐ŅĄ╚Ą╚Č╝┼c╝║├«▒Šę╗─Żę╗śėŻ¼▀B╝║├«▒ŠĄ─┐šąąĪóč▄╬─ĪóÕe(cu©░)äeūųĄ╚Ż¼Ė²│Į▒ŠČ╝┼cų«ŽÓ═¼ĪŻį┌Ų▀╩«░╦╗žŻ¼▀Ć┴¶Ž┬┴╦ę╗éĆ(g©©)▒▄ųMĄ─Ī«ŽķĪ»ūųŻ¼┼c╝║├«▒ŠĄ─▒▄ųMę╗─Żę╗śėĪŻĪ▒±TŽ╚╔·šZ(y©│)ÜŌųąļyč┌▀@ę╗░l(f©Ī)¼F(xi©żn)ĦĮo╦¹Ą─┼dŖ^ĪŻė╔ė┌Ė²│Į▒ŠĄ─┐Ņ╩Į┼c╝║├«▒Š═Ļ╚½ę╗śėŻ¼╦∙ęį╝║├«▒ŠüG╩¦Ą─▓┐ĘųŻ¼┐╔ęįÅ─Ė²│Į▒Š┐┤ĄĮ╦³Ą─įŁśėŻ¼▀@śėŻ¼╝║ĪóĖ²ā╔▒Š▒Ń│╔×ķĪČ╝tśŪē¶(m©©ng)ĪĘįńŲ┌│Ł▒ŠĄ─ę╗ī”(du©¼)╣░ĶĄŻ¼Å─▀@ā╔éĆ(g©©)│Ł▒ŠŻ¼─▄ę└ŽĪ┐┤ĄĮ▓▄č®Ū█«ö(d©Īng)─ĻįŁĖÕĄ─śėūėŻ¼▀@ę▓╩ŪĪČ╩»Ņ^ėøĪĘ│Ł▒ŠčąŠ┐╩Ę╔ŽŠ▀ėą╠ž╩ŌęŌ┴xĄ─╩┬╝■ĪŻ
ĪĪĪĪ1977─Ļ6į┬Ż¼±TŽ╚╔·īó▀@ę╗蹊┐│╔╣¹īæ(xi©¦)│╔ĪČšōĖ²│Į▒ŠĪĘŻ¼į┌Ģ°(sh©▒)ųą╦¹┐éĮY(ji©”)ąįĄžīæ(xi©¦)Ą└Ż║Ī░īŹ(sh©¬)█`╩ŪÖz“×(y©żn)šµ└ĒĄ─╬©ę╗ś╦(bi©Īo)£╩(zh©│n)Ż¼│²┤╦ų«═ŌŻ¼▓╗─▄ėąĄ┌Č■éĆ(g©©)ś╦(bi©Īo)£╩(zh©│n)Ī▒ĪŻŪ╔Ą─╩ŪŻ¼▀@Ę¼įÆŪĪ║├╩Ūīæ(xi©¦)į┌1978─ĻĄ─Ī░šµ└Ēś╦(bi©Īo)£╩(zh©│n)┤¾ėæšōĪ▒Ą─Ū░ę╗─ĻŻ¼┼cųąčļ╠ß│÷Ą─Ī░īŹ(sh©¬)█`╩ŪÖz“×(y©żn)šµ└ĒĄ─╬©ę╗ś╦(bi©Īo)£╩(zh©│n)Ī▒═Ļ╚½╬Ū║ŽĪŻę“┤╦ĪČšōĖ²│Į▒ŠĪĘĄ─ęŌ┴x▓╗āH╩Ū░µ▒ŠčąŠ┐Ą─ęŌ┴xŻ¼Ė³Š▀ėą╦╝Žļ╔ŽĄ─ęŌ┴xĪŻ
ĪĪĪĪĪČšōĖ²│Į▒ŠĪĘīæ(xi©¦)║├║¾Ż¼▒╗ŽŃĖ█ĪČ┤¾╣½ł¾(b©żo)ĪĘ▀B▌d2éĆ(g©©)į┬Ż¼ę²Ų║Żā╚(n©©i)═Ō╝tīW(xu©”)ĮńśO┤¾Ę┤ĒæĪŻė╔┤╦Ż¼▀^(gu©░)╚ź▓ó▓╗▒╗ųžęĢĄ─Ė²│Į▒Š▒╗ÅVĘ║šJ(r©©n)┐╔Ż¼▓ó▒╗┤_Č©×ķąŻūóĪČ╝tśŪē¶(m©©ng)ĪĘĄ─Ąū▒ŠŻ¼ąŻūóĪČ╝tśŪē¶(m©©ng)ĪĘĄ─╣żū„Ą├ęįĒś└¹▀M(j©¼n)ąąĪŻ
ĪĪĪĪį┌ĪČ╣Ž’łśŪģ▓ĖÕĪĘųąŻ¼±TŽ╚╔·▀Ćīóūį╝║ī”(du©¼)╝ūąń▒ŠĄ─蹊┐Č©├¹×ķĪČ╣Ž’łśŪ╩ų┼·╝ūąń▒Š<╩»Ņ^ėø>ĪĘŻ¼ī”(du©¼)╝║├«▒Š║═Ė²│Į▒Šę▓Č╝ū÷┴╦╩ų┼·Ż¼▓óį┌ĪČ╣Ž’łśŪģ▓ĖÕĪĘųąė░ėĪ│÷░µŻ¼īóī”(du©¼)ČĒ▓ž▒ŠĪó╝ū│Į▒ŠĪó│╠╝ū▒ŠĄ╚Ą─蹊┐│╔╣¹╩š╚ļĪČ╩■╩»╝»ĪĘĪŻ
ĪĪĪĪ│²┤╦ų«═ŌŻ¼±T└Ž▀Ćū÷┴╦ę╗ĒŚ(xi©żng)╩ʤo(w©▓)Ū░└²Ą─Š▐┤¾╣ż│╠Ī¬Ī¬┼c╝Šų╔▄SŽ╚╔·║Žū„Ż¼ÜvĢr(sh©¬)╩«ėÓ─ĻŻ¼░čęč░l(f©Ī)¼F(xi©żn)Ą─ČÓ▀_(d©ó)13ĘN░µ▒Šų¼│IJSįu(p©¬ng)▒Š╚½├µĄžģR╝»į┌ę╗ŲŻ¼īóĖ„▒ŠžQąą┼┼┴ąųūųųŠõī”(du©¼)ąŻŻ¼▓óģR╝»╚½▓┐ų¼įu(p©¬ng)(║¼ĘŪų¼įu(p©¬ng)▓┐Ęų)Ż¼ė┌2009─Ļ═Ļ│╔┴╦╣▓ėŗ(j©¼)30ŠĒāį(c©©)Ą─ĪČ<ų¼│IJSųžįu(p©¬ng)╩»Ņ^ėø>ģRąŻģRįu(p©¬ng)ĪĘĪŻĪ░ė├┼┼┴ąĄ─ąŻĘ©Ż¼═¼ę╗Šõūė▀@éĆ(g©©)▒Šūė▀@śėŻ¼─ŪéĆ(g©©)▒Šūė─ŪśėŻ¼į§├┤┬²┬²ūā╗»Ą─Ż¼ųę╗┼┼┴ąĪŻ╦∙ęį─Ńę¬┐┤13ĘNįńŲ┌│Ł▒ŠūųŠõĄ─ūā╗»Ż¼Š═ę╗ŪÕČ■│■┴╦ĪŻĪ▒±TŽ╚╔·Ą└ĪŻ▀@ę╗╗∙ĄA(ch©│)ąį╣żū„Ż¼╩╣īW(xu©”)ąg(sh©┤)Įńėą┴╦ę╗éĆ(g©©)╝tīW(xu©”)蹊┐Ą─┘Y┴ŽīÜÄņ(k©┤)ĪŻ
ĪĪĪĪ┼c┤╦═¼Ģr(sh©¬)Ż¼±TŽ╚╔·╗©┴╦5─ĻĢr(sh©¬)ķgŻ¼╚┌║Ž┴╦▓▄č®Ū█╝ę╩└蹊┐ĪóĪČ╩»Ņ^ėøĪĘ│Ł▒ŠčąŠ┐Īó╝tśŪ╦╝Žļ蹊┐Īó╚╦╬’蹊┐Īó╦ćąg(sh©┤)蹊┐Ą─╚½▓┐│╔╣¹Ż¼▓ó╬³╩šįu(p©¬ng)³c(di©Żn)┼╔Ą─Š½╚A║═Ųõ╦¹╝tīW(xu©”)蹊┐╝ęĄ─│╔╣¹Ż¼īæ(xi©¦)│╔ĪČ╣Ž’łśŪųžąŻįu(p©¬ng)┼·<╝tśŪē¶(m©©ng)>ĪĘŻ¼▀@┐╔ęįšf(shu©Ł)╩Ū±TŽ╚╔·╚½▓┐╝tīW(xu©”)蹊┐Ą─┐éģRŻ¼ę▓╩Ū╦¹40─Ļ蹊┐ĪČ╝tśŪē¶(m©©ng)ĪĘĄ─ą─č¬╦∙Š█ĪŻ
ĪĪĪĪ└ŅŽŻĘ▓Ž╚╔·šf(shu©Ł)Ż║Ī░Å─Ųõė╣╝tīW(xu©”)ų°ū„ųą┐┤│÷Ż¼╦¹╩Ūį┌╬─▒ŠĪó╬─½I(xi©żn)Īó╬─╗»Ą─ŽÓ╗ź╚┌═©ųą═Ļ│╔Ą─Ż¼▀@╩Ū¼F(xi©żn)┤·╝tīW(xu©”)ūŅėąŽĄĮy(t©»ng)Ą─ķ_(k©Īi)═žąįĄ─蹊┐│╔╣¹ĪŻĪ▒
ĪĪĪĪš²Ž±±TŽ╚╔·┘ø(z©©ng)ėč╚╦Ą─ę╗╩ūįŖ(sh©®)Ż║Ī░╝tśŪŖW┴xļ[Ū¦īżŻ¼├Ņ╣P╦čŪ¾ęŌĖ³╔ŅĪŻĄžŽ┬ė¹šł(q©½ng)▓▄ē¶(m©©ng)╚ŅŻ¼ŲĮ╔·┐╔įS╩Ūų¬ę¶ĪŻĪ▒Ī░ŲĮ╔·┐╔įS╩Ūų¬ę¶Ī▒ę╗šZ(y©│)Ż¼ę▓š²╩Ū±TŽ╚╔·āAą─╦─╩«▌dŃ@čąĪČ╝tśŪē¶(m©©ng)ĪĘĄ─Š½╔±īæ(xi©¦)ššĪŻ
ĪĪĪĪīŹ(sh©¬)ūCŪ¾šµŻ¼┐┤▒M²öŲØ╩«╚f(w©żn)ĘÕ
ĪĪĪĪį┌▒ŖČÓĄ─īŹ(sh©¬)Ąž┐╝▓ņųąŻ¼±TŲõė╣Ž╚╔·╩«┤╬▀M(j©¼n)Į«Ą─Įø(j©®ng)Üvįńęčé„×ķ╝čįÆĪŻĪ░ųąć°(gu©«)Ą─╬„ė“Ż¼═Ōć°(gu©«)╚╦į┌100ČÓ─Ļķgū÷┴╦─Ū├┤ČÓ╣żū„ĪŁĪŁĪ▒ć@═’ų«ėÓŻ¼╦¹ŽŻ═¹ė├ūį╝║Ą─ąąäė(d©░ng)Ū¾Ą├Ė³ČÓĄ─░l(f©Ī)¼F(xi©żn)ĪŻ
ĪĪĪĪė╔ĪČ╬„ė╬ėøĪĘČ°ĪČ┤¾┤╚Č„╦┬╚²▓žĘ©Ä¤é„ĪĘČ°ĪČ┤¾╠Ų╬„ė“ėøĪĘŻ¼ą■▐╩╬„╠ņ╚ĪĮø(j©®ng)Ą─ą╬Ž¾į┌╦¹╔┘─ĻĢr(sh©¬)┤·Ą─Ū¾īW(xu©”)Üv│╠ųą│╔×ķ▓╗£ńĄ─├„¤¶Ż¼Č°╦¹║¾üĒ(l©ói)ÕøČ°▓╗╔ߥ─Ŗ^ČĘĮø(j©®ng)ÜvŻ¼ę▓¤o(w©▓)▓╗┤“╔Ž┴╦ą■▐╩Ī░š\(ch©”ng)ųžä┌▌pŻ¼Ū¾╔ŅįĖ▀_(d©ó)Ī▒Ą─Š½╔±ėĪėøĪŻ
ĪĪĪĪ±TŲõė╣Ž╚╔·ū÷īW(xu©”)å¢(w©©n)ųvŠ┐Ī░╚²ĄĮĪ▒Ż║Üv╩Ę╬─½I(xi©żn)Ąõ╝«ĄĮĪ󥞎┬┐╝╣┼░l(f©Ī)Š“╬─╬’ĄĮĪóĄž└ĒīŹ(sh©¬)Ąž┐╝▓ņĄĮĪŻĪ░īŹ(sh©¬)Ąžš{(di©żo)▓ķ║═ūxĢ°(sh©▒)ę╗śėųžę¬ĪŻĪ▒±TŲõė╣Ž╚╔·ę╗ėąÖC(j©®)Ģ■(hu©¼)Š═ĄĮ╚½ć°(gu©«)Ė„Ąžė╬ÜvŻ¼ūįĘQ▀@╩ŪĪ░ūx╠ņĄžķgūŅ┤¾Ą─ę╗▓┐┤¾Ģ°(sh©▒)Ī▒ĪŻ
ĪĪĪĪūį1986─Ļų┴2005─ĻĄ─20─ĻķgŻ¼±TŽ╚╔·ęį╣┼ŽĪų«─ĻĻæ└m(x©┤)═Ļ│╔╩«▀M(j©¼n)ą┬Į«Īó╚²ĄŪ┼┴├ūĀ¢Ė▀įŁĪóā╔┤╬┤®įĮ╦■┐╦└Ł¼öĖ╔┤¾╔│─«Ą╚ēč┼eŻ¼īŹ(sh©¬)Ąž╠ż┐┤┴╦ą■▐╩╚ĪĮø(j©®ng)į┌ųąć°(gu©«)Š│ā╚(n©©i)╬„ąą║═¢|ÜwĄ─╚½▓┐┬ĘŠĆŻ¼┼─┴╦Į³╚f(w©żn)Ę∙ššŲ¼ĪŻ
ĪĪĪĪ╦¹į°ėąįŖ(sh©®)įŲŻ║Ī░┐┤▒M²öŲØ╩«╚f(w©żn)ĘÕŻ¼╩╝ų¬╬Õį└ę▓ŲĮė╣ĪŻ╦¹─Ļė¹ū„ąņŽ╝┐═Ż¼ū▀▒ķ╠ņ╬„į┘Ž“¢|ĪŻĪ▒1998─Ļ8į┬Ż¼±TŲõė╣Ž╚╔·Ą┌Ų▀┤╬ĄĮą┬Į«Ż¼į┘╔Ž┼┴├ūĀ¢Ė▀įŁŻ¼ė┌║Ż░╬4700├ūĄ─├„ĶF╔w╔Į┐┌Ż¼šęĄĮ┴╦ą■▐╩╚ĪĮø(j©®ng)╗žć°(gu©«)Ą─╔Į┐┌╣┼Ą└Ż¼┤╦╣┼Ą└×ķą■▐╩¢|Üw║¾1355─ĻüĒ(l©ói)Ą┌ę╗┤╬▒╗░l(f©Ī)¼F(xi©żn)ĪŻ▀@ę╗░l(f©Ī)¼F(xi©żn)Ż¼▐Zäė(d©░ng)┴╦ųą═ŌīW(xu©”)ąg(sh©┤)ĮńŻ¼┤µę╔┴╦1000ČÓ─ĻĄ─å¢(w©©n)Ņ}╗Ē╚╗ķ_(k©Īi)└╩ĪŻ
ĪĪĪĪšäŲŲDą┴Ą─Ė▀įŁ╔│─«ų«┬├Ż¼±TŽ╚╔·Ą└Ż║Ī░ī”(du©¼)╬ęüĒ(l©ói)šf(shu©Ł)Ż¼śĘ(l©©)┤¾ė┌┐ÓĪŻ╬ęĄ─ė╬Üv╩Ū║═īW(xu©”)ąg(sh©┤)š{(di©żo)▓ķ┬ō(li©ón)ŽĄį┌ę╗ŲĄ─Ż¼├┐ėą╩š½@Ż¼─ŪĘNŽ▓Éé▓╗┐╔├¹ĀŅŻ¼ūŃęįĄųŽ¹ę╗ŪąĖČ│÷ŻĪĪ▒
ĪĪĪĪ2005─Ļ8į┬15╚šŻ¼±TŲõė╣Ž╚╔·ęį83ÜqĖ▀²gĄ┌╚²┤╬╔Ž┼┴├ūĀ¢Ė▀įŁŻ¼×ķą■▐╩┴ó¢|Üw▒«ėøĪŻ▀@ę╗─Ļ9į┬26╚šŻ¼╦¹ė╔├ū╠m▀M(j©¼n)╚ļ┴_▓╝▓┤Ż¼ĄĮ▀_(d©ó)śŪ╠mŻ¼ėųĮø(j©®ng)²ł│ŪĪó░ū²łČčĪó╚²ē┼╔│Ż¼╚ļė±ķT(m©”n)ĻP(gu©Īn)ĄĮČž╗═Ż¼į┌┤¾╔│─«╦└═÷ų«║Ż└’═Ż┴¶17╠ņŻ¼ĮKė┌┤_ūC┴╦ą■▐╩╚ĪĮø(j©®ng)¢|ÜwĄ─ūŅ║¾┬ĘČ╬ĪŻ
ĪĪĪĪ±TŲõė╣Ž╚╔·▀Ćė├ńRŅ^║═«ŗ(hu©ż)╣Pėøõø┴╦ūį╝║ī”(du©¼)╬„ė“Ą─ŪķĖąĪŻį┌╦¹Ą─özė░╝»ĪČÕ½║ŻĮ┘ēmĪĘųąŻ¼ĮzŠIų«┬Ęš╣╩Š│÷ČÓį¬Ą─╬─╗»ęŌ╠N(y©┤n)Ż¼├±ūÕĄ─’L(f©źng)ŪķŻ¼Üv╩ĘĄ─ÅUąµŻ¼ūį╚╗Ą─’L(f©źng)╣ŌŻ¼ū┌Į╠Ą─╦ćąg(sh©┤)Ż¼į┌▀b▀h(yu©Żn)Ą─Üqį┬┼c┬├═Šųą»B╝ėŻ╗į┌└L«ŗ(hu©ż)ū„ŲĘ└’Ż¼±TŽ╚╔·į┌ēč├└Ą─╔Į┤©ųą╚ĪĖÕŻ¼¬Ü(d©▓)äō(chu©żng)┴╦ųž▓╩╬„▓┐╔Į╦«Ż¼ęįĪČĮ╦■╦┬ĪĘĪóĪČ╚ĪĮø(j©®ng)ų«┬ĘĪĘĪóĪČŲŅ▀BŪ’╔½ĪĘĪóĪČ╣┼²öŲØć°(gu©«)╔Į╦«ĪĘĄ╚×ķ┤·▒ĒŻ¼░▀ö╠▌x╗═Ż¼│┴ų°║±ųžŻ¼ūī╚╦Ėą╩▄ĄĮ╬„▓┐╔Į╦«Ą─š║│ų«├└Ż¼ŚŅ╚╩ÉŽ╚╔·įu(p©¬ng)ār(ji©ż)Ż║Ī░ĄĮ╚╦ų«╦∙╬┤ĄĮŻ¼ęŖ(ji©żn)╚╦ų«╦∙╬┤ęŖ(ji©żn)Ż¼Ųõąžųą▓žėą╠ņŽ┬Ųµ╔Į«É╦«Ż¼╣╩ę╗░l(f©Ī)Č°▓╗┐╔╩šę▓ĪŻĪ▒
ĪĪĪĪ2005─ĻŻ¼ųąć°(gu©«)╚╦├±┤¾īW(xu©”)ć°(gu©«)īW(xu©”)į║│╔┴óŻ¼±TŲõė╣Ž╚╔·╩▄Ģr(sh©¬)╚╬ąŻķL(zh©Żng)╝o(j©¼)īÜ│╔┴”č¹│÷╚╬ą┬ųąć°(gu©«)Ą┌ę╗╦∙ć°(gu©«)īW(xu©”)į║Ą┌ę╗╚╬į║ķL(zh©Żng)ĪŻ9į┬Ž┬č«Ż¼ć°(gu©«)īW(xu©”)į║ķ_(k©Īi)īW(xu©”)ų«ļHŻ¼ę╗Ę▌╩ų°╝Š┴w┴ų║═±TŲõė╣├¹ūųĄ─ł¾(b©żo)Ėµ▀fĮ╗ĄĮ³hųąčļŻ¼╠ß│÷Ī░Į©┴óĪ«╬„ė“Üv╩ĘšZ(y©│)čį蹊┐╦∙Ī»Ż¼Å─╩┬ųąć°(gu©«)╬„▓┐╬─╗»Üv╩ĘšZ(y©│)čį├±╦ū╦ćąg(sh©┤)ĘĮ├µĄ─蹊┐Ż¼Ųõųą╠žäe╩Ū╬„ė“ųą╣┼Ģr(sh©¬)Ų┌Ą─ČÓĘNšZ(y©│)čįŻ¼╝▒ąĶ┼ÓB(y©Żng)╚╦▓┼└^│ąŽ┬╚źŻ¼ęįæ¬(y©®ng)ć°(gu©«)╝ęīóüĒ(l©ói)▓╗Ģr(sh©¬)ų«ąĶĪ▒ĪŻ
ĪĪĪĪł¾(b©żo)Ėµ╔Ž╚ź▓╗ĄĮ10╠ņŻ¼«ö(d©Īng)Ģr(sh©¬)▀Ćį┌ą┬Į«┐╝▓ņ═ŠųąĄ─±TŽ╚╔·Ż¼į┌┴_▓╝▓┤Ą─ĀI(y©¬ng)Äż└’Ą├ĄĮ▒▒Š®Ž¹ŽóŻ¼ųąčļŅI(l©½ng)ī¦(d©Żo)ī”(du©¼)ł¾(b©żo)Ėµū„│÷┴╦┼·╩ŠŻ¼ę¬Ū¾Į╠ė²▓┐║═žö(c©ói)š■▓┐┤¾┴”ų¦│ųĪŻ±TŽ╚╔·¤o(w©▓)▒╚Ė▀┼dŻ¼╗žŠ®║¾Š═ų°╩ųīó╦¹Ą─Ī░┤¾ć°(gu©«)īW(xu©”)Ī▒įO(sh©©)ŽļęÄ(gu©®)äØ│÷üĒ(l©ói)Ż¼īó╬„ė“?q©▒)W╝{╚ļć°(gu©«)īW(xu©”)蹊┐ĘČ«ĀĪŻ
ĪĪĪĪ╬„ė“Üv╩ĘšZ(y©│)čį蹊┐╦∙ķ_(k©Īi)äō(chu©żng)ų«╩╝Ż¼±TŽ╚╔·Å─Ą┬ć°(gu©«)šł(q©½ng)╗ž┴╦╬„ė“?q©▒)Ż╝ę╔“ąl(w©©i)śsŽ╚╔·Ż¼Å─ą┬Į«šł(q©½ng)üĒ(l©ói)┴╦╬„ė“┐╝╣┼īŻ╝ę═§▒■╚AŽ╚╔·Ż¼Č°Ūę▀ĆĻæ└m(x©┤)ę²▀M(j©¼n)┴╦ę╗┼·╚╦▓┼Ż¼▓ó┼╔╚╦ĄĮ║Ż═ŌīW(xu©”)┴Ģ(x©¬)Ż¼─┐Ū░ęčĮø(j©®ng)ėą─▄ē“╠Ä└Ē╣┼▓ž╬─Īó├╔╬─ĪóĶ¾╬─Īó═┬╗┴_╬─Īó╦┌╠ž╬─Ą╚ĘĮ├µĄ─╚╦▓┼Ż¼┐╔ęį░č╬šė┌ĻD╬─Īó╗ž·X╬─Īóöó└¹üå╬─Īóųą╣┼▓©╦╣╬─Ą╚ČÓĘNšZ(y©│)čį╬─½I(xi©żn)▓─┴ŽŻ¼ę╗éĆ(g©©)╬„ė“Üv╩ĘšZ(y©│)čį蹊┐Ą─ą┬╠ņĄžŻ¼ęčĮø(j©®ng)┬²┬²š╣ķ_(k©Īi)ĪŻ
ĪĪĪĪ±TŽ╚╔·į°šf(shu©Ł)Ż║Ī░ėĶ╔┘ūxą■▐╩ʩĤ鄯¼╦ņč÷ų«×ķĤŻ¼ļm╚f(w©żn)Į┘Č°▓╗£ńŪ¾īW(xu©”)Ū¾šµų«ą─ę▓ĪŻĪ▒▀@śėĄ─×ķīW(xu©”)┼c×ķ╚╦└Ē─ŅŻ¼╦¹ę╗╔·łį(ji©Īn)│ų█`ąąĪŻÅ─Ž╚╔·Ą─īW(xu©”)ąg(sh©┤)蹊┐│╔╣¹ųąŻ¼┐╔ęį┐┤ĄĮą■▐╩Š½╔±į┌Į±╠ņĄ─Å═(f©┤)┼dĪŻ
ĪĪĪĪī”(du©¼)įÆ?c©Żi)TŲõė╣
ĪĪĪĪĻP(gu©Īn)ė┌ĪČ╝tśŪē¶(m©©ng)ĪĘ ╝╚▓╗─▄ļSęŌüy▓┬Ż¼ę▓▓╗─▄▓╗╚źŪ¾ūC
ĪĪĪĪėøš▀Ż║─·į┌ĪČ╣Ž’łśŪģ▓ĖÕĪĘ┐éą“└’╠ߥĮŻ¼ĪČ╝tśŪē¶(m©©ng)ĪĘ╩Ūę╗éĆ(g©©)ū÷▓╗═ĻĄ─Ņ}─┐Ż¼ėą▓╗╔┘å¢(w©©n)Ņ}▀Ć┤µį┌─·Ą─ą─└’Ż¼ø](m©”i)ėąīæ(xi©¦)ĄĮ╝ł╔ŽĪŻī”(du©¼)ė┌ĪČ╝tśŪē¶(m©©ng)ĪĘ─·ūŅĮ³ėųėą──ą®ą┬Ą─╦╝┐╝Ż┐
ĪĪĪĪ±TŲõė╣Ż║╬ęī”(du©¼)ĪČ╝tśŪē¶(m©©ng)ĪĘĄ─šJ(r©©n)ūR(sh©¬)įĮüĒ(l©ói)įĮ╔ŅŻ¼Č╝╩ŪĖ·▓▄č®Ū█Ą─╝ę╩└ėąĻP(gu©Īn)Ż¼ĪČ╝tśŪē¶(m©©ng)ĪĘ└’▒Ż┴¶Ą─▓▄č®Ū█╝ęļ[ļ[╝s╝sĄ─ę╗ą®╩┬īŹ(sh©¬)Ż¼ū„š▀Č╝ø](m©”i)ėą├„šf(shu©Ł)ĪŻ▒╚╚ńį¬Õ·╩ĪėHŻ¼×§▀M(j©¼n)ąóī”(du©¼)┘Zšõšf(shu©Ł)Ż║Ī░─ŪĖ«└’╚ńĮ±ļm╠Ē┴╦╩┬Ż¼ėą╚źėąüĒ(l©ói)Ż¼─’─’║═╚f(w©żn)ÜqĀöžM▓╗┘pĄ─Ż┐Ī▒┐╔╩Ū┘Zšõģsšf(shu©Ł)Ż║Ī░į┘ā╔─ĻŻ¼į┘╩Īę╗╗žėHŻ¼ų╗┼┬Š═Š½ĖF┴╦ĪŻĪ▒ų¼│IJS┼·šZ(y©│)Ī░ĮĶ╩ĪėH╩┬īæ(xi©¦)─Žč▓Ī▒Ż¼į¬Õ·╩ĪėHĄ─║└╚Ał÷(ch©Żng)├µŻ¼Š═╩Ūė░╔õ┐Ą╬§─Žč▓Ą─ł÷(ch©Żng)├µŻ¼┐Ą╬§┴∙┤╬─Žč▓Ż¼4┤╬ūĪį┌▓▄╝ęŻ¼▓▄╝ę╗©ÕX(qi©ón)╚ń┴„╦«Ż¼ū„š▀▀ĆĮĶ┌wŗ▀ŗ▀ų«┐┌šf(shu©Ł)Ż║Ī░ę▓▓╗▀^(gu©░)╩Ū─├ų°╗╩Ą█╝ęĄ─Ńyūė═∙╗╩Ą█╔Ē╔Ž╩╣┴T┴╦ŻĪĪ▒▀@ą®ĄžĘĮ▓▄č®Ū█Č╝╩ŪįÆ└’ėąįÆŻ¼é╚(c©©)├µųv▓▄╝ęĄ─ŲŲöĪĪŻ
ĪĪĪĪĪČ╝tśŪē¶(m©©ng)ĪĘĄ─▒Ē¼F(xi©żn)╩ųĘ©▓╗Ž±ę╗░ŃąĪšf(shu©Ł)Č╝╩Ūų▒░ūĄ─Ż¼ĪČ╝tśŪē¶(m©©ng)ĪĘėąūų├µ╔ŽĄ─ę╗īėęŌ╦╝Ż¼▀Ćėąļ[į┌║¾├µĄ─ę╗īėø](m©”i)═Ļ╚½ųv│÷üĒ(l©ói)Ą─ęŌ╦╝ĪŻĄ½╩ŪŻ¼ę▓▓╗─▄Ė∙ō■(j©┤)▀@éĆ(g©©)ĄĮ╠Ä╚źū┴─źŻ¼║├Ž±ØMŲ¬ĄĮ╠Ä▒│║¾Č╝ėąļ[▓žŻ¼ū„╝ęų╗╩Ūį┌▀m«ö(d©Īng)?sh©┤)─ĄžĘĮ═Ė┬Čā╔ŠõŻ¼ø](m©”i)ėąų¼│IJSĄ─┼·Ż¼▓╗┴╦ĮŌ▓▄╝ęöĪ┬õĄ─▀^(gu©░)│╠Ż¼Š═¾wĢ■(hu©¼)▓╗│÷įÆ└’ėąįÆĪŻ╦∙ęįę¬ĮY(ji©”)║Ž╦¹Ą─Üv╩Ę▒│Š░Īó╝ę═ź▒│Š░Ż¼─Ń▓┼─▄¾w╬“│÷üĒ(l©ói)ĪŻĪČ╝tśŪē¶(m©©ng)ĪĘ╩ŪéĆ(g©©)ū÷▓╗═ĻĄ─Ņ}─┐Ż¼ĻP(gu©Īn)ė┌▓▄╝ęĄ─öĪ┬õĪó└ŅņŃ╝ęĄ─öĪ┬õĄ╚Ą╚Ż¼ėą▓╗╔┘å¢(w©©n)Ņ}▀Ć┤µį┌╬ęĄ─ą─└’Ż¼╬ę▀ĆŽŻ═¹ėąĢr(sh©¬)ķg║═Š½┴”üĒ(l©ói)└^└m(x©┤)▀@ĘĮ├µĄ─╠Į╦„ĪŻ
ĪĪĪĪėøš▀Ż║ĪČ╝tśŪē¶(m©©ng)ĪĘ└’║▄ČÓ▓╗├„┤_Ą─¢|╬„ų┴Į±¤o(w©▓)Č©šōŻ¼ę²│÷Ė„ĘN▓┬£y(c©©)Ż¼ć·└@ų°╦³Ą─ĀÄ(zh©źng)šō╩ŪʱĢ■(hu©¼)ę╗ų▒┤µį┌Ž┬╚źŻ┐
ĪĪĪĪ±TŲõė╣Ż║ĪČ╝tśŪē¶(m©©ng)ĪĘ╠½╔Ņ┴╦Ż¼╝╚▓╗─▄ļSęŌüy▓┬Ż¼ę▓▓╗─▄▓╗╚źŪ¾ūCĪŻīW(xu©”)ąg(sh©┤)蹊┐Ż¼ė╚ŲõĪČ╝tśŪē¶(m©©ng)ĪĘŻ¼Ä¦ėą╠ž╩Ōąį┘|(zh©¼)Ż¼¼F(xi©żn)į┌ļSęŌüyšf(shu©Ł)│╔┴╦Ųš▒ķĄ─¼F(xi©żn)Ž¾┴╦Ż¼▓┬£y(c©©)Ą─╚╦įĖęŌ▀@├┤▓┬Īó─Ū├┤▓┬Ż¼╬─╗»╦«ŲĮĄ═ę╗ą®Ą─╚╦╚▌ęū▒╗▀@ĘNĄ═╝ē(j©¬)╚ż╬Čū¾ėęŻ¼Č°▓╗╚ź╔Ņę╗īė┐╝æ]š■ų╬ĪóÜv╩ĘĪó╦╝ŽļĄ─▒│Š░ĪŻ╝tīW(xu©”)╩ŪīW(xu©”)å¢(w©©n)Ż¼ø](m©”i)ėąĖ∙ō■(j©┤)Ą─ļSęŌ═Ų£y(c©©)╩Ū▓╗ąąĄ─Ż¼ī”(du©¼)ūxš▀꬞ō(f©┤)ž¤(z©”)ĪŻ
ĪĪĪĪĻP(gu©Īn)ė┌╬„ė“蹊┐ ▓╗āH╩ŪĖ─╔ŲŻ¼▀Ćėą┴╦ķL(zh©Żng)ūŃĄ─▀M(j©¼n)š╣
ĪĪĪĪėøš▀Ż║─·į°╠ߥĮĻP(gu©Īn)ė┌╬„ė“Ą─蹊┐Ż¼100ČÓ─Ļķg╬„ĘĮīW(xu©”)š▀ę╗ų▒ŅI(l©½ng)Ž╚ė┌ųąć°(gu©«)īW(xu©”)š▀Ż¼Ī░╬„ė“Üv╩ĘšZ(y©│)čį蹊┐╦∙Ī▒│╔┴ó6─ĻüĒ(l©ói)Ż¼╬„▓┐Üv╩ĘĪóšZ(y©│)čįĄ─蹊┐╩ŪʱĄ├ĄĮ┴╦Ė─╔ŲŻ┐
ĪĪĪĪ±TŲõė╣Ż║▓╗āH╩ŪĖ─╔ŲŻ¼▀Ćėą┴╦ķL(zh©Żng)ūŃĄ─▀M(j©¼n)š╣ĪŻ100ČÓ─ĻŪ░▒╗ć°(gu©«)═Ō┼¬ū▀Ą─╬─½I(xi©żn)Č╝ęčĮø(j©®ng)╣½ųTė┌╩└Ż¼░³└©╬„ĘĮīW(xu©”)š▀Īóć°(gu©«)ā╚(n©©i)īW(xu©”)š▀Č╝▀M(j©¼n)ąą┴╦蹊┐Ż¼▀@ą®Č╝╩Ū└ŽĄ─┘Y┴ŽĪŻĮŌĘ┼ęį║¾Ż¼╬„▓┐▓╗öÓ░l(f©Ī)¼F(xi©żn)ą┬Ą─╬─½I(xi©żn)Ż¼╬ęéāĮ©┴ó╬„ė“Üv╩ĘšZ(y©│)čį蹊┐╦∙Ż¼Š═╩Ūę¬ī”(du©¼)▀@ą®╬─½I(xi©żn)▀M(j©¼n)ę╗▓Į蹊┐ĪŻ╬ęÅ─Ą┬ć°(gu©«)░č╔“ąl(w©©i)śsŽ╚╔·šł(q©½ng)╗žüĒ(l©ói)Ż¼Š═╩Ūę“?y©żn)ķ╦¹╩Ūį┌╬„ĘĮ蹊┐╬„ė“Ą─Ö?qu©ón)═■Ż¼╦¹ī”(du©¼)╬„ė“šZ(y©│)čįĄ─蹊┐ĘŪ│ŻŠ½╔ŅŻ¼ė╚Ųõ╩Ūī”(du©¼)╣┼▓žšZ(y©│)蹊┐Ż¼┴„ĄĮ╬„ĘĮĄ─╬─½I(xi©żn)╦¹╗∙▒ŠČ╝┐┤ĄĮ┴╦Ż¼╦¹╗žć°(gu©«)┐╔ęįĮėė|Ė³ČÓą┬░l(f©Ī)¼F(xi©żn)Ą─╬─½I(xi©żn)ĪŻ╬„ė“šZ(y©│)čį║▄Å═(f©┤)ļsŻ¼▓╗╩Ūå╬╝āę╗ĘNšZ(y©│)čįŻ¼ųą╣┼Ģr(sh©¬)Ų┌Ą─šZ(y©│)čį¼F(xi©żn)į┌ęčĮø(j©®ng)╦└┴╦Ż¼░l(f©Ī)Š“Ą─Üv╩Ę╬─½I(xi©żn)▒žĒÜė╔▀@ą®īŻ╝ęüĒ(l©ói)ßīūxŻ¼ĘŁūg│╔¼F(xi©żn)┤·╬─ūųĪŻ
ĪĪĪĪÅ─╩┬┴╦40─Ļ╬„ė“┐╝╣┼╣żū„Ą─═§▒■╚A╩ŪįŁą┬Į«ūįų╬ģ^(q©▒)┐╝╣┼╦∙╦∙ķL(zh©Żng)Ż¼╦¹ę▓▒╗šł(q©½ng)ĄĮ╬„ė“蹊┐╦∙ō·(d©Īn)╚╬Į╠╩┌Ż¼Ä¦čąŠ┐╔·Ż¼¼F(xi©żn)į┌╦¹ėŗ(j©¼)äØīæ(xi©¦)ę╗▓┐╬„ė“Ą─ķ_(k©Īi)░l(f©Ī)╩ĘŻ¼Å─šŲ╬šĄ─Üv╩Ę╬─½I(xi©żn)Ż¼Å─ūCō■(j©┤)│÷░l(f©Ī)Ż¼īæ(xi©¦)ę╗▓┐ųą╚A├±ūÕūŅįńķ_(k©Īi)░l(f©Ī)╬„ė“ų▒ĄĮ║¾üĒ(l©ói)Ą─Üv╩ĘĪŻ2005─Ļ╬ę║═╝Š┴w┴ųŽ╚╔·Įoųąčļīæ(xi©¦)Ą─ł¾(b©żo)Ėµ└’Š═ųvĄĮŻ¼īóüĒ(l©ói)ėą┴╦Üv╩ĘĀÄ(zh©źng)Č╦Ż¼╬ęéāėą░l(f©Ī)čįÖÓ(qu©ón)Ż¼╬ęéāąĶę¬─├│÷ūCō■(j©┤)üĒ(l©ói)Ż¼╬ęéāšŲ╬šĄ─╩Ę┴ŽąĶ꬚¹└ĒŻ¼ųąčļ║▄┐ņ┼·╩Š┴╦ĪŻÅ─╬ęć°(gu©«)Ą─Į«ė“ĪóÜv╩ĘüĒ(l©ói)ųvŻ¼ę¬ęį░l(f©Ī)¼F(xi©żn)Ą─┤¾┴┐╬─½I(xi©żn)×ķ£╩(zh©│n)Ż¼ī”(du©¼)╬„▓┐Üv╩Ę▀M(j©¼n)ąą╚½├µčąŠ┐Ż¼ūC├„╬„ė“╩ŪØh├±ūÕ║═ąųĄ▄├±ūÕįńŲ┌╣▓═¼Įø(j©®ng)ĀI(y©¬ng)ķ_(k©Īi)░l(f©Ī)│÷üĒ(l©ói)Ą─ĪŻ
ĪĪĪĪĻP(gu©Īn)ė┌Ī░┤¾ć°(gu©«)īW(xu©”)Ī▒Ė┼─Ņ Ī░Ę▓╩Ūųą╚A├±ūÕĄ─╬─╗»Ż¼Č╝╩Ūć°(gu©«)īW(xu©”)Ī▒
ĪĪĪĪėøš▀Ż║─·╚╬ųąć°(gu©«)╚╦├±┤¾īW(xu©”)ć°(gu©«)īW(xu©”)į║į║ķL(zh©Żng)Ģr(sh©¬)╠ß│÷Ī░┤¾ć°(gu©«)īW(xu©”)Ī▒Ė┼─ŅŻ¼«ö(d©Īng)Ģr(sh©¬)╩Ū╗∙ė┌į§śėĄ─╦╝┐╝Ż┐
ĪĪĪĪ±TŲõė╣Ż║╬ęūį╝║▓╗öÓ═∙╬„ū▀Ż¼ę╗ų▒Š═ėą▀@éĆ(g©©)ŽļĘ©Ż¼šµš²╠ß│÷üĒ(l©ói)╩Ūųąć°(gu©«)╚╦├±┤¾īW(xu©”)ć°(gu©«)īW(xu©”)į║äō(chu©żng)▐kęį║¾Ż¼┤¾╝ęėæšōć°(gu©«)īW(xu©”)Ą─Ė┼─ŅŻ¼╬ę╠ß│÷┴╦Ī░┤¾ć°(gu©«)īW(xu©”)Ī▒Ą─Ė┼─ŅĪŻ╬ęéāć°(gu©«)╝ę╩Ūė╔56éĆ(g©©)├±ūÕ╣▓═¼ĮM│╔Ą─Ż¼ąųĄ▄├±ūÕėąūį╝║Ą─╬─╗»Ż¼ūį╝║Ą─Üv╩ĘĪó╬─ūųŻ¼╩Ūš¹éĆ(g©©)ųą╚A├±ūÕĄ─ę╗éĆ(g©©)ĮM│╔▓┐ĘųŻ¼╝╚╚╗╩Ū╬ęéāć°(gu©«)╝ęĄ─ųžę¬ĮM│╔▓┐ĘųŻ¼╦¹éāĄ─īW(xu©”)å¢(w©©n)×ķ╩▓├┤▓╗─▄│╔×ķć°(gu©«)īW(xu©”)Ż┐┼²┼├Īó║·Ū┘Č╝╩ŪÅ─╬„▓┐üĒ(l©ói)Ą─Ż¼¼F(xi©żn)ęč╣½šJ(r©©n)×ķć°(gu©«)śĘ(l©©)ų«Ų„Ż¼╦∙ęį╬„▓┐├±ūÕĄ─╬─╗»║═╬─ūų└Ēæ¬(y©®ng)╝{╚ļć°(gu©«)īW(xu©”)Ą─ę╗▓┐ĘųĪŻ«ö(d©Īng)╚╗Ī░┤¾ć°(gu©«)īW(xu©”)Ī▒Ė┼─Ņ└’ę▓ėą▌pųžų«ĘųŻ¼Ą½Å─ę╗éĆ(g©©)═Ļš¹Ą─ć°(gu©«)īW(xu©”)Ė┼─ŅüĒ(l©ói)ųvŻ¼æ¬(y©®ng)įō▀@├┤┐┤┤²ĪŻÅłßĘ─ĻŽ╚╔·ę▓ųv▀^(gu©░)Ż║Ī░Ę▓╩Ūųą╚A├±ūÕĄ─╬─╗»Ż¼Č╝╩Ūć°(gu©«)īW(xu©”)ĪŻĪ▒╬ęĘŪ│Ż┘Ø│╔╦¹Ą─ė^³c(di©Żn)Ż¼▀@śėĄ─╠ßĘ©ę▓ėąų·ė┌Ė„├±ūÕĄ─╚┌║Ž║═łF(tu©ón)ĮY(ji©”)Ż¼╦∙ęį╬„▓┐蹊┐æ¬(y©®ng)įō╝{╚ļć°(gu©«)īW(xu©”)Ą─蹊┐ĘČć·└’├µĪŻ
ĪĪĪĪĻP(gu©Īn)ė┌╦ćąg(sh©┤)äō(chu©żng)ū„ ▓╗╩Ūšš─Żššśė─Żīæ(xi©¦)Ż¼┐╔ęį░l(f©Ī)ō]ūį╝║
ĪĪĪĪėøš▀Ż║─·Ą─īW(xu©”)ąg(sh©┤)蹊┐Ż¼ŚlĘų┐|╬÷Ż¼▀ē▌ŗć└(y©ón)ųö(j©½n)Ż¼š├’@┴╦┐ŲīW(xu©”)└ĒąįĄ─┴”┴┐Ż╗Č°įŖ(sh©®)«ŗ(hu©ż)Ż¼ģs╩Ū¤ßŪķ▒╝Ę┼Ż¼ęŌŠ│Ė▀▀h(yu©Żn)Ż¼╠žäe╩Ū─·Ą─ųž▓╩╬„▓┐╔Į╦«Ż¼ėąĘNš║│╚╦ą─Ą─├└ĪŻ
ĪĪĪĪ±TŲõė╣Ż║╦ćąg(sh©┤)äō(chu©żng)ū„▓╗╩Ūę¬─Ń═Ļ╚½šš─ŻššśėĄž─Żīæ(xi©¦)Ż¼─Ń┐╔ęį░l(f©Ī)ō]ūį╝║Ż¼ū▀▀^(gu©░)┴╦įSČÓųąć°(gu©«)Ą─╔Į╔Į╦«╦«Ż¼Š═Ģ■(hu©¼)├„░ūŻ¼╬ęéāĄ─ūį╚╗ą╬æB(t©żi)╠½žSĖ╗┴╦Ż¼╔ĮĄ─ą╬│╔ŪķørĖ„▓╗ŽÓ═¼Ż¼Ņü╔½ę▓▓╗ę╗śėĪŻĄ½╩ŪŻ¼ųąć°(gu©«)╣┼┤·Ą─«ŗ(hu©ż)╝ęČ╝ø](m©”i)ėą«ŗ(hu©ż)▀^(gu©░)╬„ė“Ą─╔Į╦«Ż¼╦∙ęį«ŗ(hu©ż)╬„ė“Ą─╔Į╦«Ż¼╩Ūę╗éĆ(g©©)äō(chu©żng)ą┬ĪŻørŪę╬„ė“╔Į╦«║═ųąįŁ╔Į╦«═Ļ╚½▓╗ę╗śėŻ¼ąĶę¬ė├ą┬Ą─«ŗ(hu©ż)Ę©Īóą┬Ą─╔½▓╩üĒ(l©ói)▒Ē¼F(xi©żn)╦³Ż¼╬ęė├ųž▓╩üĒ(l©ói)«ŗ(hu©ż)Ż¼╔ĮĄ─ą╬æB(t©żi)║═±ÕĘ©ę▓╩ŪĖ∙ō■(j©┤)╬„▓┐╔Į╦«Ż¼╠žäe╣┼²öŲØ(Äņ(k©┤)▄ć)╔Į╦«Ą─╠ž³c(di©Żn)üĒ(l©ói)«ŗ(hu©ż)Ą─ĪŻ╬ęļm╚╗«ŗ(hu©ż)┴╦║├ČÓ─ĻŻ¼Ą½ę▓╚į╚╗╩Ūį┌╠Į╦„Ż¼ę“?y©żn)ķ╬„ė“Ą─╔Į╦«ę▓▓Ņäe║▄┤¾Ż¼▓ó▓╗╩ŪĄĮ╠ÄČ╝ę╗śėŻ¼╦∙ęį▀@éĆ(g©©)├■╦„ę▓▓╗╩Ū║▄┐ņ─▄═Ļ│╔Ą─Ż¼ąĶę¬ėąĖ³ČÓĄ─«ŗ(hu©ż)╝ęüĒ(l©ói)╣▓═¼┼¼┴”ĪŻ
ŠW(w©Żng)ėčįu(p©¬ng)šō
īŻ Ņ}


ŠW(w©Żng)╔ŽīW(xu©”)ąg(sh©┤)šōē»


ŠW(w©Żng)╔ŽŲ┌┐»╔ń


▓® ┐═


ŠW(w©Żng)Įj(lu©░)╣żū„╩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