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民族文藝 >> 作品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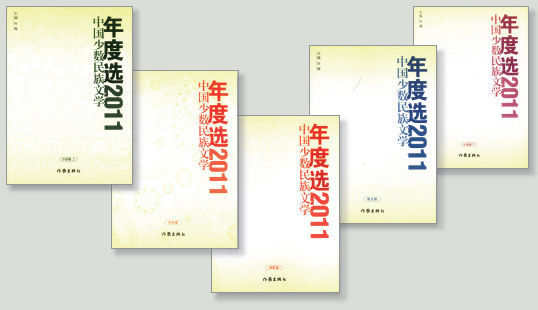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由葉梅主編的五卷本《2011·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年度選》,向公眾清晰地展示了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實績,以集束的形式展示了當下少數民族文學的真實風貌。它直觀地將“少數民族文學”呈現在人們面前,讓關于它的種種全稱判斷和統稱論述失去效力。這些具體的作家作品,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蘊含豐富的,因此需要我們深入到文本,體會作品中的情感,理解其中的思考,同它們進行對話。
按照小說、詩歌、散文、評論的分類,這套書細大不捐,有知名作家如張承志、吉狄馬加、葉梅、趙玫等的作品,馮唐、石舒清、金仁順等這些比較活躍的中青年作家也敘述在列,一些少數民族“80后”、“90后”作家也攬入其中。此外,該書還對一些用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等少數民族文字創作并翻譯為漢文的作品給予了充分關注,對珞巴、德昂、鄂溫克、普米、撒拉、毛南、錫伯等人口較少民族文學,也進行了大力推介。
從我閱讀的直觀感受來說,分為上、下兩冊的小說卷最為鮮明地體現了少數民族文學多樣性的風采,而詩歌卷最具有民族美學探索的成就,散文卷則文化意味最為深厚,評論卷相對較弱,與豐富多元的文學現實來說,無論從方法和意識上都有待范式的轉型。
一
小說作為當代文學中最有影響力的文類,證明了少數民族文學和漢族文學并沒有因為民族身份不同而帶來想象的差異。它們對于現世人生的觀照、對于故土家園的緬懷、對于超越性的追求,都在表明少數民族的生存狀態就是任何一名普通中國人的生存狀態,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期盼所渴望,就是任何一名普通中國人的現實情形。小說卷中選擇的作品關注現實的占很大比例,葉梅(土家族)的《玫瑰莊園的七個夜晚》讓人想起歐亨利的《警察與贊美詩》,不過顯然這是個中國當下本土現實的故事。農民工馬松在別墅玫瑰莊園的七個夜晚經歷了精神的輪回和升華。“七天”是《創世紀》中上帝造人的時間,是一個帶有神話原型色彩的周期。馬松原本是一個內心自卑、猥瑣乃至有些自暴自棄的落魄撿破爛農民,因為目睹了別墅主人米妖的生活,內心尚存的善念被簡單而純粹的美所激活,而經歷了脫胎換骨般的心靈新生。然而城市這個“燜鍋”并沒有給他機會,就在他準備還回手表時卻被保姆和保安設計的陷阱抓獲,這樣荒誕的結尾無疑讓人留下久久的沉痛和辛酸。救贖與救贖的絕望,讓這篇現實題材的小說充滿了超越性的恒久意味。孫春平(滿族)的《沽婚》充分地顯示了作者結撰故事與編排敘事的能力,聞維堅和呂曉雯假離婚、假結婚到最后弄假成真的故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事情最終朝著當事人無法控制的方向發展。小說審世觀人之準確、細節把握之精當、語言描寫之老到,充分體現了現實題材小說的魅力。鄧一光(蒙古族)的《深圳在北緯22°27'—22°52'》精巧地將技術、資本、權力與人的肉體、精神、心靈的變異通過隱喻的形式鋪陳開來。在深圳這樣一個資本前沿陣地,建筑工程師發現自己原來是一匹“夜照白”駿馬,夢想草原的繁盛;而女友瑜伽教練則是一只透翅長尾鳳蝶,飛過滄海和苜蓿。他們究竟是“隱身的生命”還是精神分裂的產物?
城市化給鄉土中國造成的影響毋庸諱言,石舒清(回族)的《浮世》以留守家中的妻子的視角書寫了農民工馬哈賽遠走新疆下礦上的故事,表現了金錢和技術對于鄉土情感的浸染。馬哈賽受傷弄瞎了一只眼之后在金錢與生命間的辯證取舍,凸顯了工具理性當仁不讓地占據了當下浮世的現狀。光盤(瑤族)的《孔雀》中,風景再好,年輕一代也不想在風景中生活,而竭力要保護風景的老干部余少華則被迫裝神弄鬼嚇走開發者,自己也被當作了“鬼”。“鬼”與“孔雀”之間的同一,其實講述了生存權、發展權與生態保護及可持續發展之間的聯系與緊張。第代著冬(苗族)的《狗仗人勢》中,石峽溝老社長寬嘴子的舊式思維在新經濟時代變得不合時宜,這是構成小說戲劇性沖突的關鍵。而不露痕跡的結尾,則說明“荒誕”已成為我們時代和生活的底色。
在這樣的現代性景觀中,純真和素樸成為稀有的品質。蘇蘭朵(滿族)的《尋找艾薇兒》中,落魄的狗販子設計騙錢,卻落入溫柔陷阱。小說的結尾非常巧妙:你以為作者心懷悲憫放了你一馬,殊不知圖窮匕見,兵不血刃地將真相殘忍地抖露出來。這豈非時代的真相?“艾薇兒”不過是個美好的幻覺,或者從正面的意義上來說,是一個理想。周耒(壯族)的《舞場》,空間角度頗為新穎,展示了在城鄉交接帶生活著的許多卑微人物,他們就像灑落在塵埃中的金屑,經歷時代和命運的沖刷洗禮才會煥發出耀眼的光芒。而趙玫(滿族)的《流動青樓》,書寫的就是一種“流動的欲望”,無論是浮浪的歸國“成功人士”米墟不加節制的欲望宣泄,還是普通職員伊東、蕭檣、余藎之間的情感糾纏。汽車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看到“物品”如何替代“情感”在現代情欲中成為暗通款曲的手段。拜物主義還體現在米墟交往的女性們“紅色跑車”、“大提琴女孩”這樣的替代性稱呼,她們的“無名”狀態正說明了人性在這些肉欲、物欲交換中的匱乏。而大提琴女孩最后的自戕則體現了作者的態度和立場。
在紛繁淆亂、生機勃然的生活中,一切都處于變動和發展的過程中。了一容(東鄉族)的《一路奔跑》則描寫了一個流浪漢“在路上”的狀態。在生與死的終極考驗中,他反思了金錢的虛幻,而親情則成為最后的安慰。這是失鄉、失業、失落、失心者的悲情、無奈和最后的守候。葉廣芩(滿族)的《后罩樓》說的是“幻想”的失落:王慶和與“我”對格格的想象,人們對于沒落貴族的想象,如今對于“文革”心態的想象,到最后都被拆卸得七零八落,留下的則是關于歷史、人心、世道之乖謬而不無蒼涼的感慨和嘆息。沙言(土家族)的《墓志銘》里,脫離鄉土的李立夏因為家庭糾葛回鄉省親,在祖輩墓志銘前的沉思將鄉土、家族、溫情、傳統的淪陷表露無遺。碑銘與現實的“互文”,讓主人公成了一個多愁善感又冷靜的旁觀者。他意識到,新一代的鄉土子弟已經和土地失去了最親密的聯系,這是我們社會的真相,無論如何眷念與不舍都已無能為力。阿拉旦·淖爾(裕固族)的《那一片土地》中,藏族女孩桑吉進城后遭遇了文化震驚,無法扎根下來,而在城市的一次次歷險讓她看清楚了原先草原的美好——雖然她再也回不去了。剛杰·索木東(藏族)的《阿瑪周措》里,年輕一代藏族青年面對的是失去了溫馨回憶的村莊,處于一種既不是過客也不是歸人的尷尬處境。小說對藏族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如何在變動中堅守某些恒定的價值,如何在嘈雜中樹立頑強的立場,這是許多作品竭力想要探討的主題。馬金蓮(回族)的《扛土槍的男人》中,好色荒唐、不務正業的老瓜頭一輩子扛著獵槍打兔子、勾搭婦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到老了偶然獵槍走火崩掉了卵子——另一種意味上的“槍”。這時,他才赫然發現尕老師守護女學生的苦心,猛然醒悟,接替了尕老師的位置守衛著學生們,升華成了具有高尚意義的“槍”,“槍”隱喻巧妙地成為一種精神成長和傳承的象征。白崇人(回族)的《山嵐》寫北京公司小白領潘福泉偶遇西南山區家鄉的高中同學山嵐,山嵐及其母親在山間建立中學的“夢”重新讓他思考自己的“城市夢”。小說有著樸實的清新氣息。張遠倫(苗族)的《那些細碎如蕎花的愛情》無論是敘事還是人物語言都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地方風味,而接地氣的底層人物及遭際更有著天高地闊的坦蕩與悲憫。
少數民族帶有原生色彩的文化尤能體現出作為獨特性存在的文化價值。黑鶴(蒙古族)的《獾》中,挖獾人在與群獾的對峙中感受到了獵物最后的尊嚴和憤怒,小說頗具生態警示色彩。萬瑪才旦(藏族)的《烏金的牙齒》里,“我”的小學同學烏金成了轉世的活佛,他圓寂后,“我”的牙齒也混入到他的牙齒之中,這個即圣即凡、凡俗合一的轉喻,不無智慧地對信仰做出了自己的解讀。帕蒂古麗(維吾爾族)的《牧羊神鞭》中,值得關注的是有關哈薩克人語言、心理、風情的民俗書寫,充滿讓人喜樂的生氣,有著來自草原大地的天然動人之處。德純燕(鄂溫克族)的《初長成》寫的是一個有驚無險的成長故事,其中充滿了溫暖的深情厚誼。李進祥(回族)的《換骨》是一篇具有“聊齋風格”的小說,說的是底層的溫情和寬厚。王小忠(藏族)的《我的故事本》講述的是普通生命的頑強與奮斗。
另有一些精彩的小說,在藝術手法上頗有特色。于懷岸(回族)的《正氣歌》中,環套結構為小說的敘述打上了真假莫辨的玄幻色彩。連綴情節的“正氣歌”的陽剛正氣與內容本身的詭譎陰森形成了和諧的搭配,使得整個小說充滿了引人入勝的魅惑。呂金華(土家族)的《黑煙》也是通過環套的結構講述了一個傳奇的諜戰故事。軍統特工“于”與日本間諜之間的糾纏爭斗,像一團黑煙將他籠罩在恩施城一輩子,最終勝利的只有時間。這種悠遠的人生況味在血與火的背景下更顯沉重。楊衍瑤(仫佬族)的《我們回家吧》中,一方面是對八桂集市的民俗描寫,另一方面則是在這種平和日常之下冰冷的暴力,之間的比照使得小說具有劇烈的內在張力。鐘二毛(瑤族)的《我們的怕與愛》是自敘傳式的寫作,讓我們看到過去的時光是有生命的,它們沒有消失,只是隱沒在了暗處。
向本貴(苗族)的《官場父子》以漫畫的形式講述兩代基層官員的故事,帶著泥土的香氣。關仁山(滿族)的《鏡子里的打碗花》以民工替富豪看家這種現實中不太可能存在的故事講述了農民工在城市的變異和墮落。凡一平(壯族)的《韋五寬的警察夢》中,憨厚的韋五寬被光火叔叔騙去行竊,這樣一個帶有傳奇意味的故事中穿插了許多社會新聞可以見到的情節。
二
曾經有人用“詩性思維”來論述少數民族文學所具有的特殊優勢。其實所謂詩性思維,就是指不同于被工具理性或者功利思維所異化的那種原初情感和本真詞語。它們在主流認知框架中具有了“陌生化”的效果,其實就具體某個民族的詩人而言,它就是日常、自然、貼近煙火的書寫。無論是從風格、意象、意境,還是從象征、隱喻、直接或間接的抒情來看,都是少數民族文學的核心部分。
讀年選中的詩歌卷,我的感覺可以用魯娟(彝族)的詩句來表達:“當我暮年,仍堅持抒情/不改脾氣,像個真正的孩子/躲在暗處,同樣的窗口/它送來最美的禮物”(《時光》)。這些語言的金子、詞語的鉆石,讓人靠近那些不同族群的人們和他們文化的內心。是的,正如娜仁琪琪格(蒙古族)在《十萬里的山河與長空》中所說,“是水引出了水,是光亮引出了光亮”,美好的詩句召喚出讀者內心的真誠、良善、美感、同情和希望。
北野(滿族)的《思想與陰影》組詩,奇譎、大氣、宏偉、詭異,充滿妙不可言的想象和平實直白的語言。詩人對于語言的敏感和思想的銳利,讓人在讀完這些氣象混沌的詩歌之后無法言說,只能說這是好詩!這樣的好詩如同他在《石獅子或石頭里一頭奔跑的野獸》中的句子:“我胸中有丘壑花木流水和一切野蠻之物/我可以自己花開花落也可以讓別人在其中奔騰”,如何面對一尊石獅子,或者說對于一尊石獅子的態度界定了外在的觀者本身,而石獅子在那里不言不語。少數民族文學就像這頭石獅子,它提供了各種觀察、考量它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孕育了一場新的文化變革。聶勒(佤族)的《大地情歌》則是以圣經式的頌歌體抒發生與死、青春與熱愛、神州與母愛,自豪地宣稱“半個世紀以來,我沒有再遷徙,再過流離的生活/我—是—中—國—的—阿—佤—人”(《我的族籍》),謳歌“世界的王子”就是“青春的神州”(《世界的王子》)。這樣的詩歌有著沛然莫之能御的磅礴氣派。
而少數民族詩歌中最突出的聲音是“斷裂的聲音”,是曹翔(普米族)的《家鄉,不說憂傷》中在“逐漸刻骨銘心地陌生起來的土地上”的憂郁書寫。經濟開發、資本的步伐日益進入原本寧靜悠遠的族群故地,烏托邦的田園夢想岌岌可危。生活發生了斷裂,讓詩人末未(苗族)不得不哀嘆“我拿什么安慰你們啊/除了一片云/一陣雨”。艾栗木諾(德昂族)感慨城市中“這么多的人來人往/這么多的路不夠這么多的人走”。白濤(蒙古族)的《動感的故鄉,馬背閃亮》焦慮在城里長大的孩子,“他們中的某一個/恐怕會和我現在一樣/慢慢地,就忘掉了/從前,那么好的/自己的童年”。馬旦尼亞提·木哈太(哈薩克族)的《夏牧場》也憂慮,“詩歌喪失夏牧場的氣息/擠壓,無助與嘈雜/為正在喪失的寧靜大聲呼喊”。這些無奈的憂傷在現實中得不到紓解,只能在詞語中抒發苦悶。
陳德根(布依族)的《在工業轟鳴中莊稼的疼痛》以直白、粗糲的力量展示了現實的兇悍和沉重。“工衣裹緊了青春和失眠/無所適從的面孔在流水線上反射著微光。失業,跳槽,拖欠工資,工傷/一次次天災人禍,讓這些田野里的麥芒,把鄉愁和鄉音都卡在嗓子眼/把回家的打算想象成油菜花的列車,讓郵戳追趕著一封遙不可及的家書/打工的人在顛簸中開成一朵稻花。心中一片璀璨/如同正在經歷一場陽光背面的艷遇”。“陽光背面”生存的底層,處于壓力的核心,然而卻能“在顛簸中開成一朵稻花。心中一片璀璨”,這是詩歌所具有的理想主義力量。
更多的詩歌是在艱難中,以故鄉為依托,在對風土、人物、情感的描寫和追溯中,提供安慰。如高照清(黎族)的《蛙聲縈繞的村莊》那樣的鄉土寫作,在少數民族詩歌寫作中數量極其龐大。這些詩歌體現的主題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如費城(壯族)的組詩《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最終表達的是“走回從前”的主題:“我必將回到這里/回到我的出生、乳名和方言/回到草木炊煙、酒香縈繞/回到故鄉的山川與河流/回到一棵苦楝開花的季節/在一粒種子最初的幽暗里/解讀一滴雨水的深度/在一首詩里,我時常遇到/故鄉的青草和落花/在一場春雨明凈的恩典里/我必須回到這里/回到云水覆蓋的蒼茫大地/回到雨水充沛的村莊/回到一首懷鄉詩恒久的故鄉”。柏葉(彝族)的《故鄉的月亮》中,表達的也是“我真想再次回到童年”的感想,是一種懷舊的追想和憶念。在以噴薄的氣勢書寫入海的岷江之后,羊子(羌族)在《喚》中斷然寫道:“故鄉喚我以漠然!”這是故鄉的召喚,讓日益冰冷的人復活了最初的血肉與榮光。
故鄉代表了文化的根蒂,這樣的根雖經歲月磨折、現實消損,而終究不能全然泯滅。就像梁長江(白族)的《滇西北記憶》中寫下的,“時光的黑洞把一切吞沒/故事卻頑強地在歲月底部復活”。向迅(土家族)的《清江,人世畫圖》以攝影式的淡入淡出,以及蒙太奇式的意象組合,在清江一隅看到了整個人世:“是他們的一雙雙腳,攆著日子奔跑/是他們一雙雙如松皮的手/收割糧食和愛情/是他們低下如稻谷的背脊/領受了來自太陽和星群的光芒。”故鄉博大精深、淵深久遠,它是“高天之上,大河之下/廢棄的王朝帶走細節,留下人民、文字、語言/在日全食的黎明,在圣靈沉睡的深處/亙古的羅盤指東道西,打算著光陰和信仰”(回族作家單永珍的《措哇尕則山》)。背靠這樣的文化,詩人在詩歌中恢復了驕傲。烏斯滿江·薩烏啼(維吾爾族)的《紅玫瑰花瓣拋撒我的頭頂》寫道:“大逆不道的騎士迷途而亡,/你渴望著窗前的鮮花怒放”。張牧笛(滿族)更是直抒胸臆:“我站在曠野的中央,打開月光,歌唱愛/也為世間所有貧瘠的美,放聲地,痛哭。”
詩人們對那些曾經被外來文化遮蔽的行為、實踐乃至思維,則保持了必要的距離和否定之否定式的反思。如同花盛(藏族)的《我覺得自己陌生》中寫的:“我覺得自己陌生/這么多年,我總像一個路人/與她們擦肩而過/有時候,美麗就在身邊,愛就在身邊/而我們卻不曾發現”,對于那條無名的河流的不了解,難道不就是絕大多數人對于共同生存在這片大地上的各民族同胞的陌生一樣嗎?廖淮光(苗族)的《峨眉河踏春》通過農民對觀光客的態度,赫然洞察:“他只一眼就看穿了我們,我們不懂春天,/不懂一朵花的慢;就算閃光燈把世界照亮,/花仍然開在花開處,翻不開春天的心事。”外來者浮光掠影,永遠無法觸及某種文化的靈魂深處。這樣的精神底質只有通過詞語的解放和文化的敞亮才能達到,倮伍拉且(彝族)的《大涼山的十二座山》就是一種嘗試。這首長詩通過對神話、愛情、冰雪、云霧、神靈、祖先等的歌唱,展現了邊地文化的光輝。
這些有了母族文化寄托的詩人神魂俱足,將故鄉背在身上和心上,在浮華的世間行走也就自我飽滿,不至于喪失自信。就像李貴明(傈僳族)的《我的滇西》中所說,“我要帶著象達的溫暖流浪人間”,“情愿在一碗暗色的酒里坐失江山/我情愿像一塊沉默的石頭”。“沉默的石頭”是堅定的、自信的、有底氣而不容輕褻的。阿卓務林(彝族)的《奢侈的一生》更是暢想,“我只要前世修來的那位/當我今生的妻子,由她給我生一個兒子/以便讓祖輩歷經千辛萬苦積攢下來的母語/至少在我之后尚有一個人去訴說/除此之外,我還須奢望什么呢/在這個寥廓的世界,這短暫的一生”。這是一種守候的恬然和自足。
如果說執守故土是一種文化上的信仰,那么從少數的文化走向共通,即立基于局域、本土、母族,又超越于地方性和狹隘性,走向一種相互尊重、彼此交流、尊重共榮才是最終的理想狀態。吉狄馬加(彝族)的《嘉那瑪尼石上的星空》抒發的就是這樣一種美妙的狀態:“我就是一只遺忘了思想和自我的海螺/此時,我不是為吹走而存在/我已是另一個我,我的靈魂和思想/已經成為了這片高原的主人。”西南的彝族能夠在西北的藏地有主人的感覺,正說明了各民族“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休戚關聯。
三
散文卷以各種游記、鄉土回憶、景物描寫及其引發的思索居多,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那些以失去的故園為對象的文化散文,在勾稽民族歷史、爬梳家族興衰中為一個族群的精神和心靈立傳。他們的態度大致可以用仲彥(土家族)的《澧水南源》的開宗明義來概括:“像不為世俗所動的人一樣,我一邊用柔韌的力量,同這個世界的一切苦難進行柔弱而又堅韌的抵抗,一邊在自己的朗朗乾坤里,刻寫下靈魂、信念、歌唱和秘密。就像流星劃過天空,就像陽光照射宇宙,瞬間的光芒固執而又倔強地照亮著精神的空間和夢想的天堂。我知道,自己性格的形成,和生存的環境息息相關。準確地說,我是這個民族特有的地理環境、文化土壤和民族性格培養出來的個體的生命形式……為自己的民族活著,做民族的歌者。在這個物化的世界里,我知道這樣做很傻,但我卻仍然自得于自己的天真和純粹。”
無論這段話多么高蹈凌虛,甚至有些偏執,但不可否認,確實有這樣的人存在。世變勢移,偏遠地區的文化讓人憂心忡忡,于是有些人做出了不得不做的選擇。羌人六(羌族)在《發表了日出的群山》中寫道:“群山風物是歲月流轉人間的一道硬傷,更是那些走向天涯兒女共同的惆悵,那些再也沒有歸來的浪子是詩,輾轉歸來的是小說,一直不曾離開的是散文。……文字興許是最后的故鄉了,他們就像故鄉的群山一樣繚繞在我滾燙的額頭,我不得不守住悲咽,在如此單薄又如此明亮的命運里深陷。”這大約是很多少數民族作家的共同心聲。
敖長福(鄂倫春族)的《嘠仙遐想》、艾克拜爾·米吉提(哈薩克族)的《阿勒泰,天下無處尋覓》、祁建青(土族)的《大昆侖經幡山》等都是類似的文化散文,將民族的秘史和個人的經歷與感喟交融一起,樹立起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和個體的自豪感,同時也傳播了有關民族文化的種種知識,具有認知、教育、娛樂和審美等多重價值。而對于本族群文化有著深刻了解的作家,往往能夠破除外來文化附加于自身民族文化上的種種迷霧,丹增(藏族)的《香格里拉》就是絕佳的例子。文章從歷史、現實、學理、個人感悟不同側面書寫了“香格里拉”,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不是抓在手里的永恒金傘,而只能是為民眾帶來幸福、快樂、尊嚴的標桿。精神追求的香格里拉,世俗欲望的香格里拉,佛教理念的香格里拉,文學創新的香格里拉,現實尋到的香格里拉,都會給人平淡的生活帶來平靜的升騰,就像夢能激活大腦里的潛意識。”這無疑有助廓清認識,不僅僅是對“香格里拉”的態度,而且是具有可以適用于各種他者文化的通用法則。
對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出路的思考,也體現在一些作品之中,如阿庫烏霧(彝族)的《低于大地的歌唱》就對彝族的畢摩文化、送靈儀式、誦經和文字等進行了富于詩意的闡發和探索。他的書寫就有了“招魂”的意味:“我們共同祖先創制的古老的文字被狹窄、狹隘和歷史性的短視所禁錮。實際上被久久地懸置于神秘而漆黑的山洞之中。于是,我們更多的族人的身體從未接受過祖先書寫文明的雨露自在的沐浴,從未感受過古老文字的光芒透徹的照耀!……被懸置的文字,猶如被久久流放在野山野水之中閃光的魚類,要自由自在地游向大海,還將有很遙遠的路程……”正是有著這樣的清醒認識,也許才是后發族群文化在未來有新的發展可能的契機。
另一些由小見大、尺幅興波的文章,帶有哲理的達觀和從容。如陶麗群(壯族)的《夜色里,那些關于村莊的記憶》寫了記憶中故鄉“插青墻根下的父親們”,“坐在自己生活一輩子的村莊墻根下,懷揣一生經歷的世事,等待時光最后的召喚,臉上帶著預知的從容安靜,把死亡變成了從村莊走到坡地上那樣簡單的事情。”李天斌(彝族)的《舊時光》從張愛玲文本入手,而終結于博爾赫斯的思考,最終達到了思想境界上的通透:“時光最終是一張網,時光在交叉的同時,也呈現出無限的可能性。在這樣一種終極的意義里,您或者我,都是不小心跌落在其間的一只蟲子,一只微不足道的蟲子,一只舊年的蟲子。關于故事,所有的恩怨情仇、明月秋花,早已只剩下一句話,在幽幽的爐香中一點點漫漶,一點點呈現又一點點消失。”趙晏彪(滿族)的《父親的毒酒》以平樸質實之言,通過對父親一生的白描式勾勒,展示了寬容和悲憫具有久遠的內涵。
張承志以厚重淵博的行者之文,書寫中國山河的文化地理學。格致(滿族)的《信任》則通過女性身體上“微妙的內在聯系”的同情共感,體悟到“所有的痛都是大家的”,將日常升華為帶有普遍和深刻意義的凝練性思考。這些作品無疑豐富了中國當代散文的創作格局。
四
少數民族文學評論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散文寫作,只不過是從另一角度切入的。雖然評論總是滯后于創作的現實,但往往能從理論上予以創作一定的啟示。評論卷中所選的文章基本上涵蓋2011年出現的較重要的批評和理論探索。既有馬明奎有關少數民族文學意象的敘事性研究,也有歐陽可惺對于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批評的介入理念的厘析;既有李長中對人口較少民族文學“重述歷史”的關注,也有馬季對于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觀照。民族文學的主體性、文化的地理寫作、民間話語的視角、少數民族兒童文學、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都有所涉及。蒙古族、藏族、黎族、朝鮮族、哈薩克族、哈尼族、土家族、撒拉族、回族、彝族、維吾爾族……都有兼顧;西南邊疆、西北邊疆、涼山、鄂西、烏江流域、重慶、云南等地的少數民族都有論述。應該說,評論卷就是這套五卷本年選的縮影,是典型意義上的全面盤點。
當然,既然是選本,就難免有遺珠之恨,這是不可避免的。不過,無論是從藝術的審美價值,還是認知少數族群的知識價值,無論作為當下動態文學史料的文獻價值,還是作為文學個案群像的研究價值,這個選本都是較為權威和全面的集合,提供了我們觀測近年來少數民族文學蓬勃發展的風向標和晴雨表。
這應該是少數民族文學首次有這樣群像出現的年度選集,一方面反映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充滿活力的繁榮生態,另一方面也是具有文學史意義的文化實踐和舉措。假以時日,這樣的年選陸續做下去,將會為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留下豐厚的財產,而新的文化就萌生在這些鮮活的文本中也未可知。日后,我們談論少數民族文學,就可以驕傲地說,我們談論的就是這一個個生動美麗的存在。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